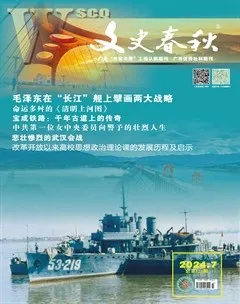命運多舛的《清明上河圖》
1949年7月,東北博物館(現遼寧省博物館)在沈陽成立并開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開放的博物館。1951年初,東北博物館開始著手整理、鑒定解放戰爭中留下的文化遺產。在該館臨時庫房里,當書法鑒定專家無意間打開一卷殘破的畫卷時,頓時眼前為之一亮——《清明上河圖》,這是否就是那幅被歷代皇室權貴爭相收藏的稀世珍品?不久,這幅長卷被火速送往北京國家文物局做進一步鑒定。
楊仁愷發現“上河圖”真跡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一行人,幾經輾轉,準備秘密逃亡日本,在沈陽機場候機時,被蘇軍俘獲。溥儀隨身攜帶的一批珠寶、玉翠、法書、名畫,同時被蘇軍收繳,存放于東北銀行代為保管。1949年8月,東北人民政府批示這批文物撥交東北博物館接收清點。
1950年冬,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研究室研究員楊仁愷和同事們接受了清點這批文物的任務。1951年初的一天,負責對從各方收繳來的大量字畫進行整理、鑒定的楊仁愷來到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與博物館館員一起在堆積如山的藏品中,進行撿拾鑒定。在一堆已經被其他工作人員認定為贗品的書畫作品中,楊仁愷無意間看到了一卷殘破畫卷,題簽上寫著《清明上河圖》,他順手拿起端詳。由古至今,《清明上河圖》的仿本太多,經楊仁愷親自過目的贗品就有10多件,結果都是明清蘇州仿摹本。張擇端繪制的《清明上河圖》真本自北宋后便神秘失蹤,幾百年來,人們對它的真實面貌始終一無所知,民間流傳著30多個版本的仿作,仿效、復制的手法大同小異。但這次,隨著這幅畫卷一點一點地展開,楊仁愷已經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被眼前這幅畫卷震撼住了。
這是一幅長卷畫,畫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已十分久遠,這幅長卷氣勢恢弘、筆法細膩,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特別是畫中的描繪手法無不體現著獨特的北宋繪畫特征,與仿摹品有著天壤之別。這個畫卷上雖然沒有作者的簽名和畫的題目,但不可思議的是,畫卷上的名人題跋卻非常的豐富翔實,歷代鑒藏者的印章更是琳瑯滿目、紛繁復雜。
解讀著畫卷上歷代名人留下的題跋所透露出的信息,再結合此畫的時代風格,激動的楊仁愷斷定:這幅殘破的畫卷應該就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之后,楊仁愷又通過研究畫上的題跋,參照相關史料的記載,更堅定了自己的判斷,他把畫卷照片發表在東北博物館編印的《國寶沉浮錄》中,立即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
很快,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將這幅畫卷調往北京。專家們經過進一步考證鑒定,確認這幅長卷就是千百年來名聞遐邇的《清明上河圖》真跡。這幅有北宋社會“百科全書”之譽的畫作自問世后,曾5次入宮,4次被盜出宮,輾轉多人之手,因其珍貴而命運多舛。
宋徽宗命張擇端作畫卷
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在北宋都城東京(又稱汴京、汴梁)雕梁畫棟、巍峨壯闊的相國寺中,聚集了不少以繪畫謀生的民間畫師,其中有一位善畫風俗畫的年輕畫師,他叫張擇端。游學東京的張擇端被屋宇林立、繁華似錦的京城所打動,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和激動,立志要把這盛景繪制成一幅長卷。由于初到京城,盤纏用盡,他只得投奔寄寓相國寺,夜晚給寺院修補佛教壁畫,白天則在寺里的簡陋倉房里潛心作畫。
一天,宋徽宗在皇家衛隊的護衛下,聲勢浩蕩地駕臨相國寺上香。宋徽宗聽說相國寺內有一個聲稱要把繁華的東京城搬到畫中的年輕人,于是召見了張擇端。交談之中,兩人十分投機,酷愛繪畫的宋徽宗對張擇端精湛的畫藝贊不絕口,認為眼前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是不可多得的繪畫奇才,立即下旨將他招入翰林圖畫院。為了彰顯大宋王朝的富麗與繁華,宋徽宗親自給張擇端命題,讓他把東京的繁華盛景繪成畫卷,以示后人。從此,張擇端廢寢忘食,潛心繪制長卷。
冬去春來,轉眼清明時節到來,東京城生機勃勃、繁華鼎盛,城內四河流貫,為水路交通中心,商業發達,居全國之首,人口達100多萬,逢年過節更是熱鬧非凡。張擇端也出現在忙碌的人群中,但他出游的目的不是休閑游玩,而是深入街巷觀察了解民俗民情,為繪畫創作做準備。
經過數載努力,張擇端終于創作完成了一幅長卷。當擺放在御案上的長卷被慢慢展開時,瞬間便把宋徽宗的目光吸引住了,畫卷中欣欣向榮的東京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他面前。這幅長達5米多的畫卷,以全景式的構圖、細膩的筆法,真實記錄了當時東京繁華熱鬧的景象,清明時節的市井百態躍然紙上。被畫卷中夢幻般的繁華祥瑞之氣所迷醉的宋徽宗稱這幅長卷為神品,親筆在畫上題寫“清明上河圖”5個字,還專門蓋上了他那枚特制的雙龍小印,從此將這幅長卷視為珍寶,收入皇宮內府秘藏。
珍貴畫作幾度流散民間
北宋皇帝宋徽宗是傳世杰作《清明上河圖》的第一位收藏人。此后,《清明上河圖》一直是后世帝王權貴、文人墨客把玩欣賞、巧取豪奪的目標,在漫長的歲月中,它輾轉飄零,歷盡劫難。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大宋國力衰弱,金兵大舉進犯中原,東京陷落,古都變成一片廢墟。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擄走宋徽宗、宋欽宗,搶掠無數珍藏北返。北宋至此滅亡,因此事發生在靖康年間,史稱“靖康之難”。“靖康之難”發生時,據說宋徽宗聽到金銀財寶等被擄掠,毫不在乎,但聽到自己的皇家藏書也被搶去,悲痛得仰天長嘆。此后,《清明上河圖》便在兵荒馬亂中被盜出宮,流散民間,不知去向。直到北宋亡國60年之后,這幅長卷才開始在民間神秘地輾轉隱現。
《清明上河圖》流散在民間時,有張著、張世積等金代文人在該畫卷上題過跋。元朝滅亡金朝以后,該畫就被收入元朝內府。一天,元朝內務府的一名裝裱匠偶見其畫,如獲至寶,用仿本將原作換出,又將真畫賣掉。元至正年間,有一個名叫楊準的人收藏過該畫,并在題跋上把得畫前因后果及這幅畫的流傳說得清清楚楚。
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圖》真本又多次易主,從詩人李東陽到官員陸完,然后落到權傾朝野的宰相嚴嵩父子手中,后嚴嵩被彈劾,其家產充公,畫卷被收入明朝皇宮。明萬歷年間,這卷畫再度神秘失蹤。后來人們才知,《清明上河圖》落入權勢顯赫的太監、東廠首領馮保之手,因為馮保也忍不住在畫卷后加了題跋,把他得到這幅名畫的時間記錄得清清楚楚。馮保以后200多年中,此畫卷又下落不明,而坊間卻有許多《清明上河圖》偽本廣為流傳。
乾隆帝命畫師作仿本
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6),極為喜愛書法的乾隆皇帝曾命內宮搜尋《清明上河圖》真本。雖然找到了一些藏本,但乾隆看過后皆不滿意,并認為真本已失傳。于是,乾隆命清宮畫院的5位畫家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長,合力重作一幅作品,這就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如此大規模的重作畫卷,令世人都以為真本真的已從人間消失。但是,到了乾隆晚期,《清明上河圖》又神秘地重現江湖,后輾轉落入當時湖廣總督畢沅之手。
畢沅得到畫卷后,經常與其弟畢龍同賞,現今畫卷上便有二人蓋的“畢龍審定”的印記。清嘉慶四年(1799年),畢沅受和珅案牽連,畢家被抄后,《清明上河圖》再入宮中,并收藏在紫禁城的迎春閣內。嘉慶皇帝對其珍愛有加,命人將畫收錄在《石渠寶笈三編》內。此后《清明上河圖》一直被珍藏在清宮之中。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圖》與其他書畫精品一起,被遜帝溥儀以賞其弟溥杰為名盜出宮外。
1932年,溥儀在侵華日軍的操縱下就任偽滿洲國皇帝,《清明上河圖》陪伴著溥儀,在長春偽皇宮東院圖書樓度過了長達13年零4個月的歲月。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寫實生動的市井風俗畫,全圖以長卷的形式生動細致地再現了北宋都城寧靜的郊外到熱鬧的城內風貌,街市的繁華景象,處處引人入勝。在這幅長528.7厘米、寬24.8厘米的畫卷上,張擇端共畫出形形色色的人物815個。人物雖小不及寸,動作表情卻皆曲盡其意,刻畫之精細,令人嘆為觀止。大到流淌的河流、雄偉的城樓,小到市招上的文字、舟車上的人物,都能真實自然、和諧統一地交織在一起,畫卷中的這一切都使觀者恍若置身流水游龍間。這幅畫的珍貴不僅表現在它的藝術成就上,在其流傳過程本身就是一部歷史長歌。當楊仁愷將《清明上河圖》真本從堆積如山的文物中尋撿出來,這個命運多舛的傳世之寶才終于回到國家手中。
1953年,《清明上河圖》由東北博物館正式移交給北京故宮博物院作為國寶收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