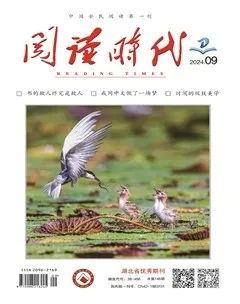趣話“糾錯詩”
所謂“錯別字”,是錯字和別字的總稱。筆畫不對,錯得不成其為字,是錯字;寫某一個字,寫錯了,成為另外一個字,是別字。當某人寫出了或說出了“錯別字”后,另一個人在為其糾正時用的是打油詩,就是“嘲諷”了。現把搜集到的一些“糾錯詩”實錄如下,供讀者茶余飯后一笑。
北宋時,有兩個相公進京趕考,因途中遇雨,便跑到一座廟門下避雨。其中一個看到廟門上首寫著“文廟(廟)”二字,便信口念道:“文朝。”另一個聽了后,端詳了一會兒說:“這哪里是‘文朝’,明明寫的是‘丈廟’嘛。”于是,兩人就爭論了起來。恰逢有個化齋的老和尚途經此地。一個相公說:“我們別爭了,讓化齊(齋)的老和尚來評評是非吧。”另一個相公卻說:“老和尚怎能評出對錯,還是把那兩個字描下來,上京城去請教大詩人蘇東皮(坡)吧。”老和尚問明原委后,就吟了一首“以錯對錯”的打油詩,來嘲諷這兩個“錯別字”不離嘴的相公。詩曰:
文朝丈廟(廟)兩相異,吾到東莊去化齊(齋)。
你們不是孔天(夫)子,吾也不是蘇東皮(坡)。
傳說古代有個人靠走后門中了解元后,就自以為了不起。一次,他見書中有“蔡中郎”一詞,大罵古人粗心大意,連“郎中(中醫醫生)”都寫成了“中郎”。時人笑之,并將錯就錯,故意把“招牌”“解元”“陶潛”三詞顛倒使用,寫了一首打油詩來嘲諷那個“解元”。詩曰:
改行當郎中,大門掛牌招。
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
清代有個縣令,給巡撫寫信,把“大人鈞稟”寫成了“大人釣稟”,“鈞”字漏掉了一點。巡撫看后,在信上面題了一首打油詩后,把信退回給了縣令。此打油詩曰:
未必他年秉大鈞,
垂竿頓觸釣魚心。
可憐一勺廉泉水,
分贈同僚總不勻。
從前,一位很有學問的人,偶然從一所村學門口經過。他聽到村學老先生大聲教學生:“都都平丈我。”他聽了莫名其妙,不知這句話出于何處。他向那位老先生請教,才知道老先生把五個字都念錯了。他向學生們糾正說,應該讀成“郁郁乎文哉”。那些學生一聽,都嚇跑了。塾師不學無術,誤人子弟甚矣!這位有學問的人見此情景,提筆在桌上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
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吳趼(jiǎn)人是清代作家,因他名字中的“趼”字,許多人都讀成了“妍”字,常常弄得他十分尷尬,所以為了表明自己不是美麗嬌妍之人,并嘲諷那些“白字先生”,就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
姓氏從來自有真,
不曾頑石證前生。
古端經手無多日,
底事頻呼作研人。
清代嘉慶年間,一次,漕運總督許兆椿因事途經長沙,一位即將赴任武岡刺史的官員忙具稟帖拜訪他。因稟帖上把“漕”字寫成了“糟”,許兆椿看后大笑,提筆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
生平不作醉鄉侯,
況奉新綸速置郵。
豈可尚書加曲部,
何妨邑宰作糟丘。
讀書字應分魚魯,
過客風原各馬牛。
聞道名區已遷轉,
武岡是否五缸州。
20世紀30年代,著名文學編輯趙景深曾翻譯一些外國作品,但由于對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譯作中時有錯誤出現。一次,他遇到“the Milky Way(銀河)”,按字面意思理解翻譯成了“牛奶路”。此后不久,他又將神話中的“半人半馬怪”,錯譯為“半人半牛怪”。時人譏之為“牛頭不對馬嘴”,魯迅先生針對趙景深譯作中的這兩處錯誤,寫了一首打油詩,善意地提醒了趙景深治學上需更加嚴謹。詩曰:
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
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
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一次歡迎外國人的宴會上,考古學家夏鼐(nài)先生旁邊,坐著某大報的總編輯。此人是個“白字先生”,他一看桌上寫有“夏鼐”的牌兒,便主動同夏鼐打招呼,稱夏鼐為“夏鼎同志”,使得夏鼐哭笑不得。后來,作家白漁聽到了這個笑話,就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
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同志嚇一跳:
偷我頭上一個乃,還來同我打交道。
現代作家廖沫沙,一次在閱讀報紙時,發現偏旁相同的“齟齬”一詞錯印為“齷齪”后,十分生氣,于是就信手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
“齟齬”忽而成“齷齪”,相爭何必發臟聲。
文章求達不求雅,報道居然出異聞。
20世紀80年代科學院院士還叫學部委員時,在南京一家報紙所登載的學部委員名單中,竟把朱夏委員誤排印為“失夏”,朱夏委員看到后,啞然失笑的同時,戲作一首打油詩。詩曰:
錚錚鐵骨何曾斷,
小小頭顱尚喜留。
從此金陵無酷夏,
送春歸去便迎秋。
(源自《月讀》,郭旺啟薦稿,有刪節)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