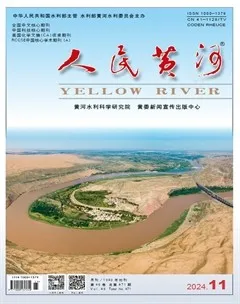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輸沙規(guī)律研究
















摘 要:黃河下游河床長期處于淤積抬升狀態(tài),其沖淤演變規(guī)律對于下游河道治理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快速預測不同量級高含沙洪水各河段的沖淤量以及判斷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游蕩河段沖淤影響很有必要。根據1960—2021 年54 場高含沙洪水的實測水沙資料,分析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游蕩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流量、含沙量、輸沙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并建立關系式,系統地研究高含沙洪水的輸沙規(guī)律。結果表明,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存在極強的相關性,進一步按來沙系數分級得到高含沙洪水期的輸沙率公式,能夠很好地模擬沖淤過程,極大地提高了與實測水沙資料的貼合度。以小浪底水文站為黃河下游游蕩河段的進口控制水文站,采用按來沙系數分級所求的輸沙率關系式能夠較準確推求花園口站、夾河灘站、高村站的輸沙率,從而計算小浪底—花園口、花園口—夾河灘和夾河灘—高村河段的累計沖淤量。
關鍵詞:輸沙率;來沙系數;河道沖淤;高含沙洪水;黃河下游
中圖分類號:TV122;TV882.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 j.issn.1000-1379.2024.11.005
引用格式:李國豪,張敏,劉俊.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輸沙規(guī)律研究[J].人民黃河,2024,46(11):29-36.
0 引言
黃河中大量的泥沙是在高含沙洪水期被輸移的,高含沙洪水的特點是含沙量非常大,河床形態(tài)變化迅速,主河道交替淤積和沖刷[1] 。高含沙洪水期,河床演變規(guī)律、洪水演進狀況復雜,給黃河下游防汛工作帶來一系列特殊問題,給汛期洪水預報造成極大的困難。黃河下游水沙變化規(guī)律、河床沖淤演變過程及其發(fā)展趨勢一直備受學者們關注,準確預測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河道泥沙沖淤過程及其沿程分布,可以為下游河道治理及上中游水利工程建設提供科學依據。已有研究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黃河下游河道沖淤對洪水過程的響應,研究了不同流量、不同含沙量洪水對下游河道沖淤的影響[2] ,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整個黃河下游或者整個汛期,對高含沙洪水期不同河段水沙規(guī)律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河道沖淤過程及其沿程水沙輸移規(guī)律。
關于高含沙洪水,目前尚無嚴格確切的劃分標準。河段不同,高含沙洪水輸移及沖淤特性也不同,劃分標準就有所不同,主要緣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目的。張瑞瑾[3] 、趙文林[4] 、齊璞等[5] 、惠遇甲等[6] 、申冠卿等[7] 從不同研究角度對高含沙洪水提出了劃分標準。整體來看,通過研究高含沙洪水特性,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認識,即黃河中下游洪水含沙量在200 kg/ m3以上可認為是高含沙洪水。為使本文成果更好地結合黃河實際,為河道輸沙規(guī)律研究提供科學依據,本次研究中對高含沙洪水的劃分主要參照黃河防汛調度標準,即洪水過程中潼關站瞬時含沙量大于200 kg/ m3且洪峰流量大于2 600 m3 / s,考慮到三門峽水庫攔沙和滯洪期一些高含沙洪水經潼關至三門峽區(qū)間調整后,三門峽出庫含沙量很低,劃入高含沙洪水不合適,經分析該階段進入下游高含沙洪水除滿足以上條件外,三門峽出庫瞬時含沙量應大于200 kg/ m3。根據以上高含沙洪水劃分標準,統計得出1960—2021 年共發(fā)生了54 場高含沙洪水。
本文主要研究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小浪底、花園口、夾河灘和高村4 個水文站的輸沙率與上站水沙因子之間的關系,從下站輸沙率與上站流量、含沙量以及輸沙率之間的關系角度出發(fā),闡述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小浪底—花園口(小花)、花園口—夾河灘(花夾)和夾河灘—高村(夾高)河段的水沙輸移特性。小浪底、花園口、夾河灘和高村平均輸沙率依次以QS1 ~QS4表示、平均流量依次以Q1 ~Q4表示、平均含沙量依次以S1 ~S4表示,其中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及平均輸沙率都為每場高含沙洪水的平均值。根據1960—2021 年54 場高含沙洪水的實測水沙資料,分析高含沙洪水期小花、花夾、夾高河段的下站輸沙率與上站流量、含沙量、輸沙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關系式,系統地研究高含沙洪水的輸沙規(guī)律。
1 高含沙洪水期各河段水沙輸移特性
1.1 小花河段
根據小浪底和花園口水文站的水沙數據,計算出每場高含沙洪水的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和平均輸沙率,點繪花園口輸沙率與小浪底流量、含沙量和輸沙率的關系散點圖,如圖1 所示。花園口輸沙率與小浪底流量關系相對散亂,確定系數僅為0.182 98;花園口輸沙率與小浪底含沙量關系也較一般,確定系數為0.473 68;花園口輸沙率與小浪底輸沙率關系點群較集中,確定系數為0.911 23,明顯大于與小浪底流量及含沙量的確定系數。
1.2 花夾河段
根據花園口和夾河灘水文站的水沙數據,計算出每場高含沙洪水的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和平均輸沙率,點繪夾河灘輸沙率與花園口流量、含沙量和輸沙率的關系散點圖,如圖2 所示。夾河灘輸沙率與花園口流量確定系數僅為0.287 94;夾河灘輸沙率與花園口含沙量確定系數為0.608 38;夾河灘輸沙率與花園口輸沙率確定系數為0.923 96,明顯大于與花園口流量及含沙量的確定系數,也比花園口輸沙率與小浪底輸沙率的確定系數大。
1.3 夾高河段
根據夾河灘和高村水文站的水沙數據,計算出每場高含沙洪水的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和平均輸沙率,點繪高村輸沙率與夾河灘流量、含沙量和輸沙率的關系散點圖,如圖3 所示。高村輸沙率與夾河灘流量確定系數僅為0.329 35;高村輸沙率與夾河灘含沙量確定系數為0.648 55;高村輸沙率與夾河灘輸沙率確定系數為0.949 48,明顯大于與夾河灘流量及含沙量的確定系數,也比小花、花夾河段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大。
根據對黃河下游游蕩河段水沙數據的分析,可以明顯得出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優(yōu)于與上站流量、含沙量的關系。此外夾高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優(yōu)于花夾河段,更優(yōu)于小花河段,這表明隨著洪水沿程向下游的流動,處于下游河段的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會變得更好,原因是小浪底站來水來沙經過沿程不斷調整,使得水沙搭配關系變得更加協調。因此,可以選擇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式作為定量反映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沿程輸沙規(guī)律的關系式。
2 輸沙率關系式合理性檢驗
基于小浪底站1960—2021 年54 場高含沙洪水的實測水沙數據,利用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式,沿程遞推出花園口站、夾河灘站和高村站的輸沙率,并采用沙量法計算出場次高含沙洪水的沖淤量,推求出54 場高含沙洪水的累計沖淤過程,對比實測累計沖淤過程,如圖4 所示。由圖4 可知,二者存在較大的差別,除1970 年前計算值與實測值接近外,在1970 年之后二者差距逐漸增大,到2018 年差距達到23 億t,這表明計算精確度較低。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在率定下站與上站輸沙率關系時,受個別特大輸沙率場次高含沙洪水影響較大,一場特大輸沙率的高含沙洪水導致整體關系線發(fā)生了較大偏離。同時,特大輸沙率的高含沙洪水較少且具有較強的偶然性,不具備統計學意義。前文中的輸沙率公式沒有考慮不同量級場次洪水在輸沙規(guī)律上的差異,將具有不同水沙輸移特性的場次洪水混在一起進行研究,導致高含沙洪水期累計沖淤量計算值與實測值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在率定下站與上站輸沙率關系式時,有必要對高含沙洪水進行分級,以便得到更加精準的輸沙率關系式。
3 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式修正
研究表明,場次洪水的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及二者的組合關系是影響黃河下游泥沙輸移的主要因素[8-9] 。同時,洪水漫灘和非漫灘對河道輸沙也有重要影響,因此也應該將高含沙洪水分為漫灘和非漫灘洪水進行研究。另外,來沙系數(S / Q)作為一個典型的水沙組合參數[10-11] ,廣泛應用于評估洪水期河道的沖淤強度。為了更好地揭示不同水沙條件下高含沙洪水在各河段的水沙輸移規(guī)律,利用小浪底站實測日均水沙數據,對1960—2021 年54 場高含沙洪水不同水沙搭配關系進行分析,計算小浪底站的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以及平均來沙系數,并對其進行分級,分析研究不同流量、不同含沙量以及不同來沙系數高含沙洪水各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另外,漫灘和非漫灘高含沙洪水的水沙輸移規(guī)律也不盡相同,需確定漫灘和非漫灘高含沙洪水的場次,并對高含沙洪水進行分級。按照上述4 種對高含沙洪水的分級方式,得出輸沙規(guī)律最好的一種分級方式,并分析計算河段累計沖淤量與實測累計沖淤量的擬合情況,最終確定此分級情況下的輸沙關系式。
3.1 按小浪底站平均流量分級
本節(jié)將1960—2021 年的54 場高含沙洪水按小浪底站平均流量劃分為4 個量級,分別為Q1 <2 000 m3 / s、2 000 m3 / s≤Q1<3 000 m3 / s、3 000 m3 / s≤Q1<4 000 m3 / s及Q1≥4 000 m3 / s。由于只有一場高含沙洪水的流量大于4 000 m3 / s,因此把3 000 m3 / s≤Q1 <4 000 m3 / s和Q1≥4 000 m3 / s 兩個量級合并為1 個量級,共劃分為3 個量級。
1)Q1 <2 000 m3 / s 的高含沙洪水。點繪黃河下游小花、花夾和夾高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5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均小于0.90,小花河段最大,為0.808 95,花夾和夾高河段確定系數均小于0.80。
2)2 000 m3 / s≤Q1 <3 000 m3 / s 的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6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均在0.90 之上,夾高河段確定系數最大,為0.919 17,說明隨著洪水沿程向下游的流動,越是處于下游河段,其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
3)Q1≥3 000 m3 / s 的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7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均在0.90 之上,且3 個河段比前面兩個流量級的確定系數都大,夾高河段依舊最大,說明該流量級下輸沙能力較強,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較好。
4)按流量分級總結。經過對高含沙洪水期小浪底站平均流量的分級,研究各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關系可以發(fā)現,當Q1 <2 000 m3 / s 時,3 個河段的確定系數均小于0.90; 當2 000 m3 / s ≤ Q1 <3 000 m3 / s時,3 個河段的確定系數均在0.90 之上,相關性優(yōu)于Q1<2 000 m3 / s;當Q1≥3 000 m3 / s 時,3 個河段確定系數又進一步增大,趨向于1,這說明隨著洪水向下游的流動,越是處于下游河段其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并且平均流量越大則下站輸沙能力越強,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也越好。
3.2 按小浪底站平均含沙量分級
將1960—2021 年的54 場高含沙洪水按小浪底站每場高含沙洪水平均含沙量劃分為3 個等級,分別為S1 <100 kg/ m3、100 kg/ m3≤S1<200 kg/ m3、S1≥200 kg/ m3。
1)S1 <100 kg/ m3的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8 所示。3個河段上下站輸沙率的確定系數均在0.95 之上,且花夾河段的確定系數接近于1,確定系數有沿程增大的趨勢,說明越是處于黃河下游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
2)100 kg/ m3≤S1 <200 kg/ m3的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9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較S1 <100 kg/ m3 級別的確定系數有明顯的下降,但確定系數仍存在沿程增大的趨勢。
3)S1≥200 kg/ m3 的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10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均在0.9 之上,且確定系數也呈沿程增大的趨勢,進一步說明越是處于黃河下游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
4)按含沙量分級總結。經過對高含沙洪水期小浪底站平均含沙量的分級,研究各河段上下站輸沙率的關系可以發(fā)現,當S1 <100 kg/ m3時,3 個河段的確定系數均在0. 95 之上, 趨近于1, 相關性很好; 當100 kg/ m3≤S1 <200 kg/ m3時,小花和花夾河段的確定系數都在0.80 以下;當S1 ≥200 kg/ m3 時,3 個河段確定系數均在0.90 之上,但相比S1 <100 kg/ m3的上下站輸沙率略小一點。以上3 個量級的確定系數均具有沿程增大的趨勢,這也說明隨著洪水向下游的流動,越是處于下游河段其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但不能說明平均含沙量越大河道輸沙能力越強。
3.3 按漫灘和非漫灘分級
將1960—2021 年的54 場高含沙洪水按照漫灘與否進行分級,從黃河下游實測大斷面成果看,高含沙洪水期下游游蕩河段發(fā)生漫灘的年份有1970 年、1971年、1973 年、1977 年、1988 年、1992 年、1994 年和1996年,共計發(fā)生8 場漫灘高含沙洪水,其余均為非漫灘高含沙洪水。
1)漫灘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11 所示。3 個河段的最大和最小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相差近0.1,小花河段確定系數略小一點,可以發(fā)現確定系數仍呈沿程增大的趨勢,說明越是處于黃河下游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
2)非漫灘高含沙洪水。點繪3 個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12 所示。3 個河段非漫灘高含沙洪水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較漫灘高含沙洪水整體呈下降趨勢。
3)按漫灘和非漫灘含沙洪水分級總結。通過將54 場高含沙洪水按照漫灘和非漫灘進行分級可以發(fā)現,發(fā)生漫灘高含沙洪水時只有花夾和夾高河段確定系數在0.9 以上,當發(fā)生非漫灘高含沙洪水時只有夾高河段確定系數大于0.9,并且相較于漫灘高含沙洪水,3 個河段確定系數均出現減小現象,即漫灘高含沙洪水的上下站輸沙率關系較好,這也說明漫灘高含沙洪水的輸沙能力強于非漫灘高含沙洪水的。
3.4 按小浪底站來沙系數分級
吳保生等[10] 將來沙系數作為典型水沙參數用來判斷下游河道沖淤情況。胡春宏[12] 認為,當S / Q >0.015 kg·s/ m6時河道發(fā)生淤積,當S/ Q<0.010 kg·s/ m6時河道發(fā)生沖刷,當0.010 kg·s/ m6≤S/ Q≤0.015 kg·s/ m6時河道大體上保持沖淤平衡。本文根據小浪底站平均來沙系數S / Q 和胡春宏的分級標準對1960—2021 年的54 場高含沙洪水進行分級,并分析各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
1)S / Q<0.010 kg·s/ m6 的高含沙洪水。點繪小花、花夾、夾高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13 所示。3 個河段的上下站輸沙率確定系數均在0.90 以上,花夾河段的確定系數更是在0.95 以上,說明按來沙系數分級的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相關性較好。
2)0.010 kg·s/ m6≤S / Q≤0.015 kg·s/ m6的高含沙洪水。54 場高含沙洪水小浪底站平均來沙系數沒有在0.010 kg·s/ m6 ≤S / Q≤0.015 kg·s/ m6 區(qū)間的,這說明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游蕩河段大體上不存在沖淤平衡的情況。
3)S / Q>0.015 kg·s/ m6的高含沙洪水。點繪各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之間的關系,如圖14 所示。3 個河段的確定系數都在0.90 之上,確定系數呈沿程增大的趨勢,進一步說明越是處于黃河下游河段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關系越好。
4)按來沙系數分級總結。將54 場高含沙洪水按平均來沙系數進行分級發(fā)現,輸沙率擬合公式的確定系數均在0.90 以上。總體來看,按來沙系數分級的情況下,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的相關性較好。
3.5 來沙系數分級輸沙率公式合理性檢驗
來沙系數分級累計沖淤過程與實測及輸沙率公式計算沖淤過程對比見圖15,可以發(fā)現,來沙系數分級計算的累計沖淤量與實測累計沖淤量貼合較好,極大地提高了分級前輸沙率公式計算的累計沖淤量的精確度。因此,按來沙系數分級得到的輸沙關系式能夠有效地反映黃河下游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的輸沙過程,按來沙系數對高含沙洪水分級,在已知小浪底站場次高含沙洪水水沙條件時,可快速沿程逐站遞推出花園口、夾河灘及高村站高含沙洪水期的輸沙率,從而計算出游蕩河段高含沙洪水期的河段沖淤量。
根據小浪底站來沙系數分級,計算小花、花園口—高村(花高)河段高含沙洪水期的累計沖淤過程,圖16是兩個河段計算累計沖淤量與實測累計沖淤量對比,可以看出,小花、花高河段計算的累計沖淤過程很好地貼合了實測累計沖淤過程,這說明通過來沙系數分級極大地提高了河段沖淤量的計算精確度,通過來沙系數分級得到的輸沙率關系式的確定系數都在0.90 以上,這也進一步說明按照來沙系數分級的輸沙率公式能夠很好地模擬沖淤過程。
4 結論
根據1960—2021 年54 場高含沙洪水的實測水沙資料,分析場次高含沙洪水的下站輸沙率與上站流量、含沙量、輸沙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輸沙率關系式,系統地研究了高含沙洪水的輸沙規(guī)律,其中下站輸沙率與上站輸沙率相關性最強,然后對其進行關系式合理性檢驗,發(fā)現進一步以來沙系數分級得到的輸沙率公式能夠很好地模擬沖淤過程,極大地提高了河段沖淤量計算的精確度,能夠很好地反映高含沙洪水期黃河下游游蕩河段的輸沙規(guī)律。
以小浪底水文站為黃河下游游蕩河段的進口控制水文站,根據按來沙系數分級所求的輸沙率關系式,推求花園口、夾河灘、高村站的輸沙率,從而計算小花河段、花夾河段、夾高河段的沖淤量。來沙系數分級所得的輸沙率公式能夠很好地預測不同量級高含沙洪水的各河段的沖淤量。
參考文獻:
[1] 趙業(yè)安,周文浩,費祥俊,等.黃河下游河道演變基本規(guī)律[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8:15-23.
[2] 郭慶超,鄭釗,陸琴,等.黃河下游河道洪水期輸沙規(guī)律研究[J].人民黃河,2019,41(10):64-69.
[3] 張瑞瑾.河流泥沙動力學[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2:34-43.
[4] 趙文林.黃河泥沙[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67-71.
[5] 齊璞,余欣,孫贊盈,等.黃河高含沙水流的高效輸沙特性形成機理(黃河下游河道存在巨大的輸沙潛力)[J].泥沙研究,2008,33(4):74-81.
[6] 惠遇甲,李義天,胡春宏,等.高含沙水流紊動結構和非均勻沙運動規(guī)律的研究[M].武漢: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出版社,2000:43-48.
[7] 申冠卿,張原鋒,尚紅霞.黃河下游河道對洪水的響應機理與泥沙輸移規(guī)律[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8:77-82.
[8] 許炯心.黃河下游洪水的輸沙效率及其與水沙組合和河床形態(tài)的關系[J].泥沙研究,2009,34(4):45-50.
[9] 許炯心,張歐陽.黃河下游游蕩段河床調整對于水沙組合的復雜響應[J].地理學報,2000,55(3):274-280.
[10] 吳保生,申冠卿.來沙系數物理意義的探討[J].人民黃河,2008,30(4):15-16.
[11] 費祥俊,吳保生.黃河下游高含沙洪水水庫調控技術研究[J].泥沙研究,2015,40(2):1-8.
[12] 胡春宏.黃河水沙過程變異及河道的復雜響應[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91-94.
【責任編輯 張 帥】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U224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