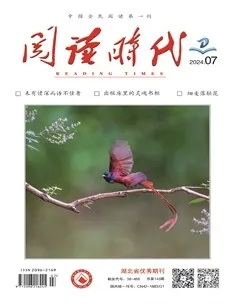刀鋒難躲,好在玫瑰真實
在一家裝飾花哨的餐館里,一位作家背靠紅棉絨的椅子,靜靜地聆聽;他的對面是位英俊的年輕人,聲音仿若天籟,語氣自然,似拉家常。
“按照吠陀經義,‘真我’(他們稱為阿特曼,我們稱為靈魂)不同于肉體和感覺,不同于頭腦和智慧,是‘無限‘的一個組成部分。鑒于‘無限’是無邊無際的,沒有‘部分’之說,所以‘真我’實為‘無限’之本身……它就像海里蒸發起來的一滴水,在一場雨后墜進水潭,然后流入溪澗,進入江河,通過險峻的峽谷和廣袤的平原,迂回曲折,擊石穿林,最后抵達它的發源地——無垠的大海。”
“依我之見,一個人最高的理想應該是自我完善。”
《刀鋒》的主人公拉里如是說。在毛姆這部極具東方神秘色彩的小說中,一位再普通不過的美國少年,受到死亡的震撼,踏上了尋找人生意義的漫長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飛行員的他親眼目睹一位親密的戰友為救他而死去。這讓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人生的價值在哪里?難道人生是一種愚蠢的、盲目的、悲慘的過程嗎?”
人一旦意識到死亡的偶然與生命的短促,便會驟然掙脫出世俗既定的軌道,從渾渾噩噩中猛然覺醒,“向死而生”。
首先他能想到的方法是讀書,從書本中尋找答案。于是拉里離開愛人伊莎貝爾,前往巴黎,先是租住在巴黎大學和國家圖書館邊的陋室里,將大把的時間擲在讀書上,享受追求知識與真理所帶來的純粹的快樂;之后,他下礦挖煤,又在農場工作了一段時間。也正是這時,他對神秘主義萌生了興趣。
他在波恩結識了一位本篤會(亦譯為“本尼狄克派”,天主教隱修院修會)的會士,并接受其邀請前往修道院住了三個月,然而他對許多教義心生懷疑。后來,拉里在印度受到當地宗教文化的吸引,拜在一位靜修者門下。
很難想象一位西方人會選擇接受印度教的教義,但拉里對宗教信仰的理解確有一種令人嘆服的尖銳。僅僅兩年的時光,他便大徹大悟,體會到了醍醐灌頂、超然物外的極樂。于是他離開印度,回到美國,立志過清修者的生活,并以其自身感化他人。這也就有了文章開頭所描繪的那一幕。
扉頁上有一句引詩:“尖利的刀鋒很難躲過;所以智者言救贖之路荊棘遍布。”關于這句詩,頗有些翻譯上的爭議,也有人認為其本義應當是“尋找自我救贖的道路如同刀鋒般鋒利難行”。
兩者都不無道理。若以第一種方式理解,書中不同的角色各有其不得不面對的“刀鋒”。對于拉里,他為追尋縹緲的人生意義舍棄了愛情,又經歷了生理上的疲憊與辛勞,可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書中的另兩個重要的人物伊莎貝爾和艾略特,前者受“情欲”的驅使陷害朋友索菲,親手將她從尋求救贖的掙扎中拽回“地獄”;后者一生看不破“名譽”二字,將體面和上流社會的認可作為畢生之追求,至死仍為一張宴會的請柬耿耿于懷。意欲躲過刀鋒,談何容易?
或依第二種譯法,通往救贖的道路便如同尼采筆下的繩索,走過去、停在中途都危險重重。刀鋒尖銳,狹窄難行,亦難站立。選擇踏上這條狹窄的路,便不得不放棄本可擁有的一切。世俗的誘惑是難以戰勝的,拉里最終通過了刀鋒,索菲卻在半途滑落——她還是重拾了酗酒、吸大麻的舊習。
“救贖之路荊棘遍布”,無論是優渥的生活抑或名流的吹捧,顯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救贖,然而總有人身陷其中深信不疑。伊莎貝爾和艾略特都未能找到“我”。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救贖,卻無法從已有的結論中找到滿意的答案——終極問題的答案是個體化的,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去尋找。
年輕的毛姆也曾潛心于哲學著作,試圖尋找那本恰和他志趣相投、能解答他所有困惑的書,然而沒有任何一種已有的哲學體系能夠說服他。于是他終于意識到:或許能夠說服個人的哲學體系也只屬于個人自己。“一個人持怎樣的哲學觀點,取決于他是怎樣的人。”
“塵世間的完滿都是暫時的,只有達到‘無窮’的境界,才可獲得持久的幸福。不過,時間的無窮并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不能使善更加善,也不能使白顏色更加白。如果說玫瑰花在中午不再嬌艷,它的美在清晨時卻是真實的。”人生的意義或還未有答案,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夠為生命中溫柔的瞬間而心生悸動。
毛姆自身對于人生意義也有他明確的看法。毛姆的另一本更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月亮與六便士》,以保羅·高更為原型,塑造了一位毅然出走的畫家形象:證券經紀人查爾斯為了畫畫拋妻棄子,流浪到塔希提島,忍受著貧窮和病痛,對于藝術的追求狂熱得近乎不可理喻。
兩部作品都對人生意義作出了探討,但也有明顯的區別。“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月亮與六便士》中的查爾斯所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理想的實現,其所作所為是一種決絕的、掙破一切世俗枷鎖的出世之舉。在《刀鋒》之中,拉里所尋找的則是更為抽象寬泛的哲學命題的答案,并在“大徹大悟”后選擇“普度眾生”,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影響他人,給予他人內心的寧靜與平和。
若將查爾斯比作中國古代的“賢人”,拉里無疑擁有“圣人”的胸懷。無論從人物的建構還是探討的范疇來看,《刀鋒》都更為成熟。自然,這與毛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有很大的關聯,《刀鋒》的創作是在1944年,誕生于《月亮與六便士》問世的25年后。
印度教的宗義和神秘色彩更是為本書增添了一抹亮色。但《刀鋒》中印度教觀念的長篇論述,也使得這部作品飽受爭議。事實上,毛姆本人也承認他對于東方神秘主義并不完全了解。
好在我們讀《刀鋒》,也并不期望找到什么最終的答案。或許這也正是我們讀毛姆的意義之所在:我們像他一樣,一邊走著自己的荊棘路,一邊從他人的人生中尋找意義,追問著千百年來仍未解決的問題,至死方休。
(源自“北大青年”,有刪節)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