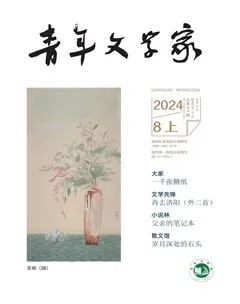因心會道,循而行之


《論語·陽貨》載:“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此章所載,堪當孔子詩論的核心觀點,被后世評價為“《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劉瑾《詩傳通釋》)。
回溯“興觀群怨”諸多訓釋,粗淺歸為兩大淵藪:原初“孔鄭之注”與“皇侃義疏”,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詩”的涵義籠罩著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的朦朧蕭索,對“興觀群怨”的訓釋僅為字面意義的疏通,而未考慮各義項之間的邏輯關聯;而后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興觀群怨”說歷經悠悠千載以至北宋。此時,二程、張載、范氏、謝氏諸論應運而生,而“興觀群怨”的內涵由混沌迷蒙走向乍見之明,反復周悉之下亦有佳論生成,直至南宋,朱熹慎思“詩”之本質,取諸家所長,棄“未安之說”,最終于《四書集注》中落下權威之論。然而,“四語”絕非“一意”,融合儒家詩教傳統,不難窺見其間“因心以會道”的“正人之風”,而宋人黃干“觀己得失”(劉瑾《詩傳通釋》)一說切中夫子之義,而后“履而踐之”的身體力行,方可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情懷道夫先路。縱觀“興觀群怨”論諸說,其間雖往復百折,而條達舒暢,無所間斷。萬事之任,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是故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亦可端正今世為文之風。
一、“興觀群怨”的學說溯源
“興觀群怨”的最早釋義,起源于三國何晏引用的孔安國、鄭玄二家著書。孔安國稱:“興,引譬連類也;群,群居相切磋也;怨,怨刺上政也。”鄭玄則稱:“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南朝皇侃沿襲孔、鄭二說,而后疏“興觀群怨”為:“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群’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何晏、邢昺《論語集解義疏》)。如此釋義,僅是訓詁,非為文論,均是疏通“興觀群怨”的字面含義,卻忽視了更為關鍵的邏輯關聯。譬如,把“興”理解成學《詩》“可令人能為譬喻”,指稱作詩的表現手法,應為詩歌的功用論;把“觀”看作“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就導向了詩歌本體論;將“群”解釋為“朋友之道,可以群居”,那么談論的是詩歌的社交功能;而“怨”被認為是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則指代的是詩歌“美刺”的政治傳統。據此,不難發現,“興觀群怨”諸說并未在同一個邏輯鏈上鋪展開,四義間的邏輯聯系并未引起當時學者重視。
直至南宋,時賢未拘泥于先論,故有萬種思量,多方開解。朱熹《論語精義》載二程、橫渠、范氏、呂氏、謝氏、楊氏、尹氏八家論調,而朱熹并不全盤肯定,他指稱:“可以興”“可以怨”“可以怨”,諸說皆得,而“可以觀”,則諸說皆未安。“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而張子以為觀眾人之志,范氏以為觀眾人之情,呂氏以為察事變,楊氏以為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賾,皆各得其一偏。而謝、尹氏以為無所底滯,而閱理自明,則是所以可觀者不在于《詩》,而在于學《詩》之人明理之后也,也其失遠矣。”(朱熹《四書或問》)于是乎,朱熹去粗取精,導夫先路,于《四書集注》定下權威之論:“‘《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緒余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也。”
雖為權威之論,亦有撼樹蜉蝣,論量書生之意味。朱熹自稱“可以觀”諸說皆有未安之感,從而反復推敲《四書集注》之調,“興”感發意志,“群”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三者均為《詩三百》的功用論,均能落于學《詩》者情意品格之教化,而“觀”卻釋為“考見得失”,橫逸旁出,按朱子之說“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論述主體是《詩經》,而非學詩者,即借由《詩三百》,來見證其中所記載的先民治亂得失。換言之,“興群怨”為詩歌功用論,“觀”為詩歌本體論。由此可見,朱子之說仍然未安,如其學生黃干之言:“‘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言,謂考究其人之得失也”。無可奈何,朱子無以更改“觀”諸說窘境。而黃干又稱:“以為觀已得失,亦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后四語皆一意也”(劉瑾《詩傳通釋》)。由此可見,朱子的“四語”并非“一意”,亦不符合詩歌功用論一以貫之的思維邏輯,為彌補朱熹的論述罅漏,盡管黃干多有糾正補缺,但是經由《詩》實現“觀己之得失”的教育理想卻缺乏更為深入的系統釋義。
二、“興觀群怨”的功用導向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推求“興觀群怨”邏輯本質,應當把握儒家“詩教”傳統,實踐儒家“知行”理念,方能遵從史實、破除虛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文”,即《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夫子崇“文”,而不以“學文”為一,以踐行高于學文,“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文非惟求知,而是學以致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由此可知,孔子所求無非德行,禮樂之養與忠孝之行。夫子之教,品格為先,次為踐行,最次為“王之遺文”。因此,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生、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故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后,自本而末,“四教”與“四科”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教融合文化熏陶與人格培養,孔子所云“興觀群怨”,并非詩歌創作論或本體論,而是詩歌功用論。
通乎詩教背景,方可穿花尋路,直入白云深處。若按朱熹之解,“觀”為“考見得失”,便把學習《詩經》用于知識求索,而非指向磨礪道德與培養人格,這無疑不合于孔夫子的知行教育觀。相反,若是按照黃干釋義,將“觀”理解為“觀已之得失”,便將《詩經》用于砥礪人格,顯然夫子樂于觀之。非唯黃干作此解,宋代戴溪云:“通乎《詩》,則明乎人情;識乎物理,可以感發善心;察觀世變,以群居不亂雖有怨誹而不至于已甚。”(《石鼓論語答問》)由個人修養提升入手,只是“察觀世變”之意尚不明確。明代蔡清亦云:“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群’;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四書蒙引》)根據蔡清的論述,進一步說明“興觀群怨”四義都指向自身,應當為“己事”。因此,“考見得失”可以推理為“觀己之得失”。學《詩》若能“起己之善意”“觀己之得失”,使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便足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忠孝兩全,水到渠成。此為“興觀群怨”總體邏輯,而《詩三百》中的博物學,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表述,則是學《詩》余利,無非補充說明,當為讀者笑納。
三、“興觀群怨”的理論價值
詩學之畔,積石如玉,列松如翠。茫茫詩海,“詩言志”的論述,不僅衍生出了“千古詩教之源”,也為古代文論奠定了頂天立地的“開山綱領”。而后,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成為千古“詩教基石”,也為我國詩論的發展“道夫先路”。兩者一為詩歌本體論,令學《詩》者知詩歌從何而來;一為詩歌功用論,令學《詩》者知詩歌何路可去,“詩言志”與“興觀群怨”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唯有比翼連篇,并以創作論之好風,方能凌萬里長空,看座下山河。
“興”“觀”“群”“怨”雖指向各異,但各具理論價值。詩“可以興”,導向詩歌的情感皈依。無論“起人之善意”,抑或“感發志意”,《詩》中一詞一句,均為情感凝結,且此情此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者誦讀詩歌,涵泳其中,便會為之感動,引起共鳴,滋養纏綿情意。正如謝良佐所言:“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此處“可以興”即為引發情感共鳴。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觀者受“詩”啟發,方能進一步發揮詩歌的言情功用,是故“興”為詩用之基,亦是學“詩”之基。
詩“可以觀”,指出詩歌能夠認知自我。“觀”應當釋為“觀已之得失”,以《詩三百》為明鏡,可照射“治亂得失之變,人情物態之微”,從而三省吾身,涵養松柏品格。“觀”由東周的“詩言志”多加延伸,借所賦詩句,溫柔敦厚地表達其思想傾向。史書中多載《詩經》獨特的外交功能,即從“詩言志”的概念衍生而來,譬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班固《漢書·藝文志》)。因此,“觀”應為“《詩》之中美刺并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于此有惕然感動者,故可以觀”(陳廷敬《日講四書解義》),這般表述既貼合了“詩言志”的“詩教之源”與歷史事實,也與孔夫子的教育觀形成了真理的回扣。
詩“可以群”,說明學《詩》有利于人際交往。《詩》能夠感發善意,修養道德,完善個體品格,更進一步使得群居社交走向“和而不流”,故“可以群”,即為張載所云“蓋不為邪,所以可群居”,當人性之“善”戰勝人性之“惡”,也就激發出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社會必然趨于團結穩定的和諧狀態。至于“興”“觀”“群”三者之間的關聯,我們不難發現,“可以興”“可以觀”是“可以群”的個體基礎,而“可以群”是“可以興”“可以觀”符合邏輯發展的群體表現。也就是說,先有“詩”“起己之善意”“觀己之得失”的個體功用,方能達到“敘述情好,每于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陳廷敬《日講四書解義》)的社會教化功效。最終,“和而不流”實現群體的穩定和諧。
而詩“可以怨”,則表明了“詩”獨有的政治功能。詩“可以怨”歷來指向明確,如程頤所說“詩‘可以怨’,譏、刺皆是也”,謝良佐所云“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足以見得,“怨”是中國古代人民溫良的反抗、美善的指正,為大一統秩序的穩定和諧,為此生家國天下的安好悠然,是“溫柔敦厚”“怨而不怒”,而非純粹金剛怒目的發泄或反叛。一切都是因為“可以怨”基于已有的“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詩》既然已經“起己之善意”“觀己之得失”,并且使得社會“和而不流”,于是乎,包含著“美刺”政治意義的“怨”自然也就“怨而不怒,優游不迫”。“興觀群怨”自獨善其身通往“兼濟天下”,由此“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忠孝兩全,圓融自適。大天下的“怨”,正是對小社會“群”的向前一步。由此,孔子“興觀群怨”的詩論,終至邏輯一貫而無可置疑。
觀儒家文論“興觀群怨”之辨,可謂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無論兩漢時期“引譬連類”的詩歌創作論,抑或兩宋時期“情發于中而形于言”的詩歌本體論,還是南宋至元明清“觀己之得失”的詩歌功用論,“興觀群怨”諸說皆寄寓了古人“玉鑒瓊田三萬頃”的風月無邊與“盡挹西江,細斟北斗”的肝肺冰雪。以詩教為導,悠然心會,“興觀群怨”則歸向“為己之學”。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范曄曰:“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而“穩泛滄浪空闊”的悠然自明,來源“因心會道,循而行之”為己的方寸之隅,通向“事父事君,多識萬物”,朝向他者的濟世之境,而我輩察之古視之往,定能端正今時與來日為文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