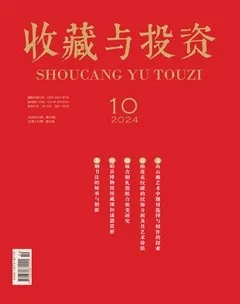唐宋黃山竦口窯的源流考
摘要:竦口窯位于安徽省歙縣,是安徽南部地區的民間窯廠。1985年歙縣文化局和博物館在文物普查時發現其生產青瓷,且造型多樣,根據其造型特點和紋飾,將其生產時間定在唐代中晚期到南宋早期。關于竦口窯的源流問題,官方沒有進行詳細說明。本文以近年出土的標本為基礎,結合近年專家學者所編的文獻材料,實地走訪窯址,并將竦口窯與周邊窯口對比,淺談唐宋時期黃山竦口窯的源流問題。
關鍵詞:竦口窯;風格特征;源流;其他窯口
一、窯址概況和調查情況
竦口窯,窯址位于中國安徽省黃山市歙縣桂林鄉竦口村東南150米左右,距歙縣縣城東北部大約10公里。窯址位于二條河道交匯處,因靠近河流,運輸瓷器便利,且木材燃料運輸方便。窯址自北往南傾斜,窯身全長20~24米[1]。瓷窯依山而建成,據考古所調查,均屬于竦口窯。這些不同的窯址總占地面積可能有數千平方米。相傳竦口原來有數百窯,全部由程姓族人所開設燒造,后因瘟疫和戰爭才慢慢衰敗。目前,對竦口窯的調查只發現了南宋的瓷片,尚未找到南宋以后的相關實物標本,因此推測竦口窯從南宋開始衰落。

歙縣竦口窯(圖1)為黃山市的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筆者和導師一起通過走訪發現的竦口窯窯址多位于河道邊。當地擁有豐富的高嶺土,瓷石以及釉料等,使得竦口窯燒造時間跨度長,從唐代中晚期到南宋前期。在調查中發現竦口窯產品種類豐富,既有碗、盤、壺、罐等生活用具,也有束口盞、束口缽等文人飲茶器。
二、竦口窯瓷器源流考
對于竦口窯的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恢復竦口窯整體風貌之前,筆者認為確定竦口窯的源流問題是非常有必要的。
竦口窯與唐代宣州窯青釉、五代到宋代越窯制品因地理位置等原因,釉色、釉相都非常接近,有很深的工藝淵源。甚至竦口窯還與地區窯口或有所關聯。
(一)從越窯到竦口窯
竦口窯和越窯二者具有較高的相似度,筆者將從器物本身、燒造工藝以及人員流動等以下方面探討二者之間的聯系。
首先從兩者的器物本身來說,竦口窯的產品有青釉瓷和黃綠釉以及醬褐色釉瓷之分,目前根據現有采集的標本看:唐代時期黃綠釉以及醬褐色釉瓷占總窯口數量的80%。五代到北宋時期青釉瓷占整體數量的70%~80%。青釉瓷的釉水細膩,整體滿釉且底部施釉;黃綠釉、醬褐色釉瓷的釉水較粗,胎釉結合不緊密。醬褐釉者,則多為日用器,釉水大部分施到整體的三分之二處,且底部露胎,有火石紅和旋紋,胎釉結合不夠緊密,易出現剝釉現象。竦口窯大部分為單色,但也存在點褐彩,即在青釉上出現褐彩的現象,而青釉點褐彩現象最早便出現在三國時期吳國所管轄的越窯內。晚唐到五代時期,越窯釉水整體呈青釉質感,胎釉結合緊密,通體滿釉。越窯的釉水和竦口窯中的青釉瓷的釉水幾乎接近。可以看出竦口窯中的青釉瓷部分受越窯影響較大,唐代時期由于竦口窯處于起步階段,釉色偏醬褐色和黃綠色,五代到北宋時期,隨著窯業的發展以及同時期越窯走向鼎盛,竦口窯學習越窯,不斷提升其釉水質量,使得竦口窯的釉水呈現出青綠釉的效果。
竦口窯瓷器有精細瓷和厚胎粗瓷之分。北宋時期竦口窯多精細瓷,瓷土經過精細的淘洗,胎質堅實細膩,為香灰胎,顏色偏灰白色,底足露胎部分呈深褐色和深黑色。五代到北宋時期越窯,胎土同樣細膩,通過比較發現竦口窯的瓷胎相對于越窯露胎部分黑的程度更高,但兩者胎體瓷土差別微弱。究其原因,竦口窯和越窯雖分別處在兩個省份,但二者緯度一致,且同屬于東南丘陵,兩地瓷土較為接近,竦口窯瓷胎更黑,因當地瓷土的含鐵量較越窯偏高所致。
從器型上看,越窯器中多有仿金銀器之作,竦口窯從器型上看,產品以碗、碟、盤、杯、罐、壺為主(圖2),還有盞托、燈盞、束口盞等器型。其中竦口窯的產品又可以分精細者和粗糙者,精細瓷中有一部分仿金銀器造型,如葵口碗、持壺、花口洗等。因越窯地處浙江沿海地區,寧波和紹興屬于港口城市,對外貿易發達,和西方文化貿易交流較為頻繁,西方在越窯多有定制和外銷等現象,所以可以看出越窯器型有部分受到西方金銀器的影響,而竦口窯瓷器則直接受到越窯器型的影響。
從燒造工藝上看,竦口窯在唐代基本上采用疊置裸燒,支釘粗大。五代到宋,支釘的形狀開始變得細小,支釘數也多為4~13個不等。在北宋有托珠疊燒和墊圈疊燒。墊圈疊燒是匣缽單件仰燒,提高了單個質量和成品率。匣缽分為漏斗匣缽和筒式匣缽,其中漏斗式匣缽以碗碟盤等臥件為主,筒式匣缽以罐壺等立件為主[2]。越窯在瓷器燒造工藝上,從唐代到北宋時期一直采用小支釘墊燒和匣缽燒造,并且從未間斷。因此可以看出燒造工藝的傳播具有相對滯后性,唐代竦口窯未能及時吸收越窯的先進技術,到了五代和北宋時期,開始摒棄較為落后的疊置裸燒,學習越窯的托珠疊燒和墊圈疊燒以及使用匣缽[3]。
從人員流動和技術傳播角度看,竦口窯位于安徽東南部的歙縣,毗鄰浙江。越窯位于浙江的寧波和紹興,中心窯口則處于慈溪上林湖[4]。兩個窯口相距約兩百公里,且有河流相連接。竦口窯處在揚之河與雙竦河的交匯處,揚之河作為新安江的支流,由新安江匯入錢塘江,錢塘江流經紹興、寧波、上虞等越窯產地,進而最終匯入東海。古代窯口的分布都位于河流的附近,既有港口方便運輸,又有水資源進行原料加工,方便木材燃料的采伐和輸送。在古代,人員流通在江南地區基本以水運為主,竦口窯工匠既可以通過新安江一線直接前往越窯學習,也方便越窯窯工將技藝傳到竦口窯。
通過兩個窯口的器物和燒造工藝的分析,人們可以看出在五代到宋代時期,竦口窯積極學習和吸收越窯的燒造技術,燒出了一批和越窯質量不分上下的青釉瓷器(圖3),以至于許多人稱竦口窯為“安徽越窯”。
(二)從宣州窯到竦口窯
宣州窯作為皖南地區的窯廠群,包括了諸多窯口,如繁昌、東門渡、小竹園等,宣州窯的窯工既有北方因避戰亂而南下制瓷者,也有皖南本土制瓷者,以至于宣州窯器物的整體風貌有北方瓷的粗獷,也有南方瓷的精致、小巧。在唐代,宣州窯的粗獷風格在竦口窯中也有出現,故而筆者將二者相比較,并進行探討,以找出兩者之間的聯系。
宣州窯的早期窯址為唐代涇縣的琴溪窯、蕪湖的東門渡窯。他們的瓷器釉色以黃綠釉和醬黃釉為主,釉水相對較薄,胎釉結合不夠緊密,釉水為整體的三分之二左右,器身釉面開片較深,且大部分釉面存在土沁現象,器物口沿有脫釉,有的器物腹部常有鼓釉現象,這與唐代竦口窯存在極大的相似性。因兩者的釉料均來自皖南本地,釉料較薄導致開片和土沁現象嚴重。宣州窯存在青釉褐彩瓷,其中褐彩能夠進行彩繪花草紋,而竦口窯只存在點褐彩現象。
在胎質上,宣州窯和竦口窯兩地相隔較近,瓷土幾乎一致。唐代晚期兩個窯口的瓷土淘洗都相對粗糙,瓷質內存在雜質,胎體都為灰白色,底足的刮削痕與旋紋明顯。
在器型上,唐代宣州窯和竦口窯生產的多都為日用器,如碗、盤、壺、雙系瓶、罐等,且碗盤等器物少見圈足器,多為平底刮削[5]。宣州窯、竦口窯生產了少數禮樂器,如宣州窯出土的唐代腰鼓、竦口窯出土的鼓槌。可見兩個窯口生產的器型都較為豐富。但是通過對兩個窯口唐代晚期出土器型的比較,發現宣州窯生產的器型比竦口窯豐富,如宣州窯生產的長流刻畫花持壺、青釉蓋罐、瓜棱罐等(圖4)。宣州窯除了一般民間日用器外,還出土了帶有官字款的壺。由此可見,宣州窯在晚唐時期曾為官方進貢過瓷器。可見當時宣州窯的影響力之大,宣州窯器型種類繁多,而竦口窯作為當地的民間窯廠則積極學習宣州窯的器型樣式,最終在晚唐時期,人們在竦口窯身上看到了宣州窯器物的身影。
在燒制工藝上,唐代宣州窯和竦口窯都會采用龍窯燒造,因都是皖南山地地形,窯址依山而建,利用坡度增加燒造火力和提高產品產量。晚唐時期,二者窯具都相對簡單,一般采用疊置裸燒。器物內部是四個支釘支燒,支釘較為粗大,將疊燒的器物放在利頭上,明火燒制,兩者燒造工藝來說幾乎一樣。
唐末宣州窯正處于由官窯向民窯轉變的時期[6]。竦口窯作為皖南地區的民間窯廠,積極學習宣州窯的燒造工藝。兩地之間相距僅一百多公里,既有水運,也有陸運。竦口窯地處竦口村,是雙竦河與揚之河交匯處,兩河均發源于宣城市;陸運上櫸根嶺是歙州到宣州的古道,這條古道是宣州窯和竦口窯相互學習借鑒的橋梁樞紐。水陸交通的便利,使得兩地之間交流頻繁。宣州窯作為晚唐到五代前期的官窯,自然也就成為周邊地區窯口所學習的榜樣。

三、結語
唐代到北宋時期安徽歙縣的竦口窯,雖然不及宋代五大名窯或者八大窯系有耀眼的光環,但是他對當時瓷業體系的豐富和完善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于唐代吸收學習宣州窯制瓷工藝,于宋代學習越窯工藝,并在瓷業高峰的宋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輻射帶動周邊窯口的形成和發展,成為安徽窯業一朵璀璨的奇葩。
作者簡介
程釗睿,男,漢族,安徽黃山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學。
參考文獻
[1]高一龍,賈慶元.安徽歙縣竦口窯調查[J].考古,1988(12):1142-1143.
[2]洪兵.唐宋歙州竦口窯調研報告[J].陶瓷科學與藝術,2023(3):105-107.
[3]屠宗毅.越窯青瓷燒制技藝研究[J].陶瓷科學與藝術,2024(7):90-91.
[4]盛海堯.越窯青瓷,千年秘色—越窯青瓷的裝燒工藝探究[J].陶瓷科學與藝術,2024(7):100-101.
[5]王丹丹,劉東.宣州窯瓷器初探[J].文物春秋,2019(3):48-53.
[6]李廣寧,董家驥.皖南瓷器考古的幾點思索[J].東南文化,1991(2):20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