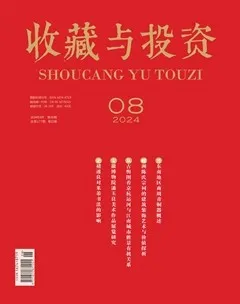西周金文《毛公鼎銘》與《虢季子白盤銘》藝術比較研究
摘要:金文是書法藝術的瑰寶,《毛公鼎銘》《虢季子白盤銘》作為西周金文經典,在藝術上極具美學價值,書法家多從中汲取靈感。《毛公鼎銘》是西周金文的廟堂經典,銘文數量位居青銅器之首。《虢季子白盤銘》是金文向小篆演變時期的代表,為歷代學者追捧。二者雖都處于西周晚期,且都于寶雞出土,所呈現的美感卻不盡相同。本文通過圖像對比的方法,探求二者書風之間的異同,以期對金文的書法創作提供借鑒。
關鍵詞:西周金文;《毛公鼎銘》;《虢季子白盤銘》
西周金文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毛公鼎》與《虢季子白盤》都為寶雞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銅器,且內部都鑄有銘文。《毛公鼎銘》與《虢季子白盤銘》二者的線條都有古拙質樸的金文內涵,結體都不囿于時代造型的拘束,大膽地因地制宜,有所變化,以重心的挪移和形體的融合變通打造出超脫于時代的神采意趣[1]。筆者通過對《毛公鼎銘》與《虢季子白盤銘》的比較研究,探討西周晚期金文的不同風貌,以期對金文的創作實踐有所啟發。
一、線條的“圓渾沉雄”與“豐力多筋”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時期的重器,因其為毛公所作而得名。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曾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2]《虢季子白盤銘》線條溫潤灑脫,文字結體嚴整勻稱,卻已漸有籀書之姿,《石鼓文》《秦公簋》字體的特點皆可從此處尋求源頭,可謂籀書之源。對比二者的線條可以看出,《毛公鼎銘》起筆圓多方少,筆畫多圓厚凝練,線條古樸沉雄,剛柔并濟,具有廟堂經典的美感。《虢季子白盤銘》筆勢均勻,內含筋骨,方圓粗細變化豐富而細膩,在典雅雄闊的同時又有秦小篆爽朗簡凈的意味。從用筆分析上看,二者相似之形中蘊含演進趨勢的不同。
《毛公鼎銘》線條的質感是多重樣式的,有渾厚、有靈動、有質樸、有婉約,而不同質感的線條則是由起筆、收筆以及運筆過程中的直曲所造成的。其用筆變化極為豐富,起筆時輕時重,運筆時轉時折,錯落有致,收筆有尖有圓,筆畫與筆畫之間,字與字之間都有輕重粗細的變化,給人以內斂含蓄、婉轉通暢的美感,詮釋了西周金文由繁雜、粗率、嚴謹肅整到圓熟精到的衍變和發展軌跡[3]。
《虢季子白盤銘》則不然,其形以瘦勁為主,卻有濃厚的質拙氣息。筆畫圓潤,起筆藏鋒,收筆有時以“頓尖狀”呈現,自然萬千,凝重中流露出優美瀟灑的韻致,字跡出于大篆而與大篆不完全相同,已和后來的秦系篆書非常接近。如果說《毛公鼎銘》是金文篆法廟堂之經典,《虢季子白盤銘》則是在渾厚金文基礎之上的新風。
以圖1中的“夕”字為例,“夕”字在《毛公鼎銘》與《虢季子白盤銘》中線條彎曲程度有很大不同。《毛公鼎銘》中更為彎曲,呈半弧狀,《虢季子白盤銘》中則為方直狀線條;“子”字上半部分在《毛公鼎銘》中以“口狀”來表達,在《虢季子白盤銘》中則以“三角狀”進行減形留勢,以方直線條代替圓曲線條,避免書寫復雜化,展現清直延展意味。《毛公鼎銘》線條剛柔相濟,有時又有肥筆以及點團華飾其形,形式美變得純粹,用筆凝重暢快,達到頂峰。《虢季子白盤銘》則成為一種單純由線條組合而成的符號結構,裝飾意味減少,行款疏朗暢然,起筆處有明顯的停頓動作,收筆處又作提筆出鋒,顯示出譎皇茂雋、細勁質樸的風貌。
二、結體的“渾厚內斂”與“舒展秀麗”
對比二者的結體特點,《毛公鼎銘》內放外收,以圓筆為主,瘦勁方長,勻稱和諧,儀態萬千,甚至有一部分字形長寬之間的比例已經近似于黃金分割,將西周金文渾厚內斂的美感闡發。《虢季子白盤銘》以方筆為主,柔勁細健,古拙質樸,結構疏密,欹側的變化呈現出舒展細勁的神采,這可能與當時對于文字審美的意識日趨自覺有關。

《毛公鼎銘》形體已不再像早期一般可以任意地變換位置,而是逐漸規范,結構穩定而嚴謹,整體取縱勢,注重對長短、欹正、大小、縱橫、穿插的應用,不過分突出某一方面。左右結構的字,或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在方長的體形中,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錯落欹側,參差變化,疏密避讓穿插其中。
《虢季子白盤銘》在展現縱長體式的同時,內部結構穩固收緊排列,外部線條拉長,勻整中有疏密,形成一種理性組合的規律。正是其“內收外放”的結體特征,在平正、凝重、嚴謹中流露出優美瀟灑的韻致。這種瀟灑意趣的流露正是其有別于其他金文的獨特所在,在西周金文中并不多見。《虢季子白盤銘》結體在沿襲大小、欹側、錯落的同時,又在發展中多了些均衡、平正的傾向,將靈動與嚴謹相結合。
以圖2中的“光”字為例,在《虢季子白盤銘》中,上半部分舒展,下半部分收窄,整體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風貌,對比明顯,將古拙與秀潤相結合,《毛公鼎銘》中的“光”字則呈瘦長狀,上下寬度對比不大,更注重質樸氣息;《虢季子白盤銘》中的“政”字呈現出“上窄下寬”的勢態,幅度較大,內部留白較多,靈動瀟灑之感從此處展現,左右兩部分所展現的大小對比將雍容與秀麗融于整體之中。《毛公鼎銘》中的“政”字雖同樣呈現“上窄下寬”狀但幅度較小,其靈動感則來源于結體外側的空間留白,以此展現質樸典雅的神韻。《毛公鼎銘》的渾厚內斂來自內部寬疏、外部內秀的陰陽結合,《虢季子白盤銘》的舒展秀麗來自內部結構沉穩的同時,線條的延伸又呈現出活潑灑脫的獨特意趣。
三、布局的“錯落有致”與“寬闊疏朗”

《毛公鼎》內部鑄有銘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青銅器中篇幅最長的銘文。銘文布局錯落有致,豎有行,橫無列,呈現出一派天真爛漫的藝術氣息。此鼎口大,腹胖,底部逐漸收窄,其銘文每行除了起始的四五字較為方正端整之外,下行至鼎的弧度較大之處,銘文字便隨著鼎身圓弧的面進行傾斜,如圖3中第8行,第12行的“王”字。這是由于腹部為極深的半球狀態,弧度較大,難于平整書寫,所以線條多彎曲且具有斜度。雖然由于不同字的筆畫多寡自然造就了銘文字形的大小變化,但仍可以看出空間布局的和諧統一。由于銘文隨鼎的弧面形制順勢展開,縱勢曲線,整體布局呈圓弧狀向兩側延伸,構成了和諧有趣,自然質樸的整體。以環狀、斜狀運動的線條與靈活多變的結字完成了整體布局。
相較而言,《虢季子白盤》底部鑄有銘文111字,其章法在西周金文中極其罕見,具有獨特的風貌。其通篇講究寬闊疏朗的空間感,反差極大,字形顯得尤其豎長,有些字橫畫排列緊密,豎畫刻意加長,與《毛公鼎》銘文緊密的布局不同,《虢季子白盤》銘文以寬闊疏朗的布局為主線,空間布白留隙極大,豎有行,橫有列,通篇文字熠熠生輝,如同“群星漫天”,加之銘文線條遒潤靈動,結體端莊雅致,與后世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遙相呼應,均為曠世名跡[4]。同時在章法整齊之中,又蘊含率意活潑,在第三四行的上半行都不同程度地向左欹側,而其余各行仍舊保持上下連貫,中心對齊,不管當時作者是否有意為之,這樣一來,作品的空間關系便產生了變化,整齊排列的一部分。《虢季子白盤》銘文雖大小參差錯落,但整體布局仍舊嚴整勻穩,這與其空間舒展疏闊有著極大的關系,故筆畫多者展其大,筆畫少者居其小,自由灑落,悠然自得。如圖4中“獻”“義”“廟”字就要比“子”“白”“于”字大出不少。
《毛公鼎銘》與《虢季子白盤銘》濃厚的金文意味蘊藏在字體行間,雖處于同時期,但卻呈現出不同氣勢的藝術美感。《毛公鼎銘》典雅質樸,渾穆古拙,通篇布局若有群鶴游天,蛟龍戲海,氣勢磅礴如云,神采絢麗飛動。《虢季子白盤銘》則是端莊秀雅,遒婉柔和,豐腴之中筋骨內含,變平常金文的沉雄茂密為空闊閑適、從容不迫,既有每個字的獨立性,又有呼應顧盼的勢態,疏朗活潑。整體布局方面,二者同屬于鑄于青銅器上的文字,字形隨著器型的變化而發生轉變。

四、結語
西周金文以其獨特的載體完整保存了篆書字體演變的本真狀態,如果說渾厚樸拙是《毛公鼎銘》立于經典的根基,灑脫意趣是其獨到的美感沉淀,那么端莊秀雅則是《虢季子白盤銘》獻與時代的寶藏,舒暢清疏便是其流傳于世的審美積淀。它們對于認識金文以及書法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西周金文在一脈相承、相對統一的風格神采上,形成了銘文沉雄穩健、古雅內蘊以及充滿靈動氣息的審美意趣,是中國書法史上標志金文發展的一座里程碑。
作者簡介
丁一兵,女,漢族,河南鄭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書法。
參考文獻
[1]陳思.試析石門經典漢隸書風之異同—以《大開通》《石門頌》《楊淮表紀》為例[J].書法教育,2019(4):55-62.
[2]歐陽中石,徐無聞主編.書法教學參考資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姜若木.文明之源[M].北京:中國書店,2020.
[4]馬博主編.書法大百科第1冊圖文珍藏版[M].北京:線裝書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