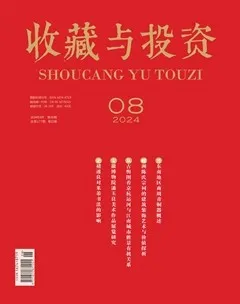文化記憶視域下歷史建筑的內涵重構與新生
摘要: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原為哈爾濱猶太新會堂,是哈爾濱猶太人活動舊址群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它見證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哈爾濱人民與猶太僑民間的交往與活動,為哈爾濱留下了專屬的城市記憶。伴隨著城市的發(fā)展與人口的遷移,這座歷史建筑的功能不斷變化—由最初的猶太會堂,最終演變?yōu)楠q太歷史文化紀念館,這一過程展示了哈爾濱多元友好的城市氛圍,也印證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自覺心態(tài)。本文將借助“文化記憶”理論,以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為例,擬分析歷史建筑所承載的文化記憶在當今社會的紀念方式與傳播途徑,力求探尋其背后的歷史價值與現(xiàn)實功用。
關鍵詞:哈爾濱;文化記憶;歷史建筑;猶太人
哈爾濱與猶太民族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傳統(tǒng)友誼。作為中國最早的鐵路樞紐之一,自19世紀末開始,哈爾濱就吸引了大量來自俄國的猶太僑民來此定居,他們在此籌建金融機構、商業(yè)會館和宗教場所,更興建了醫(yī)院、學校等社會福利設施,推動了哈爾濱各領域的繁榮發(fā)展。作為中國近代的國際化都市,哈爾濱的繁榮與血淚是不可分開的。一方面,哈爾濱是近代東北地區(qū)乃至中國屈辱歷史的重要見證地;另一方面,它以其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接納了同樣深受迫害的俄國猶太難民,這在世界上實屬罕見。在半個多世紀里,哈爾濱猶太僑民建成了系統(tǒng)性的猶太社區(qū),推動了哈爾濱的城市建設,為哈爾濱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建筑與文化遺產。
由于歷史原因,哈爾濱保留有一定數(shù)量的猶太歷史遺存,形成了初具規(guī)模的“哈爾濱猶太人活動舊址群”,為哈爾濱的城市文化中增添了一抹“國際化”色彩,在各式的猶太人活動舊址中,尤以哈爾濱猶太新會堂(現(xiàn)稱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最具代表性。作為20世紀初哈爾濱猶太人重要的活動場所之一,它保存了俄國猶太僑民與近代哈爾濱之間豐富的文化記憶,而在此基礎上修繕了的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是當代哈爾濱對這段歷史記憶的傳承與紀念。
一、猶太新會堂的歷史變遷與文化記憶
19世紀中葉以來,奉行積極對外擴張政策的沙皇俄國開始對中國東北進行蠶食。清政府相繼與沙俄簽訂了《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密約》等不平等條約。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控制該地區(qū),沙俄開展了積極的移民計劃,鼓勵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俄國人向哈爾濱移民,這是猶太人最初來到哈爾濱的主要緣由。19世紀末,隨著中東鐵路開始修建,大量的俄國人來到我國東北地區(qū),其中就有相當數(shù)量的猶太人。中東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哈爾濱近代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索斯金、斯基德爾斯基等猶太企業(yè)家紛紛來到哈爾濱并扎根于此①。20世紀初,俄國發(fā)生的一系列動蕩,促使哈爾濱的猶太人數(shù)量迅速增長。至1920年,哈爾濱的猶太人數(shù)已高達12000至13000人,形成了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猶太社區(qū)②。
哈爾濱猶太社區(qū)作為中國近代最大的猶太社區(qū)之一,在與哈爾濱民眾友善交往的同時,也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猶太新會堂就是其文化的重要見證之一。哈爾濱猶太新會堂由著名猶太建筑設計師約瑟夫·尤利耶維奇·列維金設計,并于1921年落成。哈爾濱猶太新會堂外部主色調為紅白色,象征猶太精神的大衛(wèi)星鑲嵌在會堂外部四周的墻面上,極具異域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哈爾濱的猶太僑民陸續(xù)離開哈爾濱,猶太新會堂最終于20世紀50年代關閉,并轉讓給中國政府。作為哈爾濱猶太人舉行主要活動的重要場所,猶太新會堂承載著哈爾濱猶太人的歷史記憶,見證了他們與哈爾濱市民之間的友好交往。猶太新會堂周邊分布著哈爾濱猶太國民銀行、猶太老會堂、索斯金故居等建筑,成為猶太僑民在哈爾濱生活居住的證明。如今,這些建筑已共同構成了哈爾濱猶太人活動舊址群,成為哈爾濱展示多元文化和包容精神的窗口。作為東北地區(qū)最大的猶太會堂,猶太新會堂曾被作為普通建筑使用,其原址一度成為哈爾濱市公安局俱樂部招待所。21世紀初,隨著哈爾濱市歷史建筑保護工作的推進,猶太新會堂得到了修繕和保護,舊址現(xiàn)今作為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對外開放。紀念館與其他猶太歷史建筑一起,共同組成了完整的猶太文化展陳體系。
二、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的記憶敘事
從會堂到辦公場所,再由辦公地轉變?yōu)榧o念館,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所承載的文化記憶是極具價值的。從城市記憶的角度來看,它收集并整理了哈爾濱猶太人歷史影像,全方位展示了哈爾濱城市發(fā)展的過程和樣貌;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它收藏了哈爾濱猶太人保留下來的歷史文件和檔案資料,注重整體研究與個體研究,既展示了哈爾濱民眾與猶太僑民之間的交流,又從側面反映出哈爾濱近代以來的歷史。紀念館大體可分為實物與模型展覽、照片與影像展覽兩部分。
(一)實物與模型展覽
在猶太文化歷史紀念館中,實物模型展覽是重要的展陳部分之一。
首先,從整體上看,展示陳列的實物包含了歷史文件、文化與名人雕塑、歷史建筑模型等。這些實物各自為陣,又統(tǒng)一構成一個整體。從布局上看,這些實物陳列分散在紀念館的各個方位,共同還原了對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的真實場景。
其次,作為哈爾濱猶太文化重要見證的歷史建筑模型,都是由建筑原型按比例進行復刻而來的。猶太國民銀行、拉比諾維奇大樓舊址、列昂季·斯基德爾斯基故居等歷史建筑模型在紀念館走廊依次排開,它們見證了猶太僑民的生存和發(fā)展。
如今,這些歷史建筑的原型已作為哈爾濱猶太人活動舊址群的一部分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歷史實物既可獨立展示,也可以共同陳列,充分見證了猶太僑民在哈爾濱的生活樣態(tài)。文化、名人雕塑同樣被展示出來,這些雕塑被賦予了與哈爾濱猶太文化有關的歷史故事,清晰地傳遞出猶太文化在近代哈爾濱的生機與活力。
(二)照片與影像展覽
老照片、紀錄片等近代影像資料是展現(xiàn)近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媒介。在中國近代史上,由于西方技術的傳入,各種照片和影視資料也隨之出現(xiàn)并流傳至今。與宏觀歷史不同,這些影像資料以其細膩的畫面和真實的場景展現(xiàn)了近代民眾的微觀生活,影像中出現(xiàn)的歷史建筑有些保留至今,記憶影像與真實建筑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當?shù)鼐用竦募w記憶。總之,以記憶影像為展陳資料的措施不僅使歷史文化極具真實性,而且極易引起參觀者的情感共鳴。
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中記憶影像展覽是其重點部分。紀念館眾多的歷史影像資料分布在各個展陳單元,屏幕上播放的紀錄片、各處的歷史照片與文字說明,都展示出哈爾濱民眾與猶太僑民親切交流與互動。除此之外,哈爾濱歷史文化紀念館本身就是由哈爾濱猶太新會堂改建而來。歷史建筑功能的轉換本身就是一種古今對比,無疑為參觀者的文化之旅增添了一分奇妙。從哈爾濱猶太新會堂到猶太文化歷史紀念館,哈爾濱對猶太文化的包容不言而喻。
三、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的價值與功用
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作為承載著哈爾濱城市史的記憶場所,既是哈爾濱猶太文化的紀念場所,又是哈爾濱市民與猶太民族友好交往的重要見證,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現(xiàn)實功用。
(一)哈爾濱猶太文化的紀念場所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東鐵路的建成與通車,哈爾濱迅速發(fā)展為遠東重要的國際化都市。“三十多個國家的二十幾萬僑民曾匯聚于此,各國文化在這個開放包容之地得到了繁榮發(fā)展。”③精美絕倫的中外建筑、精致獨特的人文風情成為哈爾濱靚麗的歷史文化名片,使得哈爾濱被冠以“東方莫斯科”和“東方小巴黎”的美譽。
在眾多外僑文化中,猶太文化尤為矚目,堪稱哈爾濱多元文化的典型代表。猶太僑民在此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們在金融、商業(yè)、新聞、教育和醫(yī)療等領域影響巨大,在取得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助力了哈爾濱經濟的發(fā)展,并為哈爾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建筑。皮埃爾·諾拉曾指出:“場所對于承載文化記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構建和傳承集體記憶最為重要的路徑之一。”④中猶友好交流已經歷近百年光陰,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哈爾濱人,親歷者和見證者已然不多,這段文化記憶正逐漸被時代湮沒。為了彌合歷史與現(xiàn)實的距離、傳承這段文化記憶,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作為哈爾濱猶太文化和歷史記憶的重要見證之地,自然成為首要的保護場所和紀念空間。
(二)哈爾濱市民與猶太民族友好交往的重要見證
在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的展廳中,大量的歷史照片和珍貴影像資料記錄了哈爾濱市民與猶太民族之間的友好交往。紀念館作為哈爾濱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見證了中猶雙方的友好交往。一方面,它體現(xiàn)了哈爾濱包容開放的城市形象,也展現(xiàn)了中國自古以來愛好和平的態(tài)度。留居中國的猶太人是世界上少有的未受到歧視和迫害的猶太群體。在紀念館二層的浮雕墻上刻有亨利·基辛格的一段話:歷史上曾經有兩萬多猶太人為擺脫歧視、迫害而定居哈爾濱。哈爾濱人民以中華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懷善待猶太人,這一歷史事實是世界人道主義的光彩記錄。另一方面,紀念館是中猶交往合作、建立互信的一塊基石。紀念館的成立向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猶太人清晰地傳遞了以哈爾濱市民為代表的中國人民愛好和平、友好交往的良性信號。可以說,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在傳承城市文化與傳播中國聲音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三)文化記憶與哈爾濱城市風貌的塑造
從城市發(fā)展的角度來說,歷史建筑對于某個城市風貌的塑造具有極高的價值。如何利用好歷史建筑,是每個歷史文化城市需要仔細研究的課題。將文化記憶融入歷史建筑上,既能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又能塑造獨樹一幟的城市風貌。
哈爾濱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各種文化在此交相輝映。通常而言,歷史聚落的整體價值要大于構成其單體要素的價值⑤。因此,當?shù)爻浞职l(fā)掘和利用歷史資源,以猶太文化紀念館為代表的歷史建筑群在保留自身文化樣貌的同時,還可以不斷構建新型的歷史文化街區(qū)。除博物館、紀念館外,咖啡館、圖書屋等兼具文化和旅游功能的場所出現(xiàn)在歷史文化街區(qū),這些歷史建筑共同構成了哈爾濱獨特的人文風情和城市樣貌,再現(xiàn)了當時猶太僑民的在哈爾濱的生活場景,為游客提供了兼顧休憩與娛樂的文化之旅,既勾連起哈爾濱與猶太僑民之間的聯(lián)系,又真正地將猶太文化融入城市之中。
四、結語
哈爾濱作為中國近代早期的一座國際化城市,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是許多城市所不及的。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紀念館幾經變遷,如棱鏡般折射出哈爾濱近百年的城市發(fā)展史,也見證了光陰歲月里友好交往的佳話。哈爾濱為猶太難民提供了棲息之地,猶太人也為哈爾濱作出了經濟等方面的貢獻。在互聯(lián)網(wǎng)經濟高速發(fā)展的時代,哈爾濱需要以多元的歷史文化為基礎,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向世界展示其獨特的城市文化。與此同時,哈爾濱也需要以積極的態(tài)度,在保護以猶太新會堂為代表的一系列歷史建筑的工作中持續(xù)發(fā)力,并適度挖掘其中的文化記憶,讓歷史建筑煥發(fā)出新的生機與活力。這樣才能真正地做到兼顧傳承歷史記憶與發(fā)展文化經濟。
作者簡介
李冬冬,男,吉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世界史、猶太文化。
注釋
①肖洪:《俄國猶太人移居哈爾濱的內外因素分析》,《邊疆經濟與文化》2017年第1期第2頁。
②徐新:《猶太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頁。
③韓天艷:《哈爾濱猶太僑民文化遺產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第4期第75頁。
④[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曹丹紅,黃艷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⑤張亞宣,王現(xiàn)石,徐明:《歷史建筑普查方法與保護傳承體系構建—以遼寧朝陽為例》,《中國文化遺產》2024年第1期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