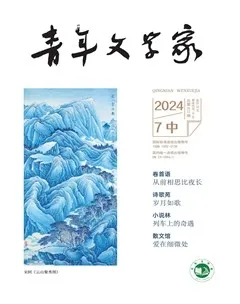《西游記》中西王母蟠桃盛宴的長生信仰
《西游記》第五回中,孫悟空在代管蟠桃園后,偷吃了九千年一熟的仙桃。當得知自己未被邀請參加蟠桃大會時,他變作赤腳大仙的模樣,私赴瑤池,偷吃了仙品、仙酒,攪亂蟠桃大會。書中寫道:“夭夭灼灼桃盈樹,棵棵株株果壓枝……不是玄都凡俗種,瑤池王母自栽培。”孫悟空與土地公交談過程中談及三千年一熟的蟠桃食之可以成仙得道,體健身輕;六千年一熟的蟠桃食之可以長生不老;九千年一熟的蟠桃食之可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由此可見,西王母親手栽培的蟠桃,難生長、周期長,食之則長壽成仙,是不可多得的靈物。西王母與蟠桃緊密關聯,因而成為長壽之神的代表。孫悟空大鬧天宮也是因為偷吃西王母的蟠桃和老君的仙丹,攪亂了蟠桃盛宴。瑤池盛宴是仙界慶壽的重要節日,孫悟空對其的破壞無疑是犯下了重罪,懲罰孫悟空,讓他保護唐僧西天取經也由此開始。考察這一章中的西王母、蟠桃,以及瑤池盛宴的成因、演變、功能,能夠讓我們明白為何瑤池蟠桃盛宴如此重要。同時,通過探求西王母蟠桃盛宴折射的長生信仰,我們能夠探究人們的生命意識,即人們的生命崇拜以及對長生不老的孜孜追求。
一、西王母:由神獸到神女的演變
西王母,又稱王母娘娘。人們對長生不老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持有不死藥、與長生信仰關系最密切的西王母由諸神中脫穎而出,成為人們崇拜的壽神之一。在《山海經》中,西王母亦人亦獸,帶有濃重的上古神話意味;自戰國末期開始,西王母逐漸脫去獸性的外衣,在《穆天子傳》中,將西王母作為部落首領;《漢武帝內傳》受神仙道教影響,將其視為擁有長生不死藥的吉神;受元明清時期雜劇、戲曲、小說的影響,民間將其奉為長生與姻緣女神,成為天界女仙之首。
《山海經·西山經》中記載:“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從形象上看,西王母是一個擁有人面,有豹尾、虎齒,且戴勝的半人半獸的怪物形象。“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從功能上來看,西王母具有掌瘟疫刑殺的神力。西周的《穆天子傳》中描寫西王母執玉獻禮,與周穆王宴飲酬唱、紀跡還歸。“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瑤池位于昆侖山,昆侖山是處于大地中央的山。“萬物誕生在這個中心,世界上的生命力、諧調、秩序等等統統以此為源泉。”(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由此,西王母逐漸獲得了女性的性別身份,地位尊貴且神秘。但此時的西王母還并不能稱為“女仙”,“仙”這一概念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后來稱呼的。我們首先要明白“仙”這一概念,《說文·人部》:“仙”又作“僊,長生僊去也,從人,從僊,僊亦聲”,“僊,升高也”,“登也”,表示人升高成仙。不死不滅,超然物外,斯之謂仙,昆侖山正是不死思想的發源地。《淮南子·地形訓》記載:“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秦漢求仙之風始興,漢武帝的求仙活動廣為人知。《漢武帝內傳》記載:“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祭嵩山,起神宮……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唯見王母乘紫云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身長丈余……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眄,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錦……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瓊鳳文之舃。視之可年卅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這里詳細描繪了漢武帝會見西王母的場景,將西王母的坐騎、隨行,以及儀容艷麗、超越世間的姿態刻畫得淋漓盡致。此時的西王母被視為天降祥福的吉神,擁有不死神藥。從這則記載中可以看出,西王母形象演變為擁有絕色天姿的長生不死的女仙人形象,其神職也由掌管人間瘟疫刑罰之事轉化為以賜壽為主要司職。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開始將西王母的神話傳說與周穆王西征、漢武帝西巡的歷史事實交織在一起,將這位神秘的女神形象具象化、人格化,同時使其神話傳說更加富有故事性。周穆王與西王母在瑤池相會的傳說被廣泛傳頌,而仙桃作為不死藥的神話也逐漸深入人心。道教也將西王母尊為“女仙之首”,成為道教中最受尊崇的女神仙之一。她不僅在天界負責宴請各路神仙,更在人間承載著婚姻和生育的神圣使命。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唐宋之后,西王母的形象開始滲透到雜劇、小說的創作中,成為眾多文學作品的中心角色。在這些小說、戲曲中,西王母的形象延續了其作為人形化吉神的傳統,展現了她作為天界女神,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的偉大形象,進一步豐富了中國文化的神話色彩。
總之,西王母的形象經歷了從兇神到善神,從生命之神到主生育、保平安的尊神的轉變,完成了由理想化到世俗化的歷史演變。她的形象更加人性化、神格更加豐富、信仰更加神圣化,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多樣化的呈現。
二、蟠桃靈物的長生寓意
蟠桃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先秦時期,人們就相信桃木可以驅鬼辟邪,而仙桃則被認為食之可得長生,被視為長壽仙果。在祝壽文化中,桃的意象本身就是神異的仙藥,有延年益壽之功效。桃子的長壽象征意義,正是源自西王母神話中的蟠桃,可以說,桃子作為長壽靈物的標志性符號,在漢代西王母神話傳說中就已經基本定型和成熟了,甚至在有的祝壽圖像中,有人干脆直接題寫“仙桃”“王母桃”來指代桃所蘊含的長壽寓意,從此也奠定了至今兩千多年人們對于它作為長壽符號的思維定式。把辟邪和長壽的功能融為一體,把原本作為食物的自然屬性,融入了神話傳說和生命信仰的祝壽“仙物”,成為后人信仰的長壽靈物。
仙桃影響的擴大與漢武帝奉道而衍生的故事密切相關。漢末建安前后的《漢武故事》、西晉張華的《博物志》、晉時的《漢武帝內傳》等書中都記載了西王母為漢武帝獻桃之事。《漢武帝內傳》中還言及西王母的成仙之藥:“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姜沉精……桃膠朱英,椒麻續斷……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發童顏,役使群鬼,得為地仙。”《漢武故事》載:“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是夜漏七刻,空中無云,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載七勝履玄瓊鳳文之舃,青氣如云,有二青鳥如烏,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與帝五枚。”記王母七月七日夜見漢武帝,并授漢武帝仙桃五枚。西王母所獻之桃“三千年一著子”,食之“可得極壽”,已具有后世傳說中神仙蟠桃的兩個基本特點:珍稀、長壽。蟠桃的美好想象,是漢代盛行神仙思想以及追求長生不老的社會風氣共同孕育的結晶。在這樣的背景下,蟠桃作為西王母贈予漢武帝的禮物,其存在顯得尤為合理,并漸漸演變為后來膾炙人口的蟠桃會故事。瑤池蟠桃會在民間流傳著諸多傳說,這些故事在元明清時期的小說和戲曲中頻繁出現,成為經典的文學場景。在宗教和民俗生活中,官宦之家在慶壽之時,常常演繹桃祝壽戲,而民間的蟠桃廟會更是熱鬧非凡,都彰顯了蟠桃文化的深遠影響。
宋代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描述唐三藏去西天取經過程中,徒弟孫行者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而招致王母娘娘將其“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其不僅描寫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吃了可使人長壽,又意指孫猴子的調皮,使得孫悟空的形象越發生動,也為孫悟空可以長生不死、神通廣大提供了合理的解釋。
三、瑤池宴賞群仙的祝壽主題
《西游記》第五回中描寫瑤池盛宴:“上會自有舊規,請的是西天佛老、菩薩、圣僧、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圣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個是五方五老。還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眾;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可見瑤池蟠桃會的盛大與隆重,仙界大大小小的神仙都來赴宴。群仙之所以都來參加瑤池盛宴,一方面是為西王母祝壽,另一方面是以西王母為代表的仙界,以蟠桃、仙丹對眾仙人進行賞賜。
瑤池宴賞群仙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時期,西王母開宴故事記載在《古本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中,都為戰國時期魏國史書,但在這個階段,西王母還沒有跟壽慶活動或壽慶文學產生直接聯系,但是已經具備了后世西王母壽慶故事中的一些元素,如西王母長生屬性的逐漸定型,西王母瑤池開宴的故事廣為流傳等。
從秦漢時期開始,西王母開宴故事在小說以及民間傳說中廣為流傳,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西王母下降賜宴,故事人物為追求長生的漢武帝;另一種是西王母攜群仙開宴,但西王母在這兩個故事中都是作為道教女仙出現的,具有增福增壽的能力,是普通民眾和道教信徒所追捧的對象,因而西王母開宴這一故事主題就帶上了濃厚的吉祥色彩,進而為宋代以后西王母蟠桃會故事成為壽慶文學和壽慶演出活動的重要題材奠定了基礎。瑤池宴賞不僅是仙界的盛事,更是人間對長生不老、福壽綿長的美好愿景的寄托。瑤池宴賞時,往往仙樂飄飄,悅耳動聽。西王母為群仙準備各種珍貴的靈物,眾仙對西王母也奉上珍奇異寶,寓意對壽神的祈愿。壽禮的豐富多樣,反映了人們對壽神崇拜和對生命價值的肯定。
西王母作為壽神,不僅因為她掌握有不死之藥,能使人長生不老,還因為西王母有賜福、賜子、化險、消災的神力。受當時自然環境和現實生存條件的制約,對于百姓而言,終其天年無疑是一種奢望。于是,人們將生存信念和美好希望寄托于神靈,并不自覺地把神話傳說傳播開來。祝壽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承載著尊老敬老、祈福納祥的深厚內涵。在瑤池宴賞的傳說中,祝壽不僅是對壽神的敬仰,更是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據錢鍾書《管錐編》的考證,“母”“土”二字在古漢語中為同音同義。土地是萬物生長之源,有兩層意義:一是撫育萬物,二是生生不息。西王母蟠桃盛宴的長生信仰折射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識,它反映了原始思維下人們對生命的認知。長生信仰源于生命意識,生命意識出于人的本能,出于對生命的珍視與對生命不死的向往。生命意識又是由“靈魂不死”的祖靈信仰發展演化生發,對于長生的渴望源自本能,先民們在求而不得的情況下相信靈魂不死。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便重視生命的綿延與存在。對于長生不老、家族繁榮以及生活安寧的向往,始終是廣大民眾內心最樸素的期盼。其中,西王母的神話傳說以其獨特的魅力,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對于長生與子孫繁衍的崇拜與追求,從而贏得了普通民眾的廣泛贊譽與喜愛。
人們通過把對不死的幻想用完整的神話故事表現出來,以此來緩解對死亡的焦慮。不死神話故事中的一些內容情節、不死觀念等得以傳承,不斷塑造著人們心中對不死的向往,豐富著長生信仰的文化內涵。對西王母這一壽神的崇拜蘊含著中華民族重生、貴生、厚生、樂生的情懷。這種帶有主觀愿望的生命意識滲透在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著重要影響,并為民間藝術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促進大批長壽文學作品的興起和發展。例如,元明雜劇《群仙祝壽》,以及涉及西王母神話傳說的《西游記》《宴瑤池》,給人留下鮮活、真實、平易、親切之感,成為長壽文化的符號和標志性元素,以《西游記》為代表的西王母蟠桃盛宴更是擴大了西王母信仰的影響。
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蘊含人們對生命的認識,是民間信仰的遺存,折射出人們好生惡死的基本心態和求吉求壽的心理。這些神話傳說深深扎根于人們心中,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給人們以心靈的安慰和對于福壽的殷切向往,催發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壽神、壽仙的不倦“塑造”,折射出人們對長生的孜孜追求。從這層意義上來說,長生信仰引發著人們對現有生命價值的反思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