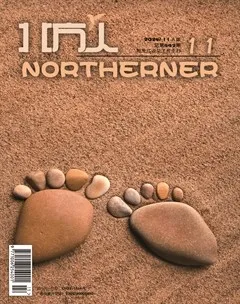那年秋天,她來到鶴崗,租下了房子

“從熟視無睹的日常逃走,從陳舊的人生軌道逃走。”一本名為《逃走的人》的書,腰封上寫著這句話。
對于深度參與都市生活,很多時候也受困于其中的人來說,“逃離”這一概念在當下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關于一本寫“背對時代”的書,我們會想象著能在書中看到人生的另一種解法,能在更勇敢的人身上收獲一些力量。不過,隨著一個一個“鶴崗青年”的故事在紙上展開,我們卻發現,他們并不能在“逃走”后一腳踏入桃花源,生活的真實面目仍會顯露出復雜乃至沉重的一面。
作者李穎迪很早就關注了“隱居吧”,在網絡上的隱居者聚落里,總有人分享、討論各種形態的隱居生活,但那更多是模糊的剪影,稍縱即逝。她覺得,要理解這些人的選擇,不能只作為旁觀者存在,而應當走到這種生活中去。
在2022年的秋天,她來到鶴崗,租下了房子,在與一些來鶴崗的年輕人有時親密、有時疏離的共處中,以“我”的在場體驗,完成了《逃走的人》這部紀實文學,記錄下了“逃走的生活”本來的樣子。
(以下內容整理自《逃走的人》原文)
林雯
來鶴崗前,林雯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手機回收公司的客服。
公司離家不遠,上班時間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
一天的工作中,林雯首先要處理前夜的留言,一般有六七十條。很快,新的問題開始涌來。每當一個客戶的對話框彈出來,林雯面前的屏幕上就會出現一個變動的小方框——
計時:00s,01s,02s,03s,04s,05s,06s,07s,08s,09s,10s……
她必須在10秒內回復每個問題,不能走神。為此她設置了上百個回復的快捷鍵,稍等——“sd”,抱歉——“bq”,有關抱歉的快捷鍵她設置了快10個。
她拿過兩次S績效(重大貢獻),那兩個月,她平均回復秒數為8秒,回復量比平常多1/3,平均每天回復500個問題,每小時大約和41個人對話。
離職前,她連續上了8天班。
回憶起這份工作,她說“沒什么價值感,活得渾渾噩噩”。
來到鶴崗后,她花6萬塊錢買了套一室一廳的房子,用很多家居用品精心布置每個角落:客廳中間的淺棕色木質島臺,投影儀和屏幕,插著紅色火棘枝的玻璃瓶,藏青色羊毛地毯,環形暖色臺燈。
她在家里開了外賣炸串店,每天早上10點醒來后開始接單,然后倒在沙發上,到中午12點起床洗漱,清點食材。
直到下午,手機上的電子女聲才會第一次響起——“XX外賣提醒您,您有新的訂單。”通常一天只能接到四五單,運氣好才有10單,每月也就賺一兩千元,但也夠了。
沒單時,她躺在沙發上打游戲,最近一個賽季平均每天打20把,耗掉五六個小時。晚上12點,她關掉外賣后臺,繼續在沙發上打游戲到凌晨三四點。
林雯不愿意過多談到過去,人生的起點空空蕩蕩,上升太難;但說到怎么看待未來,她幾乎沒有猶豫:“消磨時間到死。”
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包括過去和未來。不過,來鶴崗后,她第一次有了自由的感覺,可以在刷到丙乙烯立體畫的短視頻后立即下單,如果還在家里,爸媽不會讓她畫畫。
她也嘗試了一個“奢侈”的愛好,買來了一個“月光水母缸”,夜幕降臨后,大西洋海刺水母伸展、收縮著柔軟的身體,像在月光下浮游。
“比亞迪男生”
他曾是惠州比亞迪工廠的技術工人,來鶴崗買房生活兩年,不過房子現在還是毛坯,屋內的陳設一共不超過一千元。
他在比亞迪汽車廠待了一年半,直到和領導發生一次爭吵。辭職后,他來到了鶴崗。
他很難形容來鶴崗前后兩種生活的差別。此前,有關生活的決定雖然都是由他做出來的,但做什么工作,去哪座城市,到哪家工廠,和誰談戀愛,這些選擇都是出于慣性。
去鶴崗,也不能說就此自由了,得看怎么定義“自由”——買完房子,他把剩下的兩三萬存款拿去股市。2022年,錢在股市中消失,他又在貸款服務平臺貸了兩三萬。現在,他每天8點醒來,10點起床,看一眼股票,打六個小時游戲,做飯,睡覺。
他一個月的支出在300元左右。現在沒錢,他就吃燉白菜、炒白菜、腌白菜,燉黃瓜、炒黃瓜、腌黃瓜。
鶴崗的暖氣費一年兩三千元,他停掉了暖氣。
王荔
王荔和其他來到鶴崗的年輕人不太一樣,她愛出門走動,常爬到山頂看落日,愛交朋友,渴望與人產生連接。來鶴崗前,她去過西邊的大理、東邊的平潭,也飛到過巴厘島,走到懸崖邊看海。
來到鶴崗后,王荔說生活的目標就是掙錢,掙了錢就可以養老。她想過未來離開寒冷的鶴崗,去云南買一個帶陽臺的小院。
王荔開了自媒體賬號,從其他國家的網站搬運漫畫,搬運的漫畫多講愛情。她很快有了三四十萬粉絲,收入也翻了倍。
“我還想遇見真愛啊”,在鶴崗,很少有人愿意像她這樣講對愛情的渴望。
來鶴崗前,她經常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唱歌、玩狼人殺。來鶴崗后,她一度不能忍受孤單的生活,后來認識了來這里生活的其他年輕人,才決定留下來。
講起往事,王荔說自己老家是四川的,畢業后先去了北京的服裝廠,又到廣州給淘寶店做美工,后來和房東吵架,在網上搜房價便宜的地方,便來了鶴崗。
她說,爸媽在老家做點小生意,媽媽每天罵她,像到了更年期一樣。她排斥婚姻,因為媽媽每天太辛苦了,自己不愿再走這條老路。
后來,王荔失蹤了。
李穎迪找到和王荔關系較近的幾個人,他們聯系上了王荔的家人,在大家的催促下,她的家人才愿意來鶴崗報警。結果,在兩個半月前,王荔已經離世了。
原來,她年幼時母親就去世了,并非像她說的媽媽每天罵她。母親走后,她就像沒有了家。有一年冬天很冷,王荔想從家里拿條毛毯到學校,被父親拒絕了。王荔沒考上大學,問父親能不能花錢上大學,但當時家里沒錢。這件事告一段落后,父親找了個阿姨。
按村里習俗,自殺是厄運的象征。她去世后,父親一度不同意下葬。
可能是王荔生前見過的最后一個人回憶,臨近5月,她曾說:“我馬上就要回家,陪我媽媽去過母親節。”
逃離并非生活的終點
有人說,讀這本書的感受就像書中提到的磨砂玻璃——似乎并沒有將一切封死,可是透過它又什么都看不到。也有人說,這些文字有種北方冬日的陰郁氣質。
也許,《逃走的人》中的紀實會打破某種神話,帶來“逃走”從想象的半空落地于現實后的落差感。這些鶴崗年輕人的經歷讓我們看到,逃離后并不一定能駛向新的遠方,比做出逃離這個選擇更難的,是重建另一種生活。也許好不容易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逃走,又馬上陷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人要面對更真實的問題,當你逃離了,來到一個新地方,你想過上什么生活?慢慢發現,還是要面對很多問題。比如最現實的,如果不上班了,怎么養活自己,怎么跟人交往,以及最重要的——怎么面對自己。
這是李穎迪在鶴崗生活后的感悟。在生活這個復雜的場域中,烏托邦只存在于彼岸,那些“逃走”的人仍然要與現實和自我糾纏。
完成這本書后,她也說:文學意義上的審美和人真實的生活是兩個層面的東西。我在審美以及價值觀上仍然會理解逃離,理解這個選擇和行動,但我也想表達:逃離并非生活的終點。
后來,李穎迪回到了北京,林雯、“比亞迪男孩”和書中的許多年輕人依然留在鶴崗,他們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天離開,也可能不會。
我們無法評判逃離者的收獲與代價是否平衡,但至少,這些逃離是一次次“身體力行的求解”。我們這一代疲倦但仍擁有微小勇氣的心靈,對“人會為自己選擇何種存在”的追問,在當下,迫切地需要被更多人看見、思考。
生活還在繼續,祝福每一個仍在探尋自身存在的人。
(摘自微信公眾號“新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