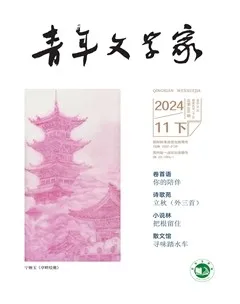劇場環境下的“破壁”
《桃花扇》中對《牡丹亭》等劇目中曲牌、曲詞的引用頗引人注目,也是明顯的“戲中戲”嵌套,然而往往被前人所忽視的,也可稱《桃花扇》特有的新奇之處,則是這些“戲中戲”的成戲過程,即往往不會被呈現在觀眾眼前的編戲、排戲等幕后進程。一旦這些幕后進程在劇場中被呈現,戲劇就不再是一個單向的輸出與接受的過程,觀眾得以見證戲中之戲的形成,也由此從觀看者向參與者的身份邁出一步,雖然兩個身份仍在模糊中跳躍不定,卻也可以算作打破單向輸出壁壘的有效嘗試。下文即從編、排兩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編戲。閏二十出《閑話》有提及,丑角賈客言:“請問老爺,方才說的那些殉節文武,都有姓名么……我小鋪中要編成唱本,傳示四方,叫萬人景仰他哩。”小生山人言:“那些投順闖賊,不忠不義的姓名,也該流傳,叫人唾罵。”這便是民間唱本的初步形成。褒忠義、貶奸佞,是這些民間作者的初衷,最直接的表現方式便是羅列出這一個個姓名,讓其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本劇中亦有這樣對人名的大段列舉,即第四十出《入道》中外角張薇以拜壇法師身份對明思宗及甲申殉難諸文武大臣的朝請大禮。兩戲之間相互呼應,張薇又在《閑話》中承諾將忠奸姓名奉送與人,于是其既成為這些姓名的收集者、遞送者,是一個唱本形成的前驅,又成為《桃花扇》戲中將諸多姓名逐個念誦的人,是為劇本形成付演的執行者。此已不單是“戲中有戲”,而是“戲中成戲”,若將對《牡丹亭》等戲的引用稱作摘取式的“戲中有戲”,《桃花扇》這般將編戲目標的提出與達成全在一場戲中呈現,便可稱為“戲中成戲”。
其二,排戲。一出戲要成,從劇本印發、演員學戲、臨場選角、一直到試戲排練,種種繁復過程都不可或缺。首先是劇本印發。第二十五出《選優》中李香君有言:“念會不難,只是沒有腳本。”憐人演戲須有腳本,故有第十七出《拒媒》:“聞得新主登極,阮老爺獻了四種傳奇,圣心大悅,把《燕子箋》鈔發總綱……”其次是演員學戲。第二出《傳歌》,既有提及妓女學曲需由清客教學,又有連板節奏、唱腔務頭等專業知識,因而也不再是對《牡丹亭》劇目文本的單純引用,而是一次濃縮的完整教習。民間妓院教習之外,也有宮中的內廷教習,其中有民間妓院承接官差,入宮。第二十四出《罵筵》有言:“前日進了四種傳奇,圣心大悅;立刻傳旨,命禮部采選宮人,要將《燕子箋》被之聲歌,為中興一代之樂。我想這本傳奇,精深奧妙,倘被俗手教壞,豈不損我文名?因而乘機啟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強似教手。’圣上從諫如流,就命廣搜舊院,大羅秦淮,拿了清客妓女數十余人,交與禮部揀選。”再次是臨場選角,這一過程集中在第二十五出《選優》中。選角時的明爭暗斗自然不少,戲劇沖突足夠鮮明,正旦一角的人選變化也合觀眾心意。最后的試戲排練過程也在此出一筆帶過。皇帝在選角末吩咐清客教習,其職能類于戲劇排演中的藝術指導,又吩咐現“管領煙花,銜名供奉”的阮大鋮不時指點,則約為舞臺導演之職,加之《燕子箋》由其親自編撰,對其藝術呈現效果自有要求。
以上幕后進程,觀眾雖不至于一無所知,卻也不會時時得見,一般劇場更是不會將劇目排演過程作為演出內容展示給觀眾。《桃花扇》選取這樣的場景作為戲劇內容,有兩方面用途。
其一是增強戲劇真實性。《桃花扇》作者自詡其作為嚴肅的歷史劇,凡例中有“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鐘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要呈現真實,自然不能只書寫排演有序的嚴整場面,在戰場上,有饑兵鬧反、將領內斗、遺民潰逃,在戲中戲上,竟也將正式演出前的種種樣態呈現出來,這場戲不再是粉飾完畢供看客欣賞的精巧物件,“表演痕跡”被這樣巧妙地消解了。
其二是增強觀眾參與感。前文提及戲中幕后情景“觀眾并非聞所未聞”,這也是選取現實素材的重要考慮因素。要專業,卻也不能太過專業,不可佶屈聱牙,清新自然、貼近生活是要旨,在這樣的選材基礎上營造出的似近非近、了解而并不熟稔的環境中,觀眾的參與感最強。“參與”并非“生活”,若戲劇內容與自己平常生活并無二致,失了新鮮感,自然就索然無味,同時若內容過分專業,也會給人難以接近融入之感。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即是與觀眾距離最近的“注視即參與”。仍用前文中例子,如蘇昆生教李香君唱戲時,曾提《牡丹亭》中“雨絲風片”一句,“絲”是務頭,應在嗓子內唱。《牡丹亭》是當時最為時興的劇目之一,《皂羅袍》更是家喻戶曉的名曲,知曉該曲唱法的民眾應不在少數。見蘇昆生教習,難免生出自己亦可擔此大任之感。現實中的戲曲教習當然不會如此簡單,而其中好理解、易傳播的,往往傳至民眾耳際,又因其與自身日常生活無甚干系而印象模糊,權當成常識般的背景板。而當民眾成了觀眾,注視這些“常識”在面前展現時,模糊的記憶被喚醒,尤其當表演內容正與自身印象相稱,僅是注視本身便成就了參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