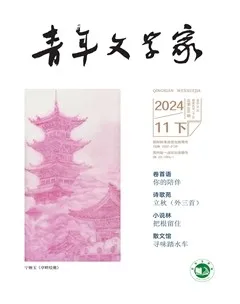蘇軾嶺南時期的詩歌創作
蘇軾早年因其文風清新灑脫得到歐陽修的賞識,在文壇嶄露頭角,正當其聲名大噪要在官場上大展身手之時,父母先后病逝,蘇軾只得暫離官場,回鄉守喪。待到蘇軾回朝,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因為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與新黨站在了對立面,后來又抨擊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腐敗不堪,以致既不能得到舊黨的認同,又不能融入新黨中,在朝中備受排擠。
紹圣元年(1094),新黨再次上臺,特立獨行的蘇軾依舊與之不和。四月,“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職知英州”(《宋史》),蘇軾才平穩幾年的仕途因此又生波瀾。同年,御史來之邵等人多次在宋哲宗面前抨擊蘇軾,稱其“詆斥先朝”,使得宋哲宗更加厭惡蘇軾,導致蘇軾在前往英州的路上再度被貶,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于惠州安置。在惠州三年后,新黨依舊沒有忘記已經遠在天涯海角的蘇軾,他們以“罰不稱愆”“幸免失刑者尚多”為理由上書請求宋哲宗對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黨人重新議罪懲罰,蘇軾因為詩中有譏諷朝廷之嫌,被貶為瓊州別駕,前往更加偏遠的儋州。盡管身處蠻荒落后之地,蘇軾也并未一蹶不振。他從剛開始的失落與苦悶中逐漸走出來,到后來變得從容與適應。其間,他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歌,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蘇軾的心態與思想品格,還深刻影響了嶺南地區的文學發展。
一、蘇軾嶺南時期的詩歌創作
自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惠州,到徽宗即位(1100),新帝將蘇軾調往廉州、永州做官,蘇軾長達六年的放逐生涯才算結束。在嶺南的六年時間里,蘇軾沒有停止自己的詩歌創作,他借詩歌抒發心中的苦悶,借詩歌為自己的生活增添生氣,借詩歌記錄日常生活與當地風物。蘇軾在嶺南時期的詩歌創作若是按階段劃分,可以分為惠州時期和儋州時期;若是按詩歌內容劃分,可以分為抒情詩、勸農詩、日常紀事詩、風物詩、和陶詩。
(一)抒情詩
初到嶺南的蘇軾是苦悶的,惡劣的生活環境、陌生的語言,甚至日常飲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朋友更是相隔千里,幾乎沒有再見的可能,蘇軾只能借詩歌抒發自己的苦悶之情,通過詩寬慰自己的精神世界;但后來蘇軾逐漸適應當地生活,變得坦然。
蘇軾并不是一直曠達樂觀的,他也有苦悶至極的時刻。政治上的失意、朝堂的放逐與荒涼陌生的環境使他悲觀,他認為自己再無重回京城的可能了。他在詩中寫到“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其一),遺憾自己不能北歸為君主分憂。然而很快他便調整了自己的心態,面對陌生的環境,他十分曠達地說到“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贈王子直秀才》),其中既有無人相識的落寞,又有逃離眾矢之的的慶幸,情感復雜。蘇軾有時也會嘆息自己日益增長的年歲、衰老的面容,他在《縱筆三首》其一中寫道:“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詩人自嘲是一個病弱衰老的老翁,兒子卻將自己飲酒所導致的面色紅潤當作是朱顏猶在,以輕快的語言描寫令人感傷之事。在嶺南居住的時間久了,蘇軾逐漸適應了當地的生活,與當地淳樸的居民和睦往來,沒有官場的鉤心斗角。嶺南仿佛是蘇軾心中的世外桃源,在這山清水秀之地,他決定“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寓居合江樓》)。他在詩中多次表達了自己對嶺南的深厚感情,比如“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以及被調離嶺南之時所寫的“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別海南黎民表》),表達了自己對嶺南這片土地深深的眷戀之情,以及對當地居民的不舍之情。蘇軾已經將海南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離去之時,更是發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喟嘆。嶺南是蘇軾被貶的傷心之地,但更是他寄托了無限情思的第二故鄉。蘇軾在這里經歷了從憂郁苦悶到坦然接受生活并熱愛這片土地的轉變,他將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了遼闊的嶺南大地之中。
(二)勸農詩
被貶嶺南無疑是蘇軾政治生涯的磨難,使得蘇軾徹底遠離了政治中心;但蘇軾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他仍然十分關心當地的民生問題,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為當地的百姓做實事。
嶺南地區的土地多荒廢,當地居民也很少有進行農業耕作的,很少種植農作物,以致“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聞子由瘦儋耳至難得肉食》)。蘇軾在嶺南的幾年時間里,見到太多荒廢著的農田,百姓常常因為農作物種植不足而糧食緊缺,只得將糧食與紅薯、芋頭混合著煮成粥以充饑。常言道:“民以食為天。”如此隨意的糧食貯藏使得蘇軾十分心痛,他惋惜于大片良田如此荒廢,哀傷于百姓糧食不足的境況,于是作《和陶勸農六首》勸民務農。
在第一首中蘇軾先闡述了嶺南地區漢族與黎族混居的現象,希望百姓不論民族,平等勞作,平等生活,“咨爾漢黎,均是一民”。接著在第二首中表達了對嶺南大片肥沃良田無人耕種的痛惜,“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指出了壓迫百姓的另一重勢力—貪官污吏,他們使得本就糧食緊缺的百姓生活更加窘迫,“貪夫污吏,鷹摯狼食”。在第三首詩中更進一步表達自己對于這種現狀的沉痛心情,“豈無良田,膴膴平陸”,擁有如此多的良田卻以芋頭和番薯充饑,“芋羹薯糜,以飽耆宿”。蘇軾在第四首中正式開始了勸農,開頭便是語重心長的“聽我苦言,其福永久”,接著勸他們應當怎么開墾荒田,經營田地,“斬艾蓬藋,南東其畝。父兄搢梃,以抶游手”。第五首勸百姓辛勤勞作才能有所收獲,“春無遺勤,秋有厚冀”。第六首則是為百姓預先織下一個豐收的美夢,當辛苦勞作之后,迎來的將是“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蘇軾這六首勸農詩,層層遞進,語重心長,語言簡潔,既分析了嶺南耕作的實際情況,又進一步給出了解決方案,并且描繪出豐收的景象鼓舞人心,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三)日常紀事詩
蘇軾的嶺南詩中有許多記述個人生活的詩,從中可以看到蘇軾在嶺南時的生活情狀,比如他在嶺南時期飲食的入鄉隨俗,喬遷新居的喜悅,以及和當地居民相處的種種趣事。
蘇軾在嶺南的生活是比較清苦的,常常因為等不到外省米商而無法飽食,但清苦的生活中卻有鄰里的互助,當地居民十分淳樸,常常幫助他這個外鄉人。他在《縱筆三首》其三中描述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灶,只雞斗酒定膰吾。”雖然已經半個月沒有酒足飯飽一次了,但好在明天就是歲末祭灶的日子,鄰居準備的肉食酒水定會邀請他一同享用,可見蘇軾與鄰居的情誼深厚。蘇軾會記錄下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比如《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中因為醉酒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情形,“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在《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中記述了自己在野外燒芋頭吃的趣事;甚至專門為初次嘗荔枝而寫了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在詩中他感嘆“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莼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自己為官不過是為了養家糊口,如今能在邊遠之地吃到如此美味,貶謫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蘇軾在這樣的逆境中仍然能如此豁達樂觀地享受當下時光,著實是令人敬佩。此外,蘇軾還寫了許多有關自己新居的詩,詳細地描述自己新居的環境:“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疏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新居》)這是他在儋州被逐出官舍后買地新建茅草屋的情狀,雖然新房子十分簡陋,但蘇軾仍能以清新的筆墨去發掘新居附近清幽的環境。蘇軾所寫的日常紀事詩展現了一個曠達知足的詩人形象,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仍能發掘出許多樂趣,苦中作樂并怡然自得。
(四)風物詩
風物詩即描寫某一地的風俗物產與風光景色的詩。蘇軾在嶺南期間寫了許多風物詩,其中有記述自己所見的嶺南山川之景,有嶺南的特產,以及當地人的某些習俗。
蘇軾在嶺南的六年時間里游覽了多處景色優美之地,既有山川風景,也有人文景觀,美景激起詩興,蘇軾在此留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在游覽碧落洞時他寫下了《碧落洞》《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諸如此類的還有《儋耳山》《白水山佛跡巖》《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等。關于當地人文景觀的詩篇大多是寫自己游覽佛寺的見聞與感受,比如《廣州蒲澗寺》《月華寺》《南華寺》《峽山寺》等。蘇軾在描寫游覽之景的同時借景抒情,比如在《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中表達自己歸隱之心的“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除了山川風景詩,描寫嶺南習俗的較少,物產詩相對較多,比如描述當地特色食物燒芋的“牛糞火中燒芋子,山人更吃懶殘殘”(《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以及吃槐葉冷淘的《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也有許多描寫當地特色水果的,比如寫荔枝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寫椰子的《椰子冠》、寫檳榔的《食檳榔》、寫龍眼的《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蘇軾的風物詩為我們展現了嶺南的物產與山水,并且塑造了一個積極探索被貶之地的詩人形象,他在游覽山川景物與品嘗嶺南物產的生活中逐漸融入并熱愛嶺南。
(五)和陶詩
和陶詩在蘇軾嶺南詩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據筆者統計,蘇軾嶺南詩有三百五十多首,其中和陶詩就有一百一十多首。蘇軾被貶嶺南之后,遠離官場,被迫過起了類似歸隱的生活,生活上與陶淵明的相似使得他在創作上更喜陶詩風格。
嶺南的清苦生活使得蘇軾不得不親自種田、買米、建新居,這樣的田園生活促使蘇軾逐漸向陶淵明靠近,但是二人的志向、抱負與人生觀念的差異造成二人詩風的差異。蘇軾雖然過起了“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雨后行菜圃》)的田園生活,但是與一心歸隱的陶淵明還是存在差異的。蘇軾從未想過放棄從政,甚至在被驅逐出政治舞臺后,仍然關心民生,心系朝中大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北歸還朝,正如他在《和陶貧士七首》中所寫的“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他還在《和陶詠三良》中將這種情感書寫得更為深沉:“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表達自己雖然被貶邊地,但是為江山社稷付出之心永遠不變。然而,正如蘇軾在《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并引》中稱:“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其中許多詩篇卻是流于形式,僅僅為了和盡陶詩而和,缺乏真情流露,違背了陶詩創作自然本真的屬性。
二、蘇軾嶺南時期詩歌創作的影響
嶺南在唐宋以前都是“崇山復嶺,盤回深阻,煙火鮮少,土曠不治”(《惠州府志》)的蠻荒之地,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在我國領土的最南邊,自古被稱為“天涯海角”,再加上嶺南地區本就是稱為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和大庾嶺五座山嶺之南的地方,使得嶺南長期與北方城市隔絕。據記載,從唐朝宰相張九齡在大庾嶺開鑿了梅關古道以后,嶺南地區才逐步得到開發。但是在交通十分落后的古代,嶺南與其他地區依舊交往不便,文化與農耕都十分落后,更遑論詩歌創作,以致被稱為蠻荒之地。
蘇軾被貶嶺南后,仍有許多文士不遠萬里慕名前來與之交談,和唱詩歌,請他指導。向蘇軾學習的文士中有很多當地的居民,他們在蘇軾這樣一個文學巨匠的悉心教導下,學問大漲,成為當地的文學傳播者、詩歌的創作者。在蘇軾前往嶺南之前,當地從未有人考取功名,如此廣闊的土地卻是個名副其實的“文化荒漠”。蘇軾的到來改變了這個局面,被蘇軾指導過的姜唐佐后來舉鄉貢,成了嶺南歷史上第一個舉人。后來,嶺南舉人、進士不斷,文教日興,學風日益興盛,詩歌創作逐漸豐富,與之前的情形大不相同,這離不開蘇軾的倡導與教導。蘇軾在嶺南時期的詩文創作與個人對文學的倡導為當地的文學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使這個偏僻落后地區的文化與那個時代的文學發展前沿接軌。
此外,蘇軾在嶺南時期的詩歌創作中所展現的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激勵著有相同遭遇的人,使他們從蘇軾的詩歌中汲取力量,走出心理上的陰霾,走向豁達樂觀的生活。蘇軾詩中所體現的對日常生活的熱愛,積極地探索生活中趣事的心境,也對身處困境中的讀者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嶺南是蘇軾人生逆境的最后一站,他在這里用詩歌書寫自己苦悶至極的情感,書寫自己北歸的愿望與為君效力的決心,書寫自己日常所見、所聞、所感,書寫自己對當地農耕落后的勸告。蘇軾在嶺南的詩歌創作不僅是他在嶺南情感、抱負與所行所見的記載,也是促進嶺南文學發展的一捧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