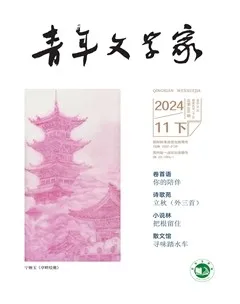共同的成都情結
從2022年2月開始,在成都逐漸郁蔥的初春中,阿來在阿來書房舉辦數場名為“杜甫成都詩”的講座。杜甫是唐代著名詩人,而阿來則是20世紀80年代起以小說被大家逐漸熟知的當代作家。阿來去解讀杜甫,本就是一個極其有意思的文學現象。阿來在系列講座中除了對杜甫入蜀詩歌作了許多獨到有趣的賞析,也借著杜甫入蜀的話題對成都作了些許自我的感受和創作經歷的追憶。歷史上入蜀的詩人不占少數,也有許多詩詞或多或少對成都作了直接描述。但唯有杜甫在成都的詩作深刻而熱烈地激蕩起阿來心頭的陣陣漣漪,這種共有的成都情結無疑是微妙而又復雜的,還需要進入兩人的文學書寫中找尋答案。
一、成都的生態自然熏染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為了躲避戰火,最終決定出關中,過秦州,一路西行來到局勢較為穩定的蜀地。《成都府》可謂是杜甫對成都的初印象—“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成都的繁華讓杜甫滿腹的愁怨有了些許改變。在朋友的幫助下,杜甫在浣花溪旁搭建起了自己的茅草屋。雖然他未脫貧寒,但成都的人文情懷與自然風貌給了他莫大的安慰,他也饒有興致地把筆觸逐漸傾斜于成都的自然意象與人文風光,形成獨特的成都敘事。這與他入蜀前的創作風格、創作對象可謂截然不同。可見,杜甫也欣然接納了成都。
首先,杜甫對自然景象尤其成都花草樹木的觀照方式是細微而又多樣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夜喜雨》),他可以運用聽覺道出自然的變幻無常,亦可以通過觸覺寫出“葉潤林塘密,衣干枕席清”(《水檻遣心二首》),《狂夫》《野老》《江村》《南鄰》等詩中直接運用視覺構成的畫面更是數不勝數。其次,杜甫對成都的生態氣候有著特別的感受,甚至在書寫中展現出別樣的博物意識。極具代表的《水檻遣心二首》中寫到“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蜀地花草魚蟲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已不能滿足詩人,于是他把眼光放在更為深邃奧妙的天象,滲透出豐富的自然美與生態美。這一時期,詩人帶著濃烈的生命與博物意識,著力去探索自然與人生的深邃奧秘,比如僅描繪鳥的姿態,他可以寫“沙暖睡鴛鴦”(《絕句二首》),也可以道“沙上鳧雛傍母眠”(《絕句漫興九首》其七),還能創作出“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春水》)的佳句。在驚嘆杜甫遣詞造句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關鍵的一點:沒有對自然界的仔細體察,沒有對生命生活的向往,沒有廣博的自然觀,是無法得到如此真摯與純真美的感受,更無法創作出如此佳句。
阿來的生態意識是在巍峨的雪山與廣袤的草原中孕育出來的。1996年,阿來離開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來到成都。受成都特殊地緣因素的影響,這種生態意識逐漸趨于純熟,并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一種更為深邃的博物觀。除了在書寫中極力保留住自然萬物最純真的味道,他的博物觀還與杜甫頗有共通之處,體現為一種對生命自然無盡探尋的科學意識。帶著濃厚的科學興趣與生態自覺意識,成名后的阿來很長一段時間在成都的《科幻世界》擔任編輯,他期待人文與科學融會貫通的夢想,在此階段展現得淋漓盡致。文摘如《讓巖石告訴我們》《關于生命的偉大發現》貫通古今,視野開闊,充分地體現出了他的科學知識儲備,讀起來詩意盎然但又充滿內蘊。與杜甫和成都相互接納的關系有所差異,從阿來入成都的幾十年來看,成都與阿來的關系更像是一對密友,兩者相互成就,相互幫助。成都作為新一線都市,在視野、資源方面對阿來提供大量幫助,尤其他在《科幻世界》任職期間與劉華杰、楊鴻雁等博物學家的結識,更是促進其博物觀的進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進入成都后的阿來找到一種新的文化切入點,他能利用自身身份與血脈特性,再結合對成都文化的獨特追溯與理解,自由地穿梭在漢藏文化之中,并積極運用于文學創作。與杜甫相同的是,阿來如此對文學表達的創新根植于兩人對成都共同的地域認同。2012年出版的《成都物候記》,作為阿來罕見的不以藏族聚居區為創作對象的作品標志其博物書寫達到新的高度。正如他所說:“我不能忍受自己對置身的環境一無所知。”自1996年出藏入蓉到此書的起筆已過十余年之久,但仍能充分感受到阿來始終是以謙遜、謹慎的姿態去追問和探索成都這個第二故鄉。可見,相同的語言基底、相同的文化記憶會打破時空限制,把不同的作家和作品相聯系,并產生精神上的共鳴。
阿來在《成都物候記》中提到過杜甫十余次,并多次把自己的生態博物意識與這位千年前的詩人相對照。翻看《成都物候記》,我們會看到兩位大家許多源于心靈的對話。杜甫在成都期間就對成都爭芳斗艷的花朵表示過濃烈興趣,其組詩《江畔獨步尋花》系列便是最好的觀照,“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六),雖然多是整體意象的描繪,但我們能看到成都的花朵在杜甫心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懷揣著對成都花朵同樣的喜愛,阿來在書中按照開花順序羅列蠟梅、海棠、櫻花、玉蘭等二十余種植物并作了詳盡的闡釋。桃花在成都屬于獨特的風景,阿來寫桃花從《詩經·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膾炙人口的詩句出發,并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桃花盛開的繁榮不應該只是詩句中中原地區衛國特有的景象。圍繞設想,經過細致的觀察與考證,他不僅發現成都賞桃的最佳觀賞點與季節,還從美學角度指出:“最漂亮的就是五只輻射狀花瓣構成的基本形狀,但那些復瓣多得過度的純觀賞性的碧桃,卻把桃花最基本的美感都取消了。”(《成都物候記》)阿來如此嚴謹細致的觀察角度,無疑是給成都奉獻了一份極佳的賞花指南。但在千年前,杜甫已為這份指南道出自己的獨特感受與體驗,如“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三),有走在浣花溪旁對整片桃花和諧唯美景象的賞鑒;“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絕句漫興九首》其五),亦有對殘花敗柳寥落意象的體驗;“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七),還有深情無限、細致入微的觀察。放眼兩位大家的生平,雖然他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年代,但或多或少都與貧困結伴,但其對精神烏托邦的不懈追求是從未停止的。成都的桃花抑或成都的地緣環境是他們共同選擇的靈魂棲息地。這片土地是神圣的,對于阿來來說,這是躁動的社會與猛烈的現代化進程下安逸舒適的棲居地;對于杜甫來講,這是遠離亂世的收容處。這片土地也是敏感的,一草一木無不牽動著兩人深邃復雜的心靈。
從興趣愛好到自然認知,再到審美體驗,阿來與杜甫都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帶著對自然的知識性認知,他們身體力行,自由暢快地穿梭在成都的花草樹木之中,融入成都的文化氛圍。綺麗的植物給他們美學和道德的滋養,他們又用筆創造詩意、靈動的文字去哺育成都這座充滿韻味的城市。杜甫與阿來的草木書寫,必然會成為成都不可或缺的文化積淀。
二、成都的人文關懷
成都的人文情懷除了讓杜甫在憂思之余多了一份沉浸自然花草的閑散,還讓他體味到在亂世中難得的人文體貼與關懷,這也助推了他對成都的完全接納。這種人文關懷首先直接來自朋友的幫助,如《酬高使君相贈》中的“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卜居》中的“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故人衣食、住所上的提供與幫助讓初到成都的杜甫肉體上得到休息,這些詩作不僅流露出杜甫對友人幫扶的感激,更代表了他對如此單純自然的交往環境與純真友誼的珍視與向往,當然,這都是屬于天府之國包容和諧人文情懷的一部分。
但真正讓杜甫的靈魂得到完全安放的是成都的人文底蘊與文化記憶。首先體現在杜甫對蜀地歷史名人的追憶。“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堂成》),這是杜甫茅屋建成有感而發所作,在自嘲懶惰之余,能清晰地看到草屋落成后杜甫發自肺腑的欣慰,也側面烘托出成都閑散平和的人文風情對杜甫心性的進一步感染。另外,還能感受到兩位異時代大家的隔空交流,尤其是杜甫對揚雄及其文學的認同。有論者已經指出在杜甫現存的詩歌中,約有二十首存在與揚雄相關的稱引,或對揚雄身世產生共鳴,或對揚雄才華表示認同。但在杜甫入蜀后,尤其在成都居住期間,揚雄成都人的身份強烈地勾起杜甫的文學情愫,不僅對其的關注空前顯著,也在詩作中深化了揚雄的形象。比如在入蜀前杜甫所作的《秋述》:“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云草《玄》寂寞,多為后輩所褻,近似之矣。”杜甫以揚雄自比,為的是凸顯出其創作時的寥落孤寂與揚雄的創作經歷頗有相似之處,多映射出凄涼悲苦之情。但在入蜀后,受成都地緣因素與揚雄西漢蜀郡籍貫的雙重呼喚,杜甫又表現出另外一副姿態,如“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鹿頭山》),“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壯游》),“子云窺未遍,方朔諧太枉”(《八哀詩·故著作郎貶臺州司戶滎陽鄭公虔》)。仔細體會,杜甫入蜀后的詩句中,身世飄蕩、仕途失意的潦倒哀怨之情儼然沖淡,更多的是以揚雄為標榜,毫無保留地抒發對其才華的贊揚與認可;盡管也有悲涼余味,但更多投射出的是杜甫由此及彼,英雄才子間的惺惺相惜之情。當然,還有一位文化名人是杜甫繞不開的,即諸葛亮。或許某天詩人在閑逛時被武侯祠外茂密的松柏所吸引,之后的所見所聞深切觸動了他感性而又深邃的心靈,繼而寫下《蜀相》這首名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句雄渾悲壯,蕩氣回腸。字里行間除了寄寓著感物思人的情懷外,還有杜甫站在蜀漢名相曾經奔走操勞的土地上,向世人宣告自身同樣渴望忠心報國、鞠躬盡瘁的人生態度。成都的花草樹木能讓杜甫怡然釋懷,成都的文化記憶又能讓他瞬間找回儒士的時代責任與擔當。不得不說,成都的杜甫向人們展示出了一種更加復雜、立體的形象。
成都的人文關懷同樣給阿來及其創作帶來巨大影響。阿來雖然并不算高產的作家,但在他一直堅持創作的作品中,總能找到屬于阿來自己的味道。這份味道既是其堅持用詩性筆調對浮躁社會的拷問,也是不停用扎實細節對崩塌價值的撞擊。尤其在1996年阿來出藏入蓉后仍堅定不移地把故鄉嘉絨藏地作為書寫的對象,他沒有在遽變的現實中茫然,在不安中退到邊緣,反而在成都人文地域的滋養中,在漢藏雙文化融會貫通的基礎上,有意避開主流話語,找到屬于自己的創作節奏。自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問世以來,阿來就已跳出民族書寫的單一維度,極力站在歷史的高度,觀照漢藏文明的對話,思考在現代力量沖擊下傳統藏地生態系統該何去何從的問題。不論是《塵埃落定》中加劇土司制度覆滅的現代異質力量的罌粟,還是《空山》中碾平村落里世代依存樹木的伐木機,顯然看出,阿來不忍也不愿接受故土文化逐漸消逝的現實,但又不得不帶著憂思奏起文化的挽歌。這樣的地域情結是復雜的。反觀阿來的早期作品,在《故土》《草原回旋曲》等詩歌中我們能看到還未離開家鄉的阿來多是帶著崇敬甚至有些許惶恐的態度回應著故土的感召,他的思想盤旋在梭磨河畔,他的意識流連于廣袤的草原與巍峨的雪山之中,滲透出的是個體生命對自然最樸素虔誠的膜拜。
或許此類現實書寫受不同時代環境的影響,杜甫與阿來的創作初衷有些許不同,但對苦難的關注,對弱勢群體的重視,他們又表現出驚人的共通之處。“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風雨交加下杜甫的茅屋被掀翻,自己都飽受貧寒折磨,可還是第一時間擔憂天下百姓,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阿來的中篇小說《云中記》則以大地震為背景,關注受災群眾的精神創傷。“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江漢》),盡管病痛纏身,杜甫仍對暮年生活表示出積極肯定的心態。阿來筆下的老人,如《荒蕪》中的老革命家駝子,《隨風飄散》中的額席江奶奶,總是閃耀著樂觀、勤勞、樸實的人格魅力。可見,兩位大家用文字既表達憂患,又彰顯對美好愿景的期望,在創作風格的多樣化嘗試上產生諸多有趣的呼應。
哲學家笛卡爾曾說過:“我思故我在。”可能對于文學家來講,是“我寫故我在”。古往今來,太多的人,造了太多的房子,但偏偏杜甫草堂能跨越風雨被世人緬懷留戀,正是因為有杜詩在,文學就在,草堂乃至錦城的生命力就在。阿來在講座中引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歌《人,詩意地棲居》與草堂的美好相聯系,恰如詩歌所講:“當人的棲居生活通向遠方,在那里,在那遙遠的地方,葡萄閃閃發光。”成都豐饒的自然景觀與濃厚的人文氣息激發了兩位大家—杜甫與阿來的創作靈感,促成了跨時代的文學共鳴與深度對話。這不僅僅是天府之地對他們的單純滋養,更在于他們對文學的無盡熱忱之下,以各自獨特的筆觸回饋給這座城市源源不斷的靈魂活力。他們的作品如同鮮活的生命體,不斷為成都注入新意,彰顯了文化交互滋養的美妙循環,展現了城市、自然與人文精神三者間相輔相成、共生共榮的美好景象。兩位大家的作品不僅映射出了成都的魅力,也成了成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構建了一個充滿詩意與想象的城市形象,體現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力量。至今,阿來也未曾停止過對杜甫的解讀與對話,這場偉大的文學交流依舊閃耀在天府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