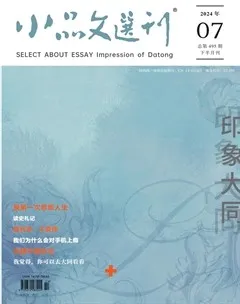阜田老街

堂弟邀請我回家參加他母親的葬禮,我欣然應邀。到了阜田鎮下了公交車,吃了一碗面條,覺得時間還早。到阜田老街轉一下,找一下童年的回憶。老街曾經是我童年夢想的地方,是我童年理想中的天堂。
來到阜田洞江河橋老橋上,向四周張望了一圈。說是洞江河,其實洞江河早已改道,繞道而行。河已經變成了池塘,往日洶涌奔騰河水不見,整個塘面完全被水葫蘆草遮蓋。這座橋是老橋倒了之后新修建的,由于當時資金有限,只能過行人和板車。后來又在既有老橋的原址又新建了一座兩車道新橋。據說是開國少將李水清通過私下的人脈關系立項、籌資修建的。最老的橋是石頭壘砌而成,老橋在我的影響中更精致、雄偉,在橋的兩頭引橋的每個橋墩上放著一尊石獅。在西頭引橋上當時擺著炸油條的攤子,炸出來的油條呈金黃色,剛撈出來,特別酥脆。在1982年春天,有幾天時間由于雨量特大,整個阜田街道處于一片汪洋之中,加上上游雙山水庫的泄洪,洪水將洞江河老橋沖跨。
據傳說,當時建橋的人在老橋橋墩里的石頭中間的放了一只金雞,在橋遇到不測之時,只要金雞一叫就會化險為夷。而那一天據說金雞睡著了,遇到洪水沒有叫,導致橋的坍塌。這只是神化傳說而已。其實橋塌的那一天的上午我是在橋上看熱鬧的,完全是橋墩之間的距離太短,橋拱太低。剛好上游有一棵大樹被洪水橫的沖下來,導致泄洪不暢,洪水漫過橋面,沖擊橋墩,導致橋體垮塌。
當時在橋的西南角是有一棟完全木制的吊腳樓也被洪水卷走了,主人用麻繩綁住房屋的主支柱上往回拖,賴何擋不住大自然的力量,最終吊腳樓就像一艘帆船從這里起航,順水而下。
阜田街道的東面和西面的通道就是靠這座橋,這三座橋見證了阜田街道的發展和變化。
在西面引橋下面矗立著一座電影院,現已破敗不堪,殘垣斷壁。但這里曾經是阜田鎮上的文化活動的風向標,也曾經見證過這里的繁華。每天到下午3-4點鐘后,就會看到在當時看來有一些穿戴時髦、整齊的年青人站在一塊粉刷在墻上的小黑板前面,看看今晚上演電影的名稱和內容簡介。這里也曾經是我追逐的樂園。下完課,吃完晚飯,有時一個人、有時邀請要好同學小跑來到電影院門口,看一下今晚上演電影。如果沒有看過,心里就在盤算如何混進去,如何逃避查票。電影票一張2角錢,但對我一個學生來講已經很貴。一份豆芽3分錢,一份豆腐5分錢,還不能長期吃,一個星期只能打一、二次菜。首先找到電影院圍墻出口處有一處缺口(這個早已踩好點)爬進電影院,站在走道上看。但不能太專心,必須另外一只眼睛察看查票人員,放映開始大約半小時左右,只要那里手電筒光一亮就知道開始查票,我們就必須順著查票人員繞著電影院兜一圈,才算完成避開查票。有時候還沒有完成,因為查票人員還會回頭再查,查到了只有補票,可能兩個星期的伙食費沒有了。昨日的繁華,今日已經破敗不堪,殘垣斷壁,電影院的門口擺放一大堆的建筑垃圾。還有當時的看電影的、放電影的人都去哪里,早已不是當年的小伙伴,人去樓敗。
在計劃經濟時代,飯店都是國營的,沒有私人的。那時候的飯店就是吃飯的,沒有住宿。當時有三家飯店中,在老橋引橋東頭的南北兩側各有一家,分別為一店、二店,現在都已不存在。店門是木板制,打開店門,就是將所有木板拆除下來。進入店內,門口左邊有一售票處,有幸進去吃過一碗面條。那是母親去逝,三舅來見最后一面后,在阜田街上給了我五角錢,二兩糧票叫我到飯店吃碗面。一碗面二兩糧票,二毛錢。購了票后,來到窗口,師傅將面條放進沸騰的水中。不一會兒,師傅將面條撈出,舀上一勺膠湯,再加上一小勺肉絲,將面條往窗口一放,自己將面條端到桌子上,看著冒著熱氣的面條,嘴巴對著面條吹氣,三下五除二一碗面條下肚,也許這是我人生當中最好吃的一碗面條,沒有之一,也是我第一次上飯店。
現在街中心的老飯店,也只有“阜田飯店”這四個字,才告知初到陌生的人這里曾經是阜田鎮上最好的飯店。因為它作為飯店的功能已經全部喪失。可當初它是阜田鎮上最好的飯店(兼旅館),每年中考的時候這里是考生歇腳的地方,可以說是一床難求。如今大門口擺著煙攤,里面好像進行過改造,沒有進去看,大廳內堆滿了雜物,雜亂無章。
整個街上有二十多家茶館,原來沒有這么多。在我的印像中東面兩橋中間是有一家茶館,平時三三兩兩的幾個人悠閑品著茶,大部分到中午散去,少數幾個人中午也不回家,留在茶館繼續聊天品茶,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到這里聚集,但我覺得這種生活很自在、愜意、高尚。隨著改革開放,可能是生活條件好了的原因,突然一下茶館增加到二十多家,這里的茶館不像大都市設施豪華、精致。這里設施簡陋,一張方桌、幾條長板凳,擺上幾個瓷碗,在瓷碗里撒上幾片粗茶,幾個人圍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就開始聊起來。每到當圩四方八里的鄉親涌進這種茶館,坐下來,抓兩元錢點心,要一碗開水。這里可是信息的發布中心,可能有些人到這里來就是散散心、消遣來的,有些就是來聽聽新聞,來這里的人都是年齡偏大的人。在這里大多數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們中間有的人會洞察社會,對社會的各個方面不斷進行總結,說出來話與時俱進。如現今的社會,腳不沾地的人只能混飽肚子,一陣風吹過來就受不住;天天閑在家里玩玩手機的沒事的人,只要不傻再不行也能擋個風雨。從這些話語中得知現在人們判斷一個人行不行的標準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也只有到茶館這種地方才能聽到這些精僻的語言。還有一些人聚集一起打打小牌,賭一下,娛樂一下。
圍著街道兜一圈,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繁華。但有些該倒閉行當依舊在。如街中心的手表修理店依舊還在,在我的記憶中可能有四十多年,這里面的師傅我真不知他能否靠這門手藝生存下去。雖然它沒有往日的繁華,但它依舊按著自己的腳步往前移動——阜田老街。
選自《鄉土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