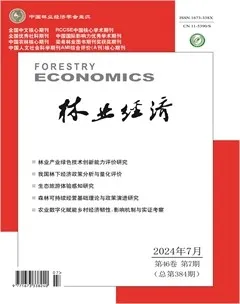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研究








關鍵詞:生態旅游體驗;感知區域;文本分析;梅里雪山
1引言
生態旅游是一種以生態資源為主要依托、以生態保護為核心、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新型旅游方式(賈田天,2024)。生態旅游資源的合理開發對于生態旅游產業持續性發展和地區自然文化的穩定性、長遠性保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朱春雨等,2022)。國際生態旅游協會把生態旅游定義為: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當地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游活動(中國生態學會旅游生態專業委員會,2008)。梅里雪山在人文、自然方面都有著典型的景觀特征,同時也是三江源保護地帶,有著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是典型的自然生態區域。旅游者作為旅游發展的切實利益相關者,其體驗感知是對旅游業本身情況的真實反映。正確認識和解析旅游者體驗感知和情感偏向,規范引導旅游者行為是保護生態旅游區自然環境和穩定旅游產業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方面。
基于此,首先,本文構建關于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的理論分析框架,探討生態旅游區旅游者體驗感知,以旅游者體驗主體角度來分析梅里雪山旅游地的旅游者體驗感知和情感體驗,以期在生態旅游地能夠更好地優化區域經濟發展與自然人文環境的良性協調發展;其次,運用文本分析法、扎根理論法和ROSTCM6軟件定性分析生態旅游地梅里雪山體驗感知區域差異和感知結果;最后,根據旅游者體驗感知結果深入討論,提出提升生態旅游發展水平的政策啟示,為今后推進生態旅游產業發展和旅游體驗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本文的邊際學術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在研究內容方面,現有關于旅游體驗的研究往往限定在特定旅游類型領域,例如只關注紅色旅游(王穎然,2022)、背包旅游(李超斌,2020)、文化遺產旅游(張瑛等,2020),徒步旅游(徐憶心等,2022)、民宿旅游、濱海旅游(陳天琪等,2021)、海島旅游(蔡禮彬等,2019)、森林旅游(呂梁等,2019)等,而本文通過全面把握生態旅游及旅游體驗感知研究的現狀,以生態旅游為切入點作為新的旅游類型體驗研究,彌補了生態旅游和旅游體驗感知方面研究的不足;第二,在研究理論成果方面,基于具身體驗理論和情感體驗理論,從生態旅游要素方面建立評價體系,評估梅里雪山區域的生態旅游體驗感知,豐富了有關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的研究成果;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傳統的旅游者體驗感知研究只側重于文本分析的單一方法,而缺乏理論建構方法的融入,通過以扎根編碼和文本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旅游者體驗感知的研究路徑。
2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文綜合參考了國內外研究成果,對現有文獻中相關領域內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進行了梳理,包含生態旅游體驗類別和體驗感知的旅游類型,總結其研究的方法、內容、思路、結論與不足等。
2.1文獻回顧
本文對相關文獻研究內容進行梳理,歸納出生態旅游體驗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體驗感知類型劃分與旅游體驗要素構建、旅游者體驗要素與影響因素研究、旅游者體驗感知情感研究與模型構建等領域。
2.1.1生態旅游體驗感知類型劃分與旅游體驗要素構建
美國學者Pine與Gilmore提出“4E體驗理論”,將游客體驗要素劃分為娛樂體驗、教育體驗、審美體驗和遁世體驗。Holbrook等(1982)指出,相比傳統的理性功能型消費,享樂體驗型消費更加關注消費行為中的“3F”,即幻想(Fantasy)、感覺(Feeling)、娛樂(Fun)方面的情感消費體驗;Julie等(1996)開發出享樂體驗、精神寧靜體驗、涉入體驗和認知體驗四維度旅游體驗模型;Sanchez等(2006)開發了旅游產品的旅游者體驗價值量表,其中包含旅游產品質量功能價值、設施功能價值、人員功能價值、價格功能價值、情感價值和社會價值六個維度;Wecl等(2019)搭建了旅游體驗的精神、文化、環境、世俗和教育五維度模型。而關于生態旅游游客的體驗感知研究不多,部分涉及生態旅游體驗的某些方面,如Tisdell等(2005)調查了澳大利亞MonRepos保護公園游客的教育和學習體驗及其對海龜保護愿望等的影響;Ballantyne等(2011)研究野生生物旅游游客體驗的動機及其對環境可持續學習的影響,調查評價了游客的感官和思考體驗及其影響因素。也有少數學者較全面地從不同角度探索了生態旅游的體驗維度(唐亞男等,2023),如Chen等(2018)發現生態旅游體驗是多維的,包括從參與生態旅游活動、與工作人員及其他游客互動等獲得的享樂、互動、新奇、舒適、刺激和安全方面的積極感受,以及因游船噪聲和煙霧等造成的厭惡、不快、沮喪、失望的消極情緒,但尚未研究這些體驗的作用結果和內在機理。
2.1.2旅游者體驗要素與影響因素研究
生態旅游是自然環境生態系統提供優美生態環境和優質生態產品的一個活動過程,本身具有環境保護和旅游活動的生態工程雙重性質(朱春雨等,2022)。生態旅游被視作在沒有被污染的自然環境區域內和優美的自然環境中對野生動植物和人文景觀進行的欣賞、學習,并獲得身心愉悅的一系列旅游活動(徐憶心等,2022)。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旅游者體驗研究已經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重視。旅游者體驗研究及其成果在推進生態旅游區治理、生態旅游區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保護及區域內經濟發展,以及助力鄉村振興等方面有著現實價值和理論意義。在廣泛關注旅游業本體與旅游業發展模式和經濟效益時,部分學者把研究目光投向旅游者體驗上,旅游體驗是旅游者行為意向的重要預測因素之一(唐亞男等,2023)。蔡禮彬等(2021)從利用難忘的旅游體驗和地方依戀感為中介探討旅游者與環境契合度會影響旅游者行為的相關關系,認為旅游者—環境契合度對難忘的旅游體驗、地方依戀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其關鍵組成部分是與經歷相關的積極情緒與感受。旅游體驗的影響因素分為兩大類:旅游者的心理因素(如情緒)和旅游地的設施或服務因素(劉相軍等,2021),對旅游體驗進行測度的新型量表在不斷涌現,已識別的結果變量主要包括旅游者主觀幸福感、目的地忠誠度、重游意愿和推薦意愿(葉艷霞,2007)等。方雨等(2017)借助用戶生成內容分析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評價和感受得出,積極感知因素體現在城市歷史人文氣息濃厚、自然旅游資源觀賞價值高、特色飲食味美實惠、當地居民直率熱情等方面,消極感知則是由于城市交通擁堵、人多擁擠、以黃鶴樓為代表的景區質價不符等因素產生。
2.1.3旅游者體驗感知情感研究與模型構建
旅游者體驗感知情感研究與模型構建主要體現在文本分析與扎根理論編碼方法結合的初探研究。譚紅日等(2021)基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認知—情感”模型,運用文本分析法提取形象感知高頻特征詞,分析旅游形象的基本認知形象;陳天琪等(2021)從游客認知、情感等方面挖掘游客的旅游形象感知,認為游客對旅游吸引物、旅游環境、旅游設施與服務、旅游體驗、旅游評價等方面形象感知的特征存在差異;苗學玲等(2021)利用扎根理論研究旅游體驗相關的新興話題,生成一些本土和原創概念,并且構建了若干概念模型和理論模型;謝彥君等(2021)認為心目中的“鄉愁”景觀具有個體建構特征,可劃分為“共相鄉愁”與“異相鄉愁”兩種類型,兩種不同的鄉愁景觀是由于立場不同而造成的景觀解讀差異,充分體現了基于體驗視角的旅游景觀打造和解讀的辯證法;金彩玉等(2020)認為滿意度影響因素主要有景區核心吸引力、旅游環境、旅游服務質量與管理水平等;李爽等(2015)采用網絡文本內容分析方法,通過建立分析類目、提取高頻特征詞,獲取游客食、住、行、游、購、娛等旅游六要素在地點選擇、內容偏好、體驗過程、服務感知等方面的感知信息;金鑫(2019)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客體驗感知與游客行為意向之間的關系,揭示徒步旅游者的群體特征;李明輝(2013)從體驗視角出發,建立基于體驗視角的鄉村游客滿意度測評模型,認為游客體驗感知由知行體驗、關聯體驗、情感體驗與感覺體驗四個維度構成,并且四項體驗感知與游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2文獻評述
生態旅游研究不僅包括旅游產業的發展,還涉及旅游者的具身層面和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物質要素層面。旅游者作為旅游活動的參與者,旅游體驗是對旅游客體的直觀真實反應,通過感知的結果能夠分析其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的內在機理。從研究內容來看,旅游類型劃分與旅游體驗要素構建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國外學者的研究注重體驗類型,認為體驗能夠帶來經濟效益,能夠產生意識反作用結果,從而影響旅游者的行為決策和重游意愿。同時,部分學者開發旅游體驗研究測度量表和指標模型,但缺乏具身層面的研究。國內研究者已經在部分領域對生態旅游體驗感知進行初步研究,多數研究立足于游客行為特征和偏好、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地方依戀感以及旅游重游意愿。從研究方法和范圍來看,研究方法以扎根理論、具身體驗、價值體驗等為主,但是研究范圍局限于傳統的公園、景點或者特定的旅游產品,主要集中于徒步旅游、森林旅游、紅色旅游、民宿旅游、康養旅游、古鎮旅游等,對于梅里雪山景區這樣具備復雜性、多樣性的生態旅游區的體驗感知研究仍然較少。為此,本文立足于生態旅游體驗感知本身,運用文本分析與扎根理論編碼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生態旅游特質以及旅游者的具身體驗層面,分析梅里雪山景區生態旅游的具體體驗內容與內在機理,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生態旅游的研究范圍、豐富了旅游體驗感知的研究內容。此外,本文注重地理學中整體性與系統性的研究范式,在旅游者體驗感知的語義網絡中,增加地理環境要素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的具體表征,并在旅游體驗要素中增加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豐富了研究內容。
3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基于具身體驗理論與情感體驗理論以及生態旅游概念界定,本文提出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理論分析框架并進行研究假設,在此基礎上運用文本分析、扎根理論等研究方法對生態旅游體驗感知內在機理和作用結果進行分析。
3.1理論分析框架
生態旅游的本質是一種體驗活動(祁寧等,2018),這種體驗感就是公眾對體驗地的一種公眾體驗感知(吳麗霞等,2007)。體驗感知測量可分為服務與設施認知、空間認知、景觀認知、體驗認知4個維度(馮曉兵,2017)。具身體驗理論是旅游者身體處于旅游環境中而產生的直觀身體感受,來源于視聽結合后對自然人文環境的心理認知過程,表現為一個感官過程最終產生的感知結果(朱宇軒等,2023)。通過身體感知和經驗最終影響到旅游者的思維情感和行為,通過這樣一個動態的作用和反作用表現在一定的旅游環境中(陳欣等,2021)。旅游者體驗感知受到旅游環境影響,旅游環境特征被旅游者體驗感知所呈現,旅游者置身于旅游環境中被旅游要素所吸引,其身心過程發生的變化通過語言文字進行表征。對于旅游者置身于旅游環境中產生的旅游體驗所表達的一般性文本材料進行歸納概括,進行普遍性的總結。根據文本材料提取出現頻率高、具有一定代表意義的特征詞匯作為詞匯矩陣,詞匯中涵蓋心理活動表現、旅游者語言結論、自然人文要素等方面(蔡克信等,2022)。高頻詞能客觀反映旅游者心理感知結果。梅里雪山作為生態旅游目的地,其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多樣性顯著,雪山景觀要素會作為旅游者體驗感知的關注點,且影響旅游者的感知結果。因此提出假設H1。
H1:梅里雪山作為生態旅游目的地為旅游者所正向感知。
生態旅游目的地是旅游者行為決策選擇的結果,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是對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各個要素進行感知,從而獲得不同的旅游體驗(王穎然,2022)。當進入特定的旅游環境后,旅游者對于最初的旅游決策地感知是否為正向(關陽等,2021),其結果不僅能反映出生態旅游業發展的實況,也能反映旅游地在旅游者認知中的具體表征,加之其內在機理更能凸顯旅游地之間的或是內在的實質聯系(沈鵬熠等,2023)。旅游者對于旅游要素的感知結果能影響旅游者的旅游體驗,旅游體驗是表現在心理上的主觀感受和身體上的客觀活動,旅游體驗的正向與否直接影響旅游者情緒,進而影響旅游者的滿意度、重游意愿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吳恒等,2022)。在旅游者體驗要素中主要呈現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生態旅游的旅游地要素不僅是吸引旅游者的直接物質或非物質實體,也是旅游體驗研究要素分類的主要來源,其存在變化是影響旅游者情感體驗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假設H2。
H2: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旅游者的情感體驗存在正向顯著性影響。
3.2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是文獻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將非系統和非定量的符號內容(如文本、圖像、圖片等)轉化為定量數據,并利用這些數據對材料的內容進行定量分析、判斷、推理(方雨等,2017)。本文采用網絡語義文本分析方法整理出情感語義、網絡語義并分析其核心語義和外化語義,進行四個主體景點差別化和景區凝聚特征共性分析,采用文本信息收集軟件OCTOPUS對于不同的APP軟件上有梅里雪山景區旅游活動經歷的旅游者在網絡上的評論進行大數據爬取收集,對收集到的不同時間段的網絡評論、游記進行篩選整理,利用Excel軟件的countifs和sumifs進行數理統計分析,得出不同類別的網絡語義詞匯和高頻詞矩陣,匯總不同類別的語義情感表達類別,用ROSTCM6總結出類別表達相似或者相近的網絡語義詞匯,生成語義網絡分析圖。
扎根理論由美國學者Glaser和Strauss在20世紀60年代共同提出,承襲了實證主義傳統,反對以純思辨構建理論,提倡從經驗材料出發“自下而上”地構建理論。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它已經成為包括旅游研究在內的眾多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Glaseretal.,1967),適用于對尚未被完全了解的現象或概念進行探索且強調對過程的關注,與本文的研究問題相契合。借鑒苗學玲等(2021)的做法,本文以大量的文本材料作為原始數據,對文本材料進行編碼從而構建理論特征詞,進而分析生態旅游的旅游者體驗感知內容。
4數據來源與案例地概況
為保證文本內容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本文先對搜索到的大量文本進行篩選,僅采納游客發布的游記、點評,并對其經歷的真實性和親歷性進行初步鑒別,剔除有廣告宣傳、虛假不真實的文本;同時要求評論游記必須較為完整地記錄旅游過程,對自我感受和情感有較為詳細的描述,剔除有明顯虛假廣告、復制的重復網絡評論文本,再對整體網絡和情感語義進行分析。
4.1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收集源自同程旅游、攜程旅游、抖音、窮游APP、去哪兒旅行等應用軟件上的網絡熱評,為保證數據的客觀性有效性,對不同軟件的數據進行批量、均等化收集處理和對比分析,數據選取時間段為2010—2023年。本文在旅游網絡平臺上以“梅里雪山”“旅游體驗”“德欽縣生態旅游”等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獲取網絡點評等網絡文本及照片,再使用Office軟件進行文本整理;利用信息爬取軟件OCTOPUS獲取了所有軟件的評論和有關游記,利用Excel進行數據歸納分析統計并刪除無關字段信息,例如:“系統默認好評”“游客無評價”等相關字段,共收集有效網絡評論4345條、字數287836個。
原始文本數據典型事實分析,如“大理雙廊,麗江,梅里雪山,雨崩村,隔日幸運地日照金頂后脫離團隊,放棄了明永冰川,直奔雨崩村,一呆就是4天,我知道,我贊同你的看法,雨崩確實是天堂,可是門票收得相當不合理。如果是雨崩村的村民收了,收去改善他們的生活我也覺得OK,可是他們并未從中得到任何利益,而且那么多的游人去踐踏他們的圣地,破壞了他們當地的生態,在上下雨崩中的那個河谷旁我看到好多垃圾,也不見那些得利益者有什么治理,所以我認為這個門票不應該收。”首先初步研判該文本信息,進行特征詞聚類,然后進行歸類分析,該段文本信息中包含“大理雙廊、麗江、梅里雪山、雨崩村”等區域特征詞群和“那么多的游人去踐踏他們的圣地”等情感態度特征詞,為此需對文本進行篩選,整理出具有代表意義的旅游者評論進行分析。
4.2案例地概況
梅里雪山景區有著最為原始的自然風貌和最為古樸的藏區人文景觀,是一個生態旅游研究的典型案例地,選為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研究的區域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梅里雪山在藏族地區被當地居民視作保護一切生靈的神山,藏區居民是靠著梅里的庇佑才能世代繁衍生息。在藏區,原始的生活習慣和獨特的神話信仰成為了當地的地方性知識(吳坤鵬等,2021),間接約束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和行為習慣,人地關系被添加了一道獨特的神話色彩,這也是受到越來越多游客青睞的原因之一。景區內的雨崩村、飛來寺、明永村都是其代表性的景點。梅里雪山地區是藏族聚居區,也是全國重點扶貧地區之一(蔣凱峰等,2020),藏區文化保存最為古樸原始,自然景觀極具震撼,自然與人文相結合的旅游體驗是景區的一大旅游特點。
4.3核心數據描述性統計分析
詞頻能夠反映某一詞語在整個文件或語料庫中的重要程度,通常這一詞語的重要程度與其出現的頻次成正相關(方雨等,2017),詞頻矩陣表通過降序的方式排列文本信息中高頻率詞匯,通過聚類后的詞群可以客觀分析意義相近的詞語,以便進行旅游體驗要素分類,從而進行評價。高頻詞匯匯總表如表1所示,“梅里雪山”出現2783次,詞頻最高,因此是旅游者體驗感知中最核心和最具代表性的景觀旅游要素。
5經驗性結果與分析
本文基于前文的生態旅游體驗感知理論分析框架和數據來源,從體驗感知區域維度、生態旅游體驗要素內容維度、旅游者情感體驗維度對梅里雪山的生態旅游體驗感知進行分析,深入探究生態旅游地的旅游者體驗感知內容和內在機理。
5.1梅里雪山旅游體驗感知區域分析
通過對收集文本的篩選整理,歸納得出旅游者體驗感知區域,進行匯總匹配相關的意義詞群,對總的詞群進行分析、計算基數按所占比例得出結果。行為地理學認為存在著環境意象,且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對旅游點的吸引力真正起削弱作用的是感知距離而不是客觀距離。對于旅游者而言,感知是行為的基礎,行為又豐富了感知,直接或間接的信息都會增強旅游者的感知。本文旅游者對于梅里雪山景區的外在感知區域分屬于出發前,對于整體區域的認知和決策選擇,內化核心區域是旅游者置身于景區觀賞景觀的直觀感受范圍,外化邊緣區域是旅游者對于景區周邊景點的邊緣性認知,精神升華區域是旅游者思想意識的直觀感受、表現為身體和心理的愉悅。通過文本選取示例句子、對整體文本篩選整理并計算得出旅游者體驗感知區域分類,如表2所示。體驗內化核心區域是游客感知的核心區域,由外在感知區域、外化邊緣區域、精神升華區域共同凝聚而成,包含游客感知深度與體驗美好程度。“日照金山”“卡瓦格博”“梅里雪山”是游客的物質實體感知內化為精神的直觀感受。由表2中四大區域關系可以看出,游客對于體驗感知源于不同區域的感受水平差異,主要影響因素有景觀要素、距離、天氣、海拔高度等。
外在感知區域是旅游者自身在未出發前對于景區的整體形象感知,一般主要通過對景區相關資料的收集與了解,網絡評論的獲取也是了解景區內部狀況的途徑,旅游者選擇目的地時會對景區基礎設施、地區位置、交通條件、特色景點做一個初步了解再作出旅游決策。從旅游者評論:“見過了南迦巴瓦、珠穆朗瑪、岡仁波齊全貌,但我最想看的還是梅里——卡瓦格博”,可以看出對于梅里雪山的旅游目的地選擇,旅游者會從自己已有的其他景區認知中尋找共同點并與之相比較,初步的旅游體驗外在感知區域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區域。外化邊緣區域是旅游者置身于旅游景區之中對于周邊景觀要素的整體感知,主要來源于感覺器官對美麗景色的遠距離或者近距離獲取,由周邊的關聯事物因素在大腦中形成的關聯性區域。該區域或是景點名稱,或是景觀名稱,或是周邊行政區劃,例如,“進梅里雪山或雨崩的重要樞紐的飛來寺觀景臺,可觀神瀑,冰湖的雨崩景區,低緯度熱帶季風海洋性現代冰川的明永冰川景區。”“梅里雪山是一座神山,和西藏的岡仁波齊、青海的阿尼瑪卿山、青海的尕朵覺沃并稱為藏傳佛教四大神山。”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周邊事物會相聯結形成一個外在感知區域網絡。“岡仁波齊”、“阿尼瑪卿”、“尕朵覺沃”與“卡瓦格博”是藏族區域內的著名山脈,在游客觀念中形成一個意識中的地理區域,每個游客對于外化邊緣區域的感知程度是不同的,由于體驗者本體差異和對外在事物形象的信息獲取程度不同,導致旅游者對于旅游區域的體驗差異不同。
精神升華區域是外在感知、內化核心、外化邊緣等區域的共同表示。旅游者在特定的景觀面前所表現的情感差異不同,來源于景觀對于自身的啟發或者觸動,比如,“美麗的日照金山就是梅里雪山露出的絕世芳容,能親眼看見,就是一種幸福,從未有過的震撼,當見到它的那一刻,圣潔、威武,感動地流淚了。”旅游者直接觀賞的景物對于自身精神的啟發與觸動來源于對日照金山美景的感知、體驗。精神升華的好與壞直接影響旅游者的整體體驗感,對于旅游區產業發展至關重要。梅里雪山依靠高山雪景吸引無數游客前來的一個客觀原因在于獨特的景色能幻化為人精神中的信仰,是對所有內在外在、物質與非物質、心理的一個升華過程,能對游客的行為觀念進行潛在的指示與引導,從而間接發揮旅游地的教育功能。
5.2語義網絡體驗感知分析
體驗感知基于對旅游者的整體網絡評價文本進行文本低頻詞處理、過濾無意義詞、提取特征詞,加工處理并進行語義歸納匯總得出的網絡文本分析圖;對飛來寺、雨崩村、明永村、梅里雪山四個著名景點分別做了可視化處理,處理結果根據語義文本詞頻數量和關聯程度顯示一個發散狀和內環閉合狀的語義網絡圖,如圖1至圖5所示。語義網絡展現了一個區域的游客體驗關注頻次,出現次數越多說明游客整體關注度比較集中,游客內在體驗感知度越密切。
5.2.1區域內語義網絡體驗感知差異分析
(1)飛來寺語義網絡分析。進入飛來寺的游客對于景區內部事物關注較高,飛來寺成為游客關注的主要核心區域。但是存在兩個地方性名稱是游客關注的次要核心區域:香格里拉——梅里雪山之間是飛來寺游客關注的次要核心區域。該區域中心展現的是來自飛來寺的游客體驗與香格里拉、梅里雪山體驗關聯度強。原文示例:“1.香格里拉—奔子欄—飛來寺(191km)宿:飛來寺(海拔3400m)—長江第一灣—石鼓鎮—白馬雪山埡口—霧濃頂十三白塔—飛來寺;2.離開香格里拉之前還選擇了普達措國家公園里的悠幽莊園,據說張杰和謝娜的婚禮就是在這里辦的,又是一個大大的驚喜,風光極美!德欽選擇了飛來寺明珠酒店,在房間里就可以看到卡瓦格博,應該說性價比挺高,但是我們在主街上轉了一圈之后覺得梅里往事會更好,當然價格也要貴不少。”主要原因在于出行游客大多按照自己規劃的路線旅游,飛來寺游客大多由香格里拉轉程過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飛來寺是觀賞梅里雪山的絕佳網友推薦地,因此飛來寺與梅里雪山之間形成內核心與外核心區域呈現在游客體驗感知中。明永冰川——日照金山——白馬雪山——雨崩村——金沙江之間形成一個語義閉環。飛來寺的游客對于景區周圍的事物形成一個觀念上的區域,即外化邊緣區域,原因在于飛來寺景點距離白馬雪山、雨崩村、明永冰川的距離效應、景點與景點之間的吸引作用。
(2)雨崩(上/下)村語義網絡分析。雨崩村外圍區域形成徒步、冰湖、梅里雪山、雨崩的次要核心詞匯,說明內部游客關注的是冰湖美景與梅里雪山。對于雨崩上村的旅游者來說,選擇徒步旅游是雨崩村游客的主要體驗方式,外圍詞匯呈現的是步進、登山、前往、時間、腳下、世外桃源、到達,表明雨崩村游客體驗關注點在于徒步旅行和徒步旅行的方式。原因在于雨崩村的地理自然環境和地方性文化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用在游客外在感知和體驗中。雨崩村是一個徒步者的天堂,大多數游客都是被其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景觀吸引與外在感知左右。較長的線路與不同的自然美景是游客親近自然、放松身心、挑戰自我的一種獨特方式。對于徒步旅行愛好者來說,雨崩村徒步線路是一個絕佳路線。原文示例:“1.雨崩啊太美了,雨季的高山杜鵑很美哦,三天走完了,冰湖線、神瀑線和尼農線、累死了~村子聽說要統一規劃改造,下次來的時候希望會更好。雨崩的幾天畢生難忘,每天都要死一次然后第二天再次重生。2.如果你想去雨崩徒步,你需要知道,這不是野炊,也不是秋游,這是一次滌蕩心靈的艱難旅程,也是一次朝神圣之旅,他什么都可以是,畢竟那就是天堂。3.海拔較高,根據自己身體條件,選擇要不要提前服用紅景天,徒步過程中盡量不要劇烈運動,慢慢走,一邊感受周身美景,一邊也能適應高反!酥油茶對高反也有一定的幫助。”旅游者對于雨崩村整體體驗源于對徒步的愛好,徒步對生態旅游區是一種最環保的方式,不僅能保護環境,還能一定程度上增加當地經濟收入。雨崩下村是游客住宿與休憩的一個選擇地,對于剛到達雨崩景點的游客,核心詞匯呈現:梅里雪山——雨崩村,表明前來旅游的游客不僅對雨崩村感知比較集中,而且對梅里雪山也呈現核心語義詞,原因在于在游客回憶體驗中展現的是,對于剛剛抵達的游客,雨崩下村游客更加關注住宿條件和飲食條件;心理情感的外在感知區域呈現的是:香格里拉——大理——麗江——西藏——昆明——卡瓦格博——客棧——徒步,對于周邊范圍內地區感知與體驗,語義網絡顯示游客可能來自于景區周邊著名景區或者已經有了云南其他景區游覽的經歷,來雨崩村的主要動機是關注徒步旅行。原文示例:“1.雨崩上村——大本營——冰湖——返回雨崩村(住宿)。2.跑了一大段蜿蜒曲折的山路,一路顛到大理;接著玉龍雪山索道修整關閉,通往瀘沽湖道路施工,雨崩村一帶修路沒法出行。”
(3)明永村語義網絡分析。在語義網絡圖核心區域最顯著的是旅游者對于明永冰川的體驗程度,明永村因為冰山而得名,在藏族地區被視為圣地,兩千多米的冰覆蓋著,在地表形成宏偉壯麗的景象,是獨特的自然地貌,旅游者把自身體驗寄托在冰川之上來獲取價值認知。在冰川下的蓮花寺是藏族寺廟,供奉著傳統的信仰,形成了人文要素與自然要素的結合。中間詞匯顯示飛來寺、香格里拉、日照金山和梅里雪山,表明明永村旅游者對于周邊景點關注度較高,游客體驗認知中對于梅里雪山與明永冰川之間形成一個連帶的語境。海拔——公里——小時是游客體驗感知的外圍次要核心詞,游客關注度比較高,表明游客對于明永冰川景點、外在感知區域存在對于物理空間、距離的認識和體驗,原因在于:明永冰川所在位置與景區入口之間距離較遠,海拔高度比較高,旅游者徒步時間比較長,因此旅游者體驗語義網絡中顯示為次要位置。原文示例:“1.體力好的不像話可以一直徒步,不過總計10公里的山路走下來估計你就沒力氣下山。2.@不叫海綿的寶寶:在看得見的時間里,它是卡瓦格博臂彎里凝固成冰的眷戀,在看不見的時間里,它是神山腳下正在逐漸消亡的冰川。3.2021年全程徒步上去過,十二點上去五點下來,中間還找了半天樓梯。”原文本顯示,冰川是游客體驗到的核心語義詞匯,海拔高度因素影響的旅游空間距離是旅游體驗的另一個要素,也是影響因素差異之一。
5.2.2梅里雪山旅游體驗語義網絡共性分析
梅里雪山是整個景區的代名詞,從上述四個地點語義網絡分析中都呈現“梅里雪山”“日照金山”“卡瓦格博”的核心詞匯或者次要核心詞匯。通過梅里雪山語義網絡展現的雪山,仍然是整個旅游者體驗的核心區域與關鍵詞,說明梅里雪山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為核心體驗物質實體,是旅游者關注的核心所在。在其他的景點與雪山關系之間、旅游者關注度和體驗上,梅里雪山都是關注和體驗到的主要旅游景觀和景點中心,因此驗證了假設H1。旅游景區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呈現:外在感知區域——內化核心區域——外化邊緣區域——精神升華區域,都是以梅里雪山為核心,梅里雪山是所有景區景點的核心,雨崩、飛來寺、明永是梅里雪山景區的外延。在語義網絡顯示可以看出:梅里雪山以雨崩、麗江、香格里拉為次要核心詞,選擇徒步路線是旅游者體驗的旅游方式,觀賞的雪山——神山——卡瓦格博是旅游者精神升華區域體驗到的物質空間。原文示例:“1.卡瓦格博日照金山的美不是用任何攝影產品能夠留下的,只有身臨其境親眼所見那短暫幾分鐘的日照金頂,才能真正體會到阿尼卡瓦格博為什么是雪山之神,為什么會是全世界公認最美的雪山。2.還好你略過了玉龍雪山和納帕海,那里沒意思,梅里才是重點[比心]曾經和你一樣的經歷。3.2020年11月份也是第一次去梅里雪山連續兩天看到了日照金山,感覺真的是幸運。”梅里雪山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為:美麗——震撼——滌蕩,是景區自然景觀對旅游者的內心世界的沁入作用,另外由于卡瓦格博本身的神化色彩,提升了旅游者的體驗程度中表現出身心的神化感,在馬天(2019)認為的旅游體驗中:在體驗強度方面,既包括暢爽這類高喚醒的體驗,也包括低喚醒的放松(relaxation)、內心寧靜(peaceofmind)等;在效價上,即包括由愉悅、興奮、新奇等積極情感產生的積極體驗。
5.3旅游者情感體驗分析
情感分析作為當前自然語言處理領域中最為活躍的研究之一,是指對在線評論文本進行情感分析,判斷文本的情感類型是積極、消極還是中性或識別用戶的觀點是“贊同”還是“反對”(程馨等,2019)。
本文通過ROSTCM6軟件對梅里雪山景區網絡評論文本進行了情感分析,得出旅游者情感統計分類,結果如表3所示。表3結果表明,旅游者對于梅里雪山景區整體體驗情感表現為積極,在提取的總樣本中高達568條正向積極評價,占比67.38%。原文分詞詞匯大多表現為:“1.雨崩村是傳說中的世界上最美麗的村莊位于梅里雪山的五冠峰腳下景色優美民風淳樸是名副其實的世外桃源。2.小魚的攝影技術真是讓我滿意的很想要什么樣的都能拍出來明天進雨崩村精彩繼續。3.徒步的時候往上看就是念慈母峰景色優美民風淳樸簡直就是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在游客體驗中對整體體驗感覺比較積極或者中性,表明景區內游客對于景區景色,整體基礎旅游水平滿足于預期外在感知水平。但是也有部分游客在旅行過程中對景區旅游持有消極情緒,例如“1.要進入上雨崩村必須經過150根電線桿其中102根是上坡路合計12公里數到102就到了南宗埡口而下坡的48根電線桿也是6公里的痛苦;2.到雨崩村的路也是磕磕絆絆我們請了一個當地的藏族阿姨帶我們上山一路上不習慣走山路的我因為山路陡峭加上雨雪路滑。”旅游者中消極情緒評價有78條,占比為9.25%。從總體呈現數據分析來看,梅里雪山景區旅游者積極情緒大于消極情緒,旅游過程中對于景觀欣賞、徒步旅游和基礎設施服務方面大部分表現為積極或者中性態度。原因在于:一是物質因素,由于景區面積過大,物理距離比較遠,加上旅游方式是徒步旅行,路線大多是在落差較大的山地環境,導致徒步時間過程太長,景區內氣候多變也是影響旅游者心情和體驗感的具體原因;二是旅游者自身因素,對于景區景觀、基礎服務設施的個體差異化感受不同。
5.4旅游者體驗要素統計分析
按照生態旅游地旅游要素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呈現的數量最多的詞匯加以匯總分析得出高頻詞。依據孫希瑞等(2022)的分類評價體驗體系,根據梅里雪山旅游者體驗文本詞匯歸納整理出旅游感知體驗評價體系語義文本特征詞表。旅游者體驗要素是對旅游環境要素的直觀感受表達,旅游者體驗要素的文本分析通過詞頻變現呈現,根據詞頻能夠直觀分析出生態旅游者的旅游體驗要素感知具體表征。在旅游者體驗要素中,生態旅游具備一定的區域性,各個區域之間又具有關聯性。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區域感知中處于中心區域,在旅游者具身體驗層面為旅游者所正向感知。旅游地的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是影響旅游者體驗的主要因素。生態旅游具備一定的獨特性和綜合性,豐富了旅游者體驗感知的內容,增強了旅游者的獨特旅游體驗。
本文從4個主類目、12個次類目對高頻關鍵詞進行了分類歸納,旅游者體驗評價體系分類如表4所示。4個主類目分別是旅游吸引物、旅游環境、旅游感知和旅游設施服務。從旅游吸引物來看,梅里雪山景區主要在游客體驗感知中呈現的是: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白馬雪山等獨特的自然景觀和經幡、寺廟、喇嘛、酥油茶、祈福等人文景觀(含風情民俗)要素,旅游者對于旅游體驗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感知程度和頻次最多,綜合上文所述為此驗證假設H2。體驗活動的表現方式與自然景觀相關聯,如朝圣、徒步、觀賞等核心高頻詞匯。從旅游環境來看,旅游者體驗來源于梅里雪山的原生態自然環境,體驗感覺:幽靜、原始、震撼、生態。但是旅游者對于景區區位條件整體感知差異明顯,旅游者對于周邊著名景區感知體驗程度較深,在大理、麗江、香格里拉、西藏之間形成了一個感知區域。梅里雪山的旅游者或有如上著名景點區域的旅游體驗。大理、麗江、香格里拉、西藏之間形成旅游區域連帶效應,對于初次來滇或者進入滇西北的游客有景區輻射效應。生態旅游區觀賞景物、景觀相近或者類似,如:玉龍雪山、梅里雪山;大理古城;麗江古城。
6研究結論、討論與政策啟示
旅游目的地體驗感知的形成是心理參與作用的過程,是認知形象、情感形象、整體形象反復融合的(譚紅日等,2021)。旅游目的地體驗感知,即游客對某一旅游目的地的綜合感知和評價,是提升內在與外在精神價值的隱形價值(關陽等,2021)。游客體驗具有現場性、情境性、流動性等特點,為獲取真實游客體驗,必須深入旅游活動發生的第一現場(馬天,2019)。基于此,以具身體驗理論在現實旅游體驗感知研究中的具體應用,生態旅游地梅里雪山旅游者網絡評論作為研究內容,從旅游者區域感知、網絡語義、情感體驗、高頻詞共現四個維度分析旅游地具身體驗感知,對梅里雪山的旅游者體驗感知進行了研究,得出研究結論并進行討論,最后針對結論提出政策啟示。
6.1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建立語義相關聯的網絡和情感分析圖,以旅游者具身層面的體驗文本材料為基礎,建立了梅里雪山生態旅游體驗評價的景觀要素,得出3點結論。
(1)生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區域感知中處于中心區域,在旅游者具身體驗層面為旅游者所正向感知。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梅里雪山在景區范圍內成為旅游者關注最高的熱點。雨崩、飛來寺、明永是旅游者感知的次要關注點,旅游者對于自然景觀要素的整體體驗表現為積極。梅里雪山景區整體區域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呈現;外在感知區域(如:空間距離、道路交通、基礎設施服務)——內化核心區域(如:卡瓦格博、梅里雪山、日照金山)——外化邊緣區域(如:雨崩、明永、香格里拉、四大神山)——精神升華區域(如:朝圣、震撼、優美、寧靜、神圣)。
(2)生態旅游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生態旅游者的情感體驗存在正向顯著性影響。梅里雪山景區旅游者積極情緒大于消極情緒,旅游過程中對于景觀欣賞、徒步旅游、基礎設施服務方面大部分表現為積極態度。生態旅游景區面積相對較大,物理距離比較遠,旅游方式是徒步旅行,路線大多是在落差較大的山地環境,因此徒步時間太長以及景區內氣候多變會影響旅游者心情和體驗感。隨著旅游者旅游距離增加、景區自然環境改變和景觀差異,旅游體驗情感差異較大,旅游者在景區旅游活動中表現的積極情緒大于消極情緒。
(3)生態旅游各個區域之間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大理、麗江、香格里拉、西藏之間在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形成了旅游體驗中的區域連帶效應,不同的旅游景區之間會對旅游者產生吸引,旅游者具身體驗層面的旅游要素對不同地區間的旅游發展形成連貫效用。
6.2討論
根據本文得出的主要結論,對比已有研究成果,對生態旅游體驗感知進行三點討論。
首先,通過質性分析驗證了旅游目的地與旅游者體驗感知的關系,以及生態旅游區域內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對旅游者情感體驗的影響。本文在體驗感知研究層面注重于旅游者對于旅游地的具身體驗層面,與蔡禮彬等(2019)研究旅游者具身層面的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相似,與馬天(2019)、程馨等(2019)、施思等(2021)、沈鵬熠等(2023)關注旅游者的情感體驗研究相同,區別在于價值認知、體驗類型、滿意度、旅游目的地、重游意愿。
其次,本文對旅游者體驗感知進行了旅游體驗要素中的區域感知進行拓展,與關陽等(2021)對于旅游目的地的區域形象感知研究相似。生態旅游體驗感知是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體驗結合于一體的研究,與呂梁等(2019)、李超斌(2020)對于旅游者與旅游目的地之間的影響、偏好研究不同。生態旅游區作為一定的特殊旅游區域,有著生態屬性的一面和旅游發展潛力的一面,生態旅游業的長遠發展和體驗感知研究要注重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協調。
最后,旅游者體驗感知中呈現區域的連接性,整體性、系統性、多樣性以及我國生態旅游發展區域之間的連接性與蔣凱峰等(2020)僅關注旅游地和文化景觀之間的保護研究不同,區域之間在旅游體驗層面顯示的連接性特點對于旅游體驗感知研究在內容上可以為未來開拓新的研究視角。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方面,僅限于景區內部景點之間對比分析,在各個景區之間缺乏旅游者體驗感知對比分析;另一方面,在旅游者體驗文本數據選取方面存在時間上分布不均、缺少線下與線上相結合的研究數據。在未來需要拓展研究范圍、獲取更加完整的數據來完善研究體系、支撐研究結論。
6.3政策啟示
生態旅游在我國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出冰雪旅游、觀光旅游、森林旅游、濕地旅游、露營地旅游等種類繁多的旅游方式。旅游體驗研究也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梅里雪山地處滇西北腹地,地理位置較遠,但是其生態旅游資源受很多旅游者追捧,旅游體驗感知也呈現其獨特性和普適性,根據本文研究得出的結論和討論,對于我國生態旅游業發展與自然人文環境的良性協調發展方面,給出兩個層面的政策啟示。
從全國層面來看,(1)發揮旅游者在生態旅游業發展和保護中的主體作用。旅游者作為旅游活動的主體,既是旅游活動的參與者,也是旅游環境的保護者。積極引導、規范、教育生態旅游者,使其自覺承擔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樹立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營造良好的生態旅游氛圍。生態旅游地自然環境相對脆弱,人文環境相對特殊,區域內有著豐富的動植物,因此要杜絕各種破壞環境的違法行為,提升其對生態旅游地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義務和自我教育意識,對于出現的破壞環境行為要加以制止和勸導,引導其積極配合協同單位進行山區、林區保護。(2)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管理功能。各地方政府應加大對生態旅游地內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打造良好的生態旅游條件,擴大生態旅游安全行為意識的教育宣傳范圍,提升生態旅游地的基礎服務質量和水平,對旅游區域內的自然災害加強監督和防控,做好應對突發情況的救援預案,加強景區內電子信息的監控和防控,杜絕一切損害自然人文環境和旅游者利益的違法行為,確保生態旅游環境的良性發展。區域內旅游業規劃需要各方共同促進、協調發展,保證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同時引進相關生態旅游業、林業治理人才,培育優秀的本地服務人員,不斷提升生態旅游業發展水平。
從梅里雪山生態旅游地層面來看,(1)相關政府部門應協調好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和生態旅游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打造具有區域性、綜合性、獨特性的生態旅游產業。另外,需加強地區旅游人員流動性的監控和防控,切實做好基礎性服務工作,完善基礎服務設施和旅游信息服務平臺,正確處理生態旅游地的旅游者與居民關系,促進文化交流與互通。(2)提升旅游者的生態環保意識,樹立正確的生態旅游理念,引導規范生態旅游者的行為方式,進行生態旅游地的安全和防范意識宣傳,不斷提升梅里雪山生態旅游地的生態旅游產業發展水平,促進地區生態旅游經濟效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