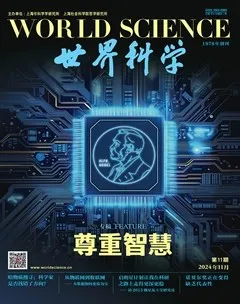諾貝爾獎正在變得缺乏代表性

科學界的地理分布正在發生變化。因此,必須擴大有資格提名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范圍。
每年一度的林道會議將青年科學家介紹給諾貝爾獎得主們
10月正是諾貝爾獎揭曉的時段,歷史表明,最有機會獲獎的科學家是來自歐洲或北美的男性。如果你出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你收獲斯德哥爾摩發來的邀請函的最佳機會就是在北美或歐洲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并搬去工作地。
這是2024年10月《自然》(Nature)發表的一篇專題文章《如何贏得諾貝爾獎》中得出的結論。分析還指出,取得獲獎科學成果的團隊往往與先前的獲獎者有淵源。
諾貝爾獎評選機構的代表向《自然》表示,他們一直在不斷努力,以更好地認可科學界的多樣性,并且確實取得了顯著進展。在整個20世紀,只有11項諾貝爾化學獎、物理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女性。而在2000年至2023年間,共有15位女性獲諾貝爾科學獎。
縱觀諾貝爾獎的歷史,只有10位獲獎者出生在目前被世界銀行歸類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的國家,而且其中大多數人在獲獎時已經移居北美或歐洲。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只是反映了科學領域中權力與資金分布持續多年的現實情況。但是,這些刺目的數字提出了一個問題:諾貝爾獎——以及其他高知名度的國際獎項——如何能夠反映當今世界科學的深度與多樣性?
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自然指數數據庫追蹤的“機構對自然科學和健康科學期刊的貢獻”排名,目前全球排名前十的科研機構中有七個位于中國。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10位出生于中國或擁有華人血統的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
一個本質上的障礙在于諾貝爾獎那基于邀請制的提名程序。根據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某些特定類別的個人無需許可就能提名獲獎者。這些人包括:往屆獲獎者,瑞典、丹麥、芬蘭、冰島和挪威的大學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和相關的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成員。其他大多數人則需要一封官方邀請函才能參與提名。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委員會秘書托馬斯 · 佩爾曼(Thomas Perlmann)在接受《自然》采訪時表示:“我們正在向越來越多來自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傳統學術研究中心以外地區的個人發出邀請。此外,我們還在積極物色更多的女性和青年科學家成為提名人。”提名過程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委員會會向大學教授、院長和領導發送信件,請他們給出有資格提名潛在獲獎者的科學家名單;然后,委員會將要求選定的科學家提交提名。
諾貝爾化學獎和物理學獎得主由位于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選,而生理學或醫學獎則由卡羅林斯卡學院頒發。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生物化學家、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秘書彼得 · 布熱津斯基(Peter Brzezinski)表示,瑞典皇家科學院已經確定了大約1250所大學并發函聯系。由于處理能力有限,每所大學平均五年才能收到一次邀請。
人脈提供者
如果諾貝爾獎組織希望與更多人建立聯系,就必須提升處理此任務的能力——或是接受外界的幫助。多年來,不少國際科學網絡向《自然》期刊表示愿意協助,這些網絡掌握了大量而多樣化的潛在提名人名單。它們包括設在肯尼亞內羅畢的非洲科學院(AAS),覆蓋全球的科學院網絡“國際科學院聯合組織”(IAP),代表250多個科學聯盟、協會和其他組織的國際科學理事會(ISC),以及世界科學院(TWAS)。
世界科學院是一個面向頂尖科學家的研究員網絡,于1983年由已故的巴基斯坦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卜杜勒 · 薩拉姆(Abdus Salam)領導的一群研究人員成立。現任世界科學院主席夸萊莎 · 阿卜杜勒 · 卡里姆(Quarraisha Abdool Karim)表示,該組織擁有1400名研究員,大多在中低收入國家(LMICs)的大學任職,他們完全有能力推薦提名人選。只需要邀請他們即可。
正如丹尼爾 · 謝弗(Daniel Schaffer)在他2005年出版的《世界科學院二十年》中所寫的那樣,當該機構在40年前成立時,許多來自中低收入國家的研究人員只有兩個選擇:“專注事業卻背井離鄉,或是留在故鄉卻犧牲事業。”如今,正如阿卜杜勒 · 卡里姆所言,隨著科學不斷發展壯大,超越了以往的權力中心,卓越的人與研究無處不在。
毫無疑問,諾貝爾獎頒獎機構已經意識到需要做些什么,也意識到了不斷擴大提名人范圍這一任務的龐大規模。變革需要時間。許多獲獎者等待了幾十年才得到認可,盡管這種歷時多年的滯后現象并非必然;有些人則是在做出獲獎發現的幾年內就得到了回報。諾貝爾獎的頒發組織應當接受外界幫助,以物色有資格提名的人選。一個獎項不能反映世界是一回事,但不能反映科學界的現實則是另一回事。
資料來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