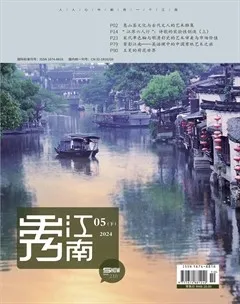“江蘇六人行”:詩歌的實驗性創造(上)
編者按:
“江蘇六人行”是王學芯、中海、龔璇、鄒曉慧、成秀虎、王明法六位長三角蘇南地區實力詩人組成的詩歌創作群。這個詩群秉持一致的新現實主義觀念,以各自不同的詩意姿態和語言風格,在繁蕪的意識莽林中,驅除種種陳腐的藩籬和偽設的邊界,努力開拓一條純凈之路,以抵達心靈最本真無飾的境界。他們的詩作都有明顯的實驗性,縱放情感的翠龍和思想的騰驥是他們不竭活力的來源。這個詩群目前已有較大的影響,期待他們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刊將分3期發表六人詩作。
抵達之謎
王學芯/文
午夜火車
穿過遙遠的距離 空空車廂
萬里與一里的蕩然無物之感 輕得浩渺
十一點 十一點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
光從窗的黑色玻璃上劃過
頭微微傾斜 身子下沉
疲倦使人忘了所有人的先后和差異
覺得此時的我
跟無數心理上的自己組成我們
交纏一起 傳遍手臂的感覺 通過頸脖
抵及臉和干燥嘴唇
斑點閃閃的燈光
如同內心深處念頭
一齊經過這片秋意深厚的土地
發出一聲闌珊之處的靜脈長笛
車廂又窄又長 看得見或看不見的事物
空間只剩下末端的輪廓
抽走了 一個個站點
一排排樹
一座座隧道 和那
五顏六色野草的山谷
空氣里的味道
王學芯/文
空氣中耽擱下來的味道
流動著 風干著 覆蓋一切
其間感覺到的鼻腔 口腔 體腺
或汗水味 大蒜味 狐臭味 其他的味
遮住表面沉靜 表面光彩的臉
層層密碼 矛盾帶著選擇 日夜驅趕
落到需要的每份情感或每一分錢上
車廂如同一根吸管
吸盡所有焦慮
使五官如同漏縫的塞子
變得獨特 短暫 謬誤或貼切
似乎不必詢問 誰在這里 我是誰
我們就是我們
味道腌制的喉嚨或嗅覺
融合了境遇中的身體 肌理和呼吸
仿佛一個巨大擴張的群體
真實的更多生命
都在比肩而坐 在中間扯開
感到一種味道飄走
又有另一種味道壓迫過來
相互一次次進入
脆弱的肺 脆弱的纏繞和脆弱器官
默默地喘氣
增多經過的一左一右
一前一后
玻璃上的側影
王學芯/文
余光里
玻璃上側影 或夜的深處
眼睛里的眼睛 一個被自己感動的人
感到面容或輪廓俊朗
五官棱角分明 沒有增厚的臉皮
緩和顴骨
還沒尖削
這種相遇
或從街道 候車室 月臺上走來的相遇
冥冥之中安排 升起一種信任和溫存
彼此尚未掉色的眼神
含有深情的水
此刻我們一起推動身軀向前
推動天空在樹和大地上穿過合腳的鞋子
拉近距離 拉近相伴的觸及
得到一點
珍貴的時間
半明半暗中突然對著的人或一大堆熟悉的名字
仿佛都在從喉嚨里出來 非感覺的感覺
余光里的凝目 充滿渴望和呼喚
翕動的嘴 好像說了一句
我們匆匆忙忙聚聚散散
因果鏈的核心
不變的 還是那
天分的連接方式
看不見的城市
王學芯/文
白晝已經消逝
無法回往的那座城市蒙蒙
熟悉的街巷 如同單薄花瓣蘊藏在胸腔
留在那里的目光 把一年一年的軀體
帶到此刻震顫的腳底
火車沿著我肌肉刮擦行走
眺望中 感覺的別離或清虛
隱沒身影 寂靜拍打了萬物之上的月暈
而依然通明的燈火 依然圓筵轉動
身份像是潛浮的東西
與相符的約定不差一點預期
似乎不在乎誰的空缺 不在乎失去什么人
都在即時為生命的迷惑
尋找一點幻影和回聲
仿佛空氣的回旋 或飄遠的氣息
在連根拔起 從意義中消泯
使所有內部閃爍的知覺
什么都沒有
視覺如在背對世界
所有感情 陷落了具體聯系的深坑
越離越遠的城市 燈如锃亮的鋼球
散發掉影子
騰清了
硬硬的
輕與空
自問
王學芯/文
相逆的臉 龐雜
自問 我是其中一例嗎
自負的 自私的 刁鉆的 狡詐的 陰暗的
狹窄的 冷漠的 瘋狂的 瘋癲的 分裂的
茫然的 計較的 虛幻的 歹意的 歹心的
辱罵的 貪婪的 負義的 齷齪的
我一次次決定我是誰
喘氣的嘴
呼吸著肺
我天天像在免疫的細胞間重建自己
我能避之若浼嗎
環顧四周 睜大緊張的眼睛
丑陋或獠牙 靈魂的一顆顆泥濘牙齒
變得可以隨時出沒
我干裂的雙唇
微笑出了血
第六種感覺全在移動的反光玻璃之中
為何我看到那些面孔總會驟然一抽
為何黑色影子幽昧 移進移出
為何凝視壓進血液
為何血液又變成了水
為何沉思
為何忍受
孤寂瞬間 我愈加珍惜培養的美麗
深深愛惜與之相反的我和我們
以及誕生的朋友們
以前的一次企圖
王學芯/文
夜空鏡子
火車的漏斗 燈火像鳥跡一樣四散
以前天長地久的一次企圖
或經過的事情 或突然寂靜下來的事物
多少路途 多長距離 多少環境
似乎忽視才有意義
落下了
密集的光
過去來到現在
沒有任何閃耀可言
某種存在 某種柔韌 某種慰藉和投入
或許還像理想那樣美好 或許
不知不覺回眸一瞥
無聲無息樣子 只有眼前
瞬間的離去
我和我們總在深沉下面
閃爍或掠過 我和我們穿越內心的天地
就像夜橫貫一層薄膜似的田野
邊緣的凹痕蜷縮
前進又前進了的動態
大群人們 仿佛都在平衡的天邊
我望著下弦月
混合了
黑夜與白天的交替
蘭花
中海/文
大病過后,空谷的創可貼揭開
新生的皮膚,舊巖上苔蘚的空手道
埋伏于裂隙的背面,光線已痊愈
下一場細雨在葉尖上凝神
注視必定開花
屏息的通幽大師,糾集疏朗
打通了纖細的氣息,翻盆的人
翻過多個山頭。作為小隱
白屋緊盯著天寒,不知如何關門
反正在不遠處,蘭用錯落的牙
一口咬住青山的顫抖
隱士獨自回到深山,生火
收集炊煙和寂靜。一支筆寫爛
三更月,口訣背成了灰燼
但仍是口訣:一筆長,二筆短
三筆破鳳眼。清氣的眼安于晨昏
寒風和香氣蓋在身上
柴扉出來的人,用嶄新的額頭
采集墨色中的花卉。一面絕壁橫亙
像荒誕夜色中豎起的鏡子
照著水土不服的善惡
美人蕉
中海/文
流水受制于溝渠,它總是用上半身
生自己的氣,下半身勉強哺育
它的嬰兒。受孕期的流水中
蝌蚪尋找一簇倒影,以解決一團黑
溶于另一團黑的難題。鮮艷產卵
美人蕉沉醉于光線的乳汁
而溝的壞脾氣流產,渠卻順從于向下
出生的事物是岸邊的雜草
鳥鳴齊膝,它說著什么,只有佛知道
他在大地行走,腳趾被刺破
邊流血邊發芽
蘸了血的花生得美
佛懷疑的是無所掛礙的血
在耳根盛開的清凈之花。花朵皈依
佛門外流水沖動過的溝渠
花朵越開越大,流水卻越來越細
像勒在腳趾上的奔跑
外出化緣,又像趕集途中的婦人
隨手丟棄的一個身影
把彩色的裙擺裹緊一點
夜歸的僧人和偷腥的月色
將睡眠掛在花的裙邊
流水很響,劃破的溝渠在止血
新生的兩岸可化淡妝,手提清風
一切都要恢復出生前的樣子
櫻花
中海/文
緊貼天空的蔚藍,被熾熱砸下
補充的白花,即刻傾盆而至
各種美妙,攪動一堆斷章的病句
一條路像書寫的白紙
折疊平滑的注視,紙飛機降落
在我們與飛鳥視覺的焦點
而贊美是病句出院后的問候
空白籠罩在斷裂處,蝴蝶在低處
盡顯求索的天性。由于火氣龐大
蝴蝶不得不扇動翅膀的病句
以澆滅鳥兒眼中的怒火
櫻花的耳膜被戰火聲刺破
我們用另一只耳分辨無序的落花
是什么在微妙中返回樹枝
呼應其中的異己主義者—
一些火一般喪命的灰
粗糙的皮膚在正午的垂直上潰爛
四月試圖喊來亡者—
落花的尸體,詢問他們:廢墟
是戰爭的尸體嗎?空白仍有火星
這余燼在櫻花全部直播完成后
再一次盲目地回到枝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