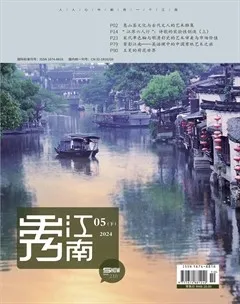從解構主義看尼采的酒神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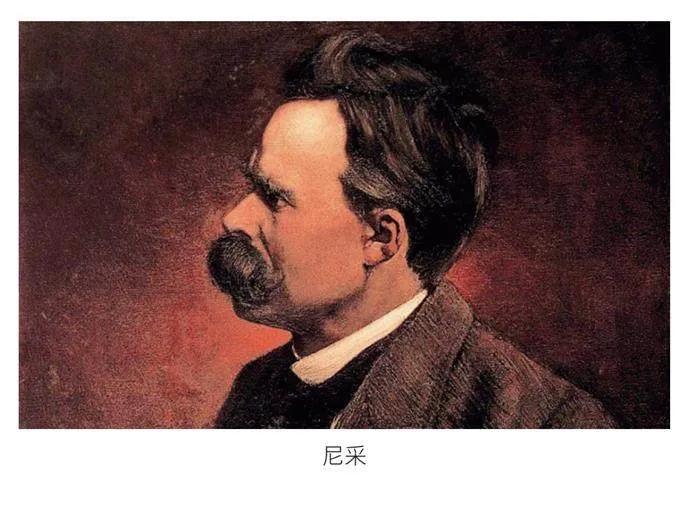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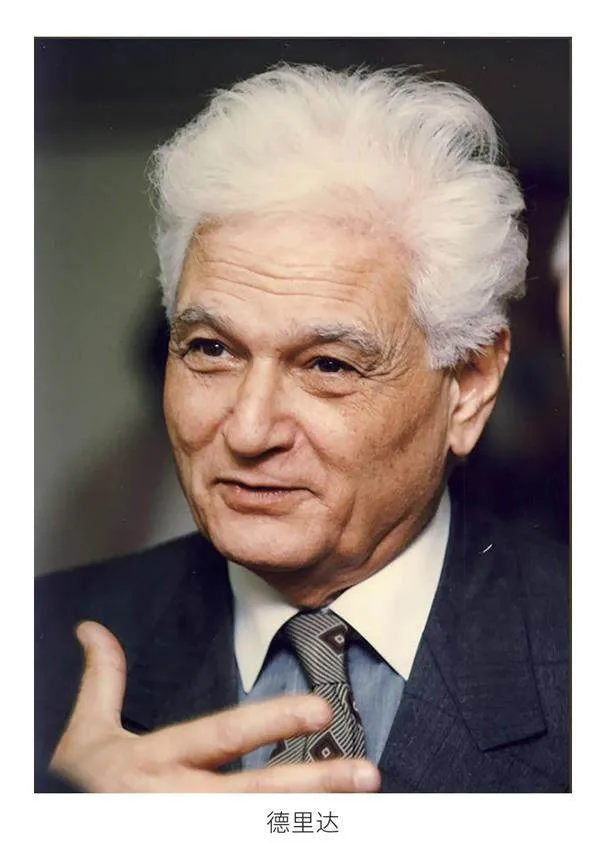
本篇讀后感聚焦于解構主義的定義、首要意義,闡述了尼采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
解構,是一種解讀和寫作方法,它拆解了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否定了原有的中心,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原有的中心和與其對立的次要因素,實現了由封閉向開放的轉變。
1966年,德里達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率先提出了解構主義,而我們雖然沒有專門講解構主義的課程,但是我們學習的女性主義、生態主義、文化批評、共同體形塑等西方文論都與解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為解構主義給許多西方文論提供了新的角度,讓我們從新的維度看待文學作品。以女性主義為例,解構主義解構了西方二元對立的男性和女性關系,揭露了西方是父權制社會,而女性處于被壓迫的他者地位。因此,女性應該認識到這種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不公正,采取種種行動,如推翻女性被呈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模式化形象、尋找并出版被忽略的女性作家作品、從女性視角重新定義經典作品、參與文學作品的討論,以達到重新定義女性形象,提高女性在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領域的地位的目的。
在文學層面,解構主義是一種分析文本的策略,而非文學理論、批評流派或哲學思潮。它與分解邏各斯中心主義中的二元對立息息相關。解構主義認為,我們原來認同的真理的中心未必全然正確。據此,解構主義拆解了各種真理的中心,如上帝、人、自我,所以我們無法肯定我們的信仰或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無法確定一篇文本的意義,因此,我們應肯定文本的不確定性,自由地從各種角度看待文本的意義。
解構的首要意義在于它解構了西方傳統思想中的真理和知識。西方社會渴望絕對真理,并利用邏各斯中心主義來保證真理的絕對和穩定。邏各斯中心主義是一種信仰: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建立在一種絕對的真理或者一種作為中心的真理之上。譬如在上帝與人類、男人與女人、理性與情緒、邏輯和修辭等二元對立中,每組對立只有一個選項處于中心地位,另一個則處于附屬地位— 上帝凌駕于人類之上、男人優于女人、理性高于情緒、邏輯勝過修辭。
解構主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尼采對西方哲學思想的思辨。一方面,尼采質疑了西方的真理傳統,重新思考了西方乃至人類思想史的走向。尼采說:“何為真理?真理是一支由隱喻、暗喻和擬人類化的喻說組成的機動部隊。”真理是人類根據利益和欲望的需要編造的價值概念,以此維護社會關系、維持秩序穩定。如同紙幣,本來只是幾乎沒有價值的紙張,人類賦予其衡量、支付、收藏等作用,久而久之,紙幣便成了一種傳統,為人所接受,也就有了價值。另一方面,尼采質疑了真理的哲學源頭,即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于真理的定義。在尼采看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并不代表古希臘精神的興盛,而是衰落。他立場鮮明地認為,古希臘精神以酒神的悲劇精神為基石,以藝術肯定生命,活力充沛,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卻片面強調理性,與古希臘精神背道而馳。古希臘的悲劇呈現出一種悲劇力、一種酒神精神,人的生命,不管是偉大還是卑微,終將隕落,融入無盡的大洋之中。這種宿命雖然悲劇,但是展現了一種智慧從容,坦露出一種無限的生命力。一如俄狄浦斯王,在命運的捉弄下殺父娶母,出于對自我的懲罰,他刺瞎了自己的雙眼,將自己放逐。但是在他悲劇的人生中,他始終熱愛人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智慧從容。個體生命雖有盡頭,但宇宙生命無限,生而滅、滅而生,無窮無盡,汪洋澎湃—酒神精神就是如此。
尼采批判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過于強調理性,認為他們用理性的樂觀否定了古希臘悲劇精神。這種理性看似富有邏輯,實則壓抑、寂靜,缺乏古希臘精神那種澎湃的生命力。蘇格拉底將理性與情緒、邏輯與美感剝離,他坦然赴死更是將他的哲學思想絕對化。柏拉圖因為蘇格拉底的神化之死深受震撼,將蘇格拉底信奉的理性奉為圭臬。
德里達等人的解構主義是對尼采思辨思想的一種演變。德里達提出了先驗所指、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及二元對立等概念。他承襲了尼采哲學的思辨,如同尼采同時認同思維和修辭一樣,德里達認為解構不是否定原有的中心,而是持有開放的觀點,認同事物的不確定性。另外,德里達解構的對象是作為西方古典思想基礎的二元對立,即以邏各斯中心邏輯為中心的解構。在二元對立中,一方是超驗所指,是絕對的、超驗的、正確無疑的,另一方則處于次要的、附屬的地位。這個中心即超驗所指,并非絕對正確,而是一種傳統、幻覺或謊言。先驗所指、二元對立、邏各斯中心主義長久以來被用于構建絕對真理、等級秩序、西方中心以及暴力體系,其解構則是從封閉走向自由的一種方法。
解構主義源于尼采,由德里達等人繼續衍生、發展,獲得新的術語和內涵。解構的思辨則提供了一種新的策略,質疑原有的中心,使思想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專制走向民主。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