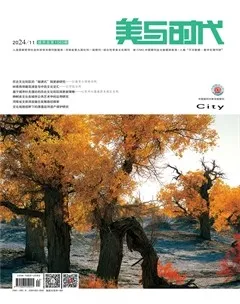宗族文化視角下鄉村人居環境的探索與建議
摘 要:宗族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對傳統村落的建設發展有著巨大影響。宗族文化幾千年來影響著我國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居環境規劃發展。廣東梅州蕉嶺縣位于粵北地區,當地的宗族文化、居住系統、村落形態相較于其他地區得到了更好的傳承,保留了基于宗族文化形成的中國傳統村落,許多客家村落仍舊保持著“大家庭,小社會”的狀態。以梅州蕉嶺縣為例,從宗族文化視角去觀察、分析傳統宗族村落的形成與發展。基于現有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從我國鄉鎮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新時代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化,提出中國傳統宗族村落未來人居環境規劃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宗族;傳統村落;鄉村建設;人居環境
人居環境是一個地區人與自然相處方式的體現,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我國對于人居環境的研究已經從20世紀50年代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搬運轉向了更加貼近我國社會發展情況的更加本土化的研究。吳良鏞的《人居環境科學導論》從中國建設實際出發,將西方人類聚居學與我國國情結合,為未來中國人居環境規劃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通過對廣東梅州蕉嶺縣宗族文化和人居環境的研究,結合《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對現代人居環境規劃發展的理論歸納,為中國傳統鄉村人居環境未來的發展規劃提供四條建議。
一、廣東梅州蕉嶺縣的宗族文化
梅州蕉嶺縣位于廣東省東北部,是客家民系聚居地。1949年后,許多地區的血源性宗族文化逐漸和地緣性宗族文化融合,但在華南地區,人們對于氏族仍有高度認同感,因此傳統宗族文化在嶺南地區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更好的保留。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受城市化影響較小,所以當地傳統的聚居形態、村落結構保留得較為完整,呈現了一個在宗族文化影響下形成的人居環境范本。以廣東梅州蕉嶺縣為研究對象,可以更好地了解在宗族文化的影響下人居環境是如何發展的。
(一)蕉嶺縣地理環境及村落來源
蕉嶺縣舊稱鎮平縣,處于閩粵贛交界處,地形復雜,山脈連綿。其地理位置偏僻,生存環境惡劣,長期以來都是流民匪盜聚集之地。正是這種動亂的環境,影響著當地的人口及文化變遷。梅州蕉嶺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以當地土著人為主的荒野時期。此處多為荒野之地,無外來人口遷入,直到南宋后遭兵禍,土著逃亡。第二個時期是南宋之后,一些姓氏家族遷入此地,長期定居。第三個時期為明朝時期,農業繁榮發展,又有許多福建人遷入,家族得到壯大發展,并演變為宗族。
據《蕉嶺縣志》記載,蕉嶺縣長期受洪災水患影響,生態系統不穩定,相較于其他客家聚居地區,農民的生存壓力更大,宗族之間由于土地資源引起的競爭也更加激烈。在元末明初,就有徐姓家族前來蕉嶺開荒,主要在沿石窟河的寬廣平原地區聚居,后來又有許多家族遷來,逐漸形成以家族姓氏為單位的聚居村落。以塘福嶺為例,最初以楊姓、卜姓、練姓為村落中的大姓,與其他小姓以祖堂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形成村落,名為塘屋嶺。直至陳姓先祖來此地開基,并逐漸占領其他家族領地,最終將此地變為一個陳姓村莊。塘福嶺是一個典型的宗族村莊,內部由一個個以血緣為主的單位構成,影響著村落的生產活動和社會交往。整個村落呈現出“大聚居,小散居”的格局[1]。
(二)蕉嶺縣宗族文化的發展
宗族文化有地緣性宗族和血緣性宗族之分:地緣性宗族主要以地域為劃分標準,強調位置上的集中;血緣性宗族文化即以血緣關系為依據,在中國,宗族主要是以男性世系為脈絡,隨著父子關系擴大形成家族集團。廣東梅州蕉嶺縣以當地的客家文化享譽世界,客家人的到來在當地形成了一個聚族而居、睦宗敬祖的和諧小社會。客家人在遷入的同時,也將中原的氏族文化帶入,且與當地原住民形成了天然的地緣沖突,這樣的情況使得客家人更加注重家族。蕉嶺縣人際關系的形成主要受地緣性、血緣性、親緣性影響,在熟人社會中形成。其中以宗族為單位,內部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親密程度取決于血緣關系上的親疏遠近,以三代五服構成日常生活的社交圈,聚居于一村或是一樓。高度集中的聚居形式使得這樣的親緣關系更加緊密,宗族文化在這樣的村落形態下得到了最好的傳承,也由此產生了在婚喪嫁娶等方面的地區性傳統文化。
二、梅州蕉嶺縣人居環境探索
(一)聚族而居的客家圍屋
客家人由中原地區遷入梅州蕉嶺,與當地人有著天然的地緣沖突,不同的文化及對資源的競爭使得客家人通過住宅對自己的后代和財產進行保護。客家建筑以圍屋最為著名:整體建筑外部結構大多為圓形,整體呈現“外圓內空”的建筑特點。客家圍屋俯瞰為一個個圓形結構,但其內部結構曲折環繞,是一種典型的防御型建筑。從內部結構來看,圍屋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結合,以堂屋為中心,橫屋在堂屋兩側對稱分布。用于擺放祖先牌位的空間是圍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屋室則各司其職。隨著時間發展,宗族不斷擴大,一個個家庭也會圍著祖屋聚居。圍屋村落內部“親親相幫、親親相隱”,形成以血緣為紐帶的圍屋居群[2]。客家圍屋采取“宗族聚居”“祠宅合一”的居住分布,宗族文化以這樣的方式在人們的生活中具體化,成了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二)單一整體結構的聚居村落
在單姓村落中,宗族文化對于村落內人居環境的影響更為明顯。單姓村落自形成之日起就是一個家族社會,將縱向清晰的親緣關系投射到村落規劃的空間形態上,呈現出由中心向四周拓展的模式。單一姓氏村落在空間形態上有著極強的聚集性和向心性,村落通常呈現一種中心邊緣結構,以宗祠或者族內長老的住所為中心,依照縱向血脈分衍向外布局房屋,形成樹狀組織構架。在血緣親屬、長幼有序的宗族文化影響下,單姓村落發展出自己的治理方式和空間規劃體系[3]。
三、宗族文化變遷與宗族村落人居環境規劃
(一)村落規劃的重心由大宗族轉向以家庭為核心的小團體
梅州蕉嶺縣塘福嶺作為典型的宗族村落,在村落基層管理中,宗族組織成了強有力的村莊結構性力量。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宗族不斷擴大,其權力被逐步削弱。由此,宗族村落規劃的重心從大宗族轉為個體家庭的具體需求。從前的中心邊緣結構村落防御性強,內部路線復雜多變,可以對宗族內重要的族老和建筑起到保護作用,而在現代社會,人們不再面臨兵禍匪患,宗族等級不再限制村落人居環境的規劃,村落中人居環境的規劃重心轉向了個體和家庭的發展。
以蕉嶺縣塘福嶺為例,塘福嶺內塘屋嶺地區主要是村民住宅,傳統時期的村落形態被保留得較為完好:地形復雜、住宅集中,與后期的住宅規劃有很大不同。隨著塘福嶺地區道路、橋梁的修建,地區內的交通狀況得到很大改善。各家為了交通方便,紛紛沿公路建造新居,宗族居群不再保持高度集中的規劃,變得更加分散,不再受制于傳統宗族村落自我保護的規劃理念。
(二)傳統宗族村落人居環境規劃
從學術發展來看,近百年來,特別是二戰之后,各國都面臨戰后重建問題,建筑學、城市設計學在這一時期成績斐然,在理論、技術、設計方法等各個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在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發現,由于社會的政治、經濟等要素的變化以及近年來科學技術的變革,傳統規劃設計變得不合時宜,人居環境發展應該走向一條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道路。學者將人居環境劃分為五個系統,分別是自然系統、人類系統、社會系統、居住系統、支撐系統[4]。
1.居住系統新轉變
梅州蕉嶺縣村落內存在大量客家圍屋,這些建筑在傳統時期是作為居民住宅,但是在如今,圍屋更多成了一份文化遺產。客家圍屋一開始是作為一種防御性建筑,為了保護客家人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但是在現代,客家人不再面臨資源爭奪的問題,加之圍屋本身居住體驗不佳,圍屋內部的人居生態分崩離析。由此,蕉嶺縣內部村落住宅脫離了圍屋的形式,開始往傳統多層獨戶民居發展。
客家圍屋如今主要呈現三種狀況:第一種是作為景點,得到相關部門的保護修繕;第二種是作為宗族精神寄托,由宗族成員進行維護,但是由于宗族人口擴大、年輕群體遷出,圍屋逐漸喪失居住功能;第三種是被徹底荒廢,即使有少數人居住其中,但由于房屋年久失修,不再適宜居住,在未來也會逐漸不再作為居所。
2.自然系統再規劃
宗族村落在創建伊始是以生存為最主要的規劃目的,在后期往往面臨無法平衡人口與自然環境的問題,造成了自然資源透支的局面。1949年后,工業快速發展,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愈發尖銳,且由于村落規劃不科學,河流污染農田的事情時有發生,成了鄉村可持續發展路上的嚴重隱患。近幾年,我國鄉村改造工作如火如荼,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可靠的數據建模技術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規劃鄉村的發展,彌補宗族村落早期在規劃上的不足。
梅州蕉嶺縣土地資源較少,在農耕方面沒有優勢。后來,由于自然資源無法供應不斷增長的人口,百姓通過水路前往南洋等地,以此緩解資源與人口之間的矛盾。如今,交通便利,大量青年前往城市謀生,人們不再以農耕水運為最主要的經濟產業。最近幾年,蕉嶺縣對于自然環境的規劃治理頗有成效:空氣質量逐年上升,水資源污染事件減少。鄉村人居環境結合其地理環境和產業發展進行合理規劃,自然、經濟、人口等多方面的平衡成為關注重點。
3.社會系統重思考
人居環境是圍繞人之間的生活交往展開的,與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需求密切相關。舊時代,在傳統宗族村落中,經常出現家族聚居的情況,普通家庭的房屋設計和人居環境規劃也旨在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并不關注個人心理需求,公共場所規劃安排考慮不周,而這些都是在現代鄉村人居環境規劃改造中主要考慮的問題。
由于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現長居在村落中的大多為老年群體及托由長輩照顧的兒童。老人和兒童對應了醫院和學校,也意味著村鎮建設的相關基礎設施需要跟進。在房屋重建中,設計師應當做出相應的適老化設計。老年人及兒童相較于青年群體往往需要更多的社交,社交場所成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現代鄉村的設計不再是只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建筑居群,更要有人情味,關心居住在其中的人和他們的活動,這才是人居環境設計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屬[5]。
4.科學追求與文化藝術創造相結合
我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文化環境建設也是人居環境規劃的內容之一,對一個地區的規劃不能僅限于經濟建設和技術發展,還需要思考地區的文化環境。這就要求規劃者因地制宜,體現各地區建筑文化的獨特性,在設計中結合藝術美感,使藝術科學化、科學藝術化,賦予人類社會生活情趣和秩序感。
梅州蕉嶺縣客家圍屋作為當地獨特的建筑文化,為蕉嶺縣帶來了大量的旅游資源。在當地,人們并沒有單一追求經濟效益,走上一貫的城市化道路,而是利用獨特的文化加以保護宣傳,提高了當地的文旅價值,再將獲得的資金進一步用于維護古建和文化保護,形成了經濟與文化的良好循環。文化藝術與科學規劃的結合可以在優化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的同時保留地域文化,給人們提供精神價值。人居環境規劃不應該只考慮經濟效益和區位科學,還要尊重、鼓勵、反映具有文化和美學價值的人類住區的特征多樣性,為子孫后代保留當地的歷史、宗族文化等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內容。
四、結語
韋伯在他的名著《儒教與道教》中表示,氏族在西方中世紀時就已經完全失去了意義,但在中國則被完整保存于地方管理的最小單位以及經濟聯合會之中。宗族文化千百年來影響著村落的規劃和建設,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宗族不再成為傳統村落構建的主要依據,這種以父系血脈為紐帶的居群正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從宗族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對現有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進行補充,并對未來傳統村落人居環境發展提出建議。可以預見,我國鄉村建設工作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參考文獻:
[1]白雪嬌.血緣與地緣:以家、房、族、保為單元的宗族社會治理[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7.
[2]劉禹冰.淺談客家土樓的建筑特色及文化內涵[J].文化產業,2021(3):74-75.
[3]彭文崢,梁挺.基于宗族文化的山地單姓村落保護方法初探:以重慶長壽區葛蘭鎮大壩村歷史文化名村為例[J].城市建筑,2021(28):106-114.
[4]唐穆君.鄉村文化的變遷及價值重構研究:以陜西省周至縣H村宗族組織為中心的考察[J].社會科學動態,2021(7):69-75.
[5]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導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40-48,66-68.
作者簡介:
陳妙,常州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設計。
袁新林(通訊作者),碩士,常州大學教授。研究方向:數碼編織產品設計、紡織及復合材料產品應用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