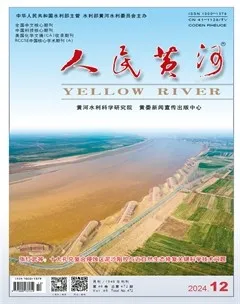基于聚類分析的膨脹土渠坡加固前后變形特征分析











摘 要:膨脹土渠坡變形具有季節性、長期性和滯后性等特點。為探究膨脹土渠坡加固前后的變形特征,基于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陶岔段運行期對膨脹土渠坡增設排水設施前后的變形數據和地下水位數據,構建渠坡多指標面板數據并進行聚類分析,對比傳統聚類方法和簡化聚類方法的聚類效果,識別渠坡內部位移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規律,分析增設排水設施對膨脹土渠坡地下水位和變形的影響。典型測點實例分析結果表明:地下水位抬升與渠坡位移變化的相關性較強;僅增設淺層排水設施處理高地下水位膨脹土渠坡的效果有限,不能修復已產生的變形。
關鍵詞:膨脹土;渠坡;加固;變形;聚類分析;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陶岔段
中圖分類號:TV9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 j.issn.1000-1379.2024.12.024
引用格式:蔣晗,胡江,李星.基于聚類分析的膨脹土渠坡加固前后變形特征分析[J].人民黃河,2024,46(12):144-148.
0 引言
在我國廣泛分布的膨脹土是一種具有顯著脹縮性的特殊土,其土體性質受內部裂隙發育影響。我國多個涉水工程的膨脹土渠坡運行后遭遇滑坡或嚴重變形問題,膨脹土渠坡失穩往往表現出平緩性、淺層性、牽引性和長期性等特征,例如:陶岔引丹灌區自20 世紀70 年代投入運行30 a 后,在渠首樞紐下游約1 km 處發生一起大型滑坡[1] ;安徽淠史杭灌區自1972 年投入運行,深切嶺渠段多次發生滑坡,2020 年瓦東干渠劉崗電灌站左岸發生滑坡[2]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南陽段的膨脹土渠段投入運行6 a 后出現了渠坡嚴重變形、襯砌面板隆起等問題[3] ;北疆供水工程總干渠渠坡施工期采取了針對性排水措施,但在通水運行近20 a 后膨脹土管道出現破壞[4] 。可見,即使對膨脹土渠坡采取加固或排水措施,但其運行期仍存在失穩破壞風險和工程安全問題,甚至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因此,探究運行工況下膨脹土渠坡的變形過程及形成原因,對后期保障渠坡安全具有一定意義。Basma 等[5] 、呂海波等[6] 、胡旭輝等[7] 通過土樣試驗發現,膨脹土黏聚力的降低是其在干濕循環中強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殷宗澤等[8] 、張家俊等[9] 、劉斯宏等[10] 通過膨脹土渠坡試驗發現,淺層滑坡主要受干縮裂隙控制,深層滑坡主要受膨脹土黏聚力控制。陸定杰等[11] 、龔壁衛等[12] 基于膨脹土渠坡滑坡機理提出了改性換填、柔性支護等防治措施。考慮到膨脹土渠坡變形具有反復性特點,楊宏偉等[13] 、胡江等[14] 提出了基于監測數據的膨脹土渠坡運行期變形特征分析方法。雖然針對膨脹土渠坡的變形與穩定性等已開展了廣泛研究,但是缺少對排水和加固措施實施前后渠坡變形特征的分析。
本文以南水北調工程陶岔段膨脹土渠坡為例,將其分為投入運行至嚴重變形、經加固處理(增設淺層排水設施)后再投入運行至拱圈出現細微開裂現象兩階段,利用多指標面板數據聚類方法[15-17] 對比分析兩階段的膨脹土渠坡變形特征,探討增設排水管、排水盲溝等淺層排水設施對控制渠坡變形的效果,以期為后期膨脹土渠坡加固處理提供依據。
1 工程概況和監測布置
南水北調工程樁號9+100—9+363 段渠坡由上弱膨脹土段和下中膨脹土段組成,膨脹土主要是Qal-pl2 粉質黏土。渠坡地面高程為169~181 m,坡高為32~44 m,渠底寬13.5 m,一級馬道寬5 m,一級馬道以上每6 m設各級馬道,過水斷面換填1.5 m 厚的水泥改性土,一級馬道以上換填1.0 m 厚的水泥改性土,渠坡典型斷面示意見圖1。該渠段施工期曾遭遇滑坡,在五級邊坡布置了一排抗滑樁,并采取弱膨脹土回填和改性土外包等措施進行處理。該渠段于2014 年12 月12 日通水運行。
2016 年8 月14 日,樁號9+000—9+120 段左岸襯砌面板出現多條縱向裂縫、1 處面板錯臺,樁號9+160—9+180 段樁頂板出現2 條縱向擠壓裂縫。據現場勘察,坡面拱圈裂縫由拱圈頂部向下發展至拱圈基礎,最大裂縫寬3 mm,拱圈基礎表面多為細微裂縫,開度最大為2 mm。結合現場情況,初步判斷是淺層土體蓄水過多引發不均勻膨脹,進而導致拱圈表面開裂。為有效解決該段渠坡土體蓄水問題,于2018 年7 月27 日—8 月15 日在樁號9+180—9+363 段二級邊坡增設集水槽、排水盲溝(底部設直徑為200 mm 的透水軟管)。運行至2021 年年初,該渠段二級邊坡坡腳混凝土拱圈出現細微裂縫,個別部位斷裂、翹起,排水管存在長期出水現象。
2 多指標面板數據聚類分析方法
2.1 多指標面板數據
膨脹土渠坡監測變形數據具有空間和時間特性,測點位移隨時間和深度變化,用多指標面板數據進行擬合,對于此類數據用二級二維表來表示,見表1。
2.2 傳統聚類方法
系統聚類方法[15] 是傳統聚類方法中使用較多的一種方法,具體步驟為:首先定義各測點位移間距離,將每個變量視為一個類別,然后將最小距離或最相似的兩類變量合并,再重新計算新類別與其他類別之間的距離或相似性,繼續按此方法重復歸類,直到所有變量歸為一類。為分析時間維度對聚類過程的影響,通常采用歐氏時空距離來度量相似性,深度h 處測點位移與深度h+i 處測點位移間的歐氏時空距離dh,h+i 計算公式為
這樣,所有兩兩測點位移之間形成了一個距離矩陣,該矩陣對稱且對角線元素為0。當需要對測點位移進行歸類合并時,為避免陷入局部最優,采用離差平方和方法選擇最優合并為一類的測點位移,相似性高的測點位移間離差平方和較小,歸類完畢后的類與類間的離差平方和較大。其中g 類的離差平方和Sg 計算公式為
式中:hg為g 類內包含之前合并的類的集合,Xqhg (t)、Xphg(t)均為g 類中t 時刻的位移分量平均值。
當r 類和k 類測點位移合并時,假設k 類最后由m 類和n 類合并而來,其新類測點位移之間的距離Drk的遞推公式為[16]
式中:nr 、nk 、nm 、nn 分別為r、k、m、n 類包含類的數量,ΔSrk為r 類與k 類測點位移合并成新類的離差平方和,Srm為r 類與m 類的初始離差平方和,Srn為r 類與n 類的初始離差平方和。
2.3 簡化聚類方法
為獲得膨脹土渠坡測點監測變形數據(位移)隨時間的變化趨勢,對數據進行分段聚類,即t0 時刻的數據為對t<t0 時刻的數據進行聚類的結果。一般而言,渠坡測點位移在時間上多呈連續性,僅在滑裂面存在一定突變。按照如下步驟對測點位移進行聚類:1)取t 時刻的測點位移,計算相鄰深度測點位移的離差平方和D(1) h,h+1;2) 合并離差平方和最小的兩類并重新計算新類與相鄰深度測點位移的離差平方和D(2) h,h+1;3)將D(1) h,h+1 < D(2) h,h+1 的兩類依次合并,計算相鄰深度測點位移的離差平方和;4) 重復步驟2) ~ 步驟3) 直到合并成為一類;5) 取t = t + 1,重復步驟1) ~ 步驟4),直至T 時刻輸出最終聚類結果。
2.4 聚類結果對比分析
使用傳統聚類方法與簡化聚類方法對南水北調工程陶岔段IN049180 測斜管某時刻的位移進行聚類,得到聚類譜系圖(見圖2)。傳統聚類方法側重于考慮數據間的相似性,如將深度為5.0~6.0 m 的數據與深度為13.0~15.5 m 的數據歸為一類,孤立深度為3.5~4.5 m的數據,存在數據失真、異常值影響較大等問題[18] 。而使用簡化聚類方法避開了此類問題,對于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較強連貫性的數據簇,聚類結果清晰。
3 聚類結果
3.1 單測點聚類結果
由于樁號9+180 斷面測點位移較完整,且該斷面二級邊坡上部拱圈已出現裂紋,因此以該斷面四級馬道IN049180 測斜管為例進行分析。該工程段自投入運用以來歷經3 個完整干濕循環,采用面板數據聚類方法對該工程段增設淺層排水設施前后IN049180 測斜管位移進行聚類分析。增設排水設施前IN049180測斜管的位移隨深度和時間的分布見圖3。渠坡內部不同深度的位移呈周期性波動。
對于高程為166.672 m 的IN049180 測斜管在2017 年7 月運行至2018 年7 月的位移聚類結果見圖4。
圖4 中位移聚類結果出現較穩定的分區:深度0~10 m對應分區Ⅲ、深度10~15 m 對應分區Ⅱ、深度15 m 以下對應分區Ⅰ,其中在2018 年3 月后出現的突變點A及深度0~5 m 對應的新位移分區Ⅳ,表明土體中出現新的位移變化趨勢。同一分區的位移數據具有相同變化趨勢,據此判定不同位移分區的土層之間存在界面。界面破壞渠坡的完整性并形成降雨入滲通道,降低渠坡抗剪強度,認為分區界面可能成為渠坡的潛在滑動面,結合位移圖可初步判斷分區Ⅲ與分區Ⅳ界面是渠坡滑動的結果。對于降雨入滲條件下非飽和土滲流模型中的潛在滑動面判別[19-20] ,一般以含水率分布為依據。結合地下水位與土體位移變化情況,推測深度15 m處潛在滑動面基本受地下水位控制;深度超20 m時潛在滑動面整體處在地下水位以下,主要受土體抗剪強度控制。
圖4 中新聚類分區Ⅳ出現的同時,該測點位移在同一時段內兩個方向上均出現較大變化,伴隨著地下水位抬升,表層土體可能形成新的潛在滑動面。結合圖3 可知,該測點位移以點A 處為分界,沿深度方向出現突變,說明簡化聚類方法可有效快速地搜索此類間斷點,輔助判斷潛在滑動面位置。干濕循環過程中分區Ⅳ的出現表明,此前相對不明顯的土體錯動受裂隙發育和地下水位抬升的影響進一步發展,在淺層形成新的位移分區。此過程中地下水位變動與渠坡位移具有關聯性,2018 年3 月地下水位逐步抬升至160 m 時出現新的位移分區Ⅳ,運行至8 月,渠坡表面拱圈開裂,出現嚴重變形,說明地下水位是膨脹土渠坡安全監測的重要指標。
增設排水設施后IN049180 測斜管的位移隨深度和時間分布見圖5,聚類結果見圖6。
分析圖5 可知,增設排水設施后渠坡位移仍呈明顯的季節波動性。圖6 中新產生的分區Ⅳ的位移趨勢與分區Ⅲ的并不能歸為一類,表明土體整體性受到影響,即使增設排水加固措施,仍不能使渠坡位移趨勢恢復至此前狀態,存在不可逆的變形。2018 年8 月后地下水位降低,保持在高程157 m(深度10 m)左右。與圖4聚類結果對比,增設排水設施后土體錯層并不隨地下水位下降而消失,說明土體性質出現變化,干濕循環作用對渠坡產生不可逆的影響。
2020 年6 月地下水位最高抬升至高程160 m(深度7 m)后不再下降,表明采取的排水措施效果有限,并不能長期有效降低地下水位。運行至2021 年年初,與增設排水設施前(2018 年3—8 月)類似,渠坡在持續高地下水位影響下,拱圈再次開裂,說明僅采取淺層排水措施處理高地下水位膨脹土渠坡的效果不佳。
由圖6 可知,渠坡投入運行至2021 年年初拱圈再次開裂時的位移波動不如圖4 中初次開裂時顯著,說明渠坡在土體劣化和裂隙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重新出現變形現象,單以位移作為監測指標并不完善,另外須進行深層排水處置。
3.2 整體聚類結果
對IN039180、IN029180、IN019180 測斜管測點同樣進行聚類分析,其結果與IN049180 的相似,取其中較為典型的聚類結果標注至渠坡中,并以圓弧滑動面擬合相近分區,繪制出排水前后樁號9+180 斷面的潛在滑動面,如圖7 所示。
分析圖7(b)可知,排水后由分區Ⅳ與分區Ⅰ構成的淺層潛在滑動面位置與地下水位相近,而位于地下水位之下的潛在滑動面基本沒有變動,符合強降雨和初始地下水位作用下淺層渠坡的位移變化趨勢[21-23] 。一般而言,地下水位抬升和潛在滑動面的出現是膨脹土裂隙發育影響的結果,干濕循環中發育的裂隙導致土體含水率上升和抗剪強度下降,從而形成多個潛在滑動面,渠坡土體位移則在多個潛在滑動面的共同作用下表現出一定的波動性與季節性。土體淺層潛在滑動面會隨地下水位的升降發生變化,在地下水位附近穩定,且膨脹土渠坡滑坡多發生在淺層,該滑動面可被視為渠坡的主要滑動面。
整體來看,土體內部含水率達到警戒值而出現表面嚴重變形或渠坡失穩前兆時,短時間內通過增設淺層排水措施使土體含水率驟降,相當于渠坡進行一段完整的干濕循環,可能加速土體微觀結構劣化,致使土顆粒間黏聚力下降,越靠近地下水位土顆粒的黏聚力損失越大,從而導致在僅增加排水措施的情況下,邊坡在承受數次干濕循環后迅速出現二次表面變形現象。
4 結論
1)采用面板數據聚類方法可以推斷渠坡的主要潛在滑動面。通過對監測位移進行聚類分析,可將渠坡變形劃分為多個區域,不同分區之間存在明顯界面,其受裂隙發育或抗剪強度控制,是渠坡的潛在滑動面,通過對比不同測點的聚類結果,可確定渠坡的主要潛在滑動面位置。
2)地下水位的抬升與渠坡位移的變化有較強的相關性。降雨入滲和地下水位變動降低了渠坡的抗滑力。地下水位附近存在一個穩定的潛在滑動面,當地下水位抬升并重新保持穩定時,將隨之出現新的位移分區,同時渠坡出現拱圈開裂等現象。可見,地下水位可以作為邊坡變形的重要參考指標。
3)僅采取淺層排水設施處理高地下水位膨脹土渠坡效果有限,不能修復已產生的變形。增設淺層排水設施后,在1~2 個干濕循環周期內地下水位恢復至增設前時聚類結果并未發生改變,拱圈出現開裂現象,表明干濕循環對渠坡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
4)長期來看,隨著土體裂隙的發育,土體含水率將增大,而排水設施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極限。僅增設淺層排水設施可能無法防止渠坡在歷經數次干濕循環后土體位移再次超出設計值的情況。在此情況下,除增設淺層排水設施外,還應考慮控制地下水位變化,實施深層排水設施。
參考文獻:
[1] 包承綱.膨脹土管道邊坡的破壞與防治對策[J].土工基礎,2014,28(5):106-114.
[2] 葉為民,孔令偉,胡瑞林,等.膨脹土滑坡與工程邊坡新型防治技術與工程示范研究[J].巖土工程學報,2022,44(7):1295-1309.
[3] 馬慧敏,何向東,張帥,等.南水北調中線膨脹土(巖)渠段問題及成因分析[J].人民黃河,2020,42(2):128-131.
[4] 鄧銘江,蔡正銀,朱洵,等.北疆渠道膨脹土邊坡破壞機制及加固措施[J].巖土工程學報,2020,42(增刊2):50-55.
[5] BASMA A A,AI?HOMOUD A S,HUSEIN M A I,et al.Swelling?Shrinkage Behavior of Natural Expansive Clays[J].Applied Clay Science,1996,11(2-4):211-227.
[6] 呂海波,曾召田,趙艷林,等.膨脹土強度干濕循環試驗研究[J].巖土力學,2009,30(12):3797-3802.
[7] 胡旭輝,張坤勇,聶美軍,等.干濕循環條件對膨脹土強度指標的影響[J].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3(1):269-279.
[8] 殷宗澤,袁俊平,韋杰,等.論裂隙對膨脹土邊坡穩定的影響[J].巖土工程學報,2012,34(12):2155-2161.
[9] 張家俊,龔壁衛,胡波,等.干濕循環作用下膨脹土裂隙演化規律試驗研究[J].巖土力學,2011,32(9):2729-2734.
[10] 劉斯宏,沈超敏,程德虎,等.土工袋加固膨脹土邊坡降雨-日曬循環試驗研究[J].巖土力學,2022,43(增刊2):35-42.
[11] 陸定杰,陳善雄,羅紅明,等.南陽膨脹土渠道滑坡破壞特征與演化機制研究[J].巖土力學,2014,35(1):189-196.
[12] 龔壁衛,程展林,郭熙靈,等.南水北調中線膨脹土工程問題研究與進展[J].長江科學院院報,2011,28(10):134-140.
[13] 楊宏偉,胡江,槐先鋒,等.基于多變量時間序列局部異常系數的滑坡預警方法[J].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中英文),2021,19(6):1227-1237.
[14] 胡江,張吉康,余夢雪,等.深挖方膨脹土渠道邊坡變形特征分析與預測[J].水利水運工程學報,2021(4):1-9.
[15] 王澤東.多指標面板數據聚類方法研究及其實證分析[D].桂林:桂林理工大學,2019:18-20.
[16] 任娟.多指標面板數據融合聚類分析[J].數理統計與管理,2013,32(1):57-67.
[17] 黨耀國,侯荻青.基于特征提取的多指標面板數據聚類方法[J].統計與決策,2016,32(19):68-72.
[18] 穆森.面板數據的灰色關聯與聚類模型構建及應用[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2:14-15.
[19] 馬慧敏,何向東,張帥,等.大型輸水渠道膨脹土(巖)渠段邊坡穩定分析[J]. 人民黃河,2020,42(3):146 -149,154.
[20] 張文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膨脹土渠段邊坡變形研究[J].人民黃河,2019,41(7):131-135.
[21] 馬世國,韓同春,徐日慶.強降雨和初始地下水對淺層邊坡穩定的綜合影響[J].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45(3):803-810.
[22] 張杰,韓同春,豆紅強,等.基于分層假定入滲模型的邊坡安全性分析[J].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45(9):3211-3218.
[23] 蘇永華,李誠誠.強降雨下基于Green-Ampt 模型的邊坡穩定性分析[J].巖土力學,2020,41(2):389-398.
【責任編輯 栗 銘】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52179138,51879169);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022M711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