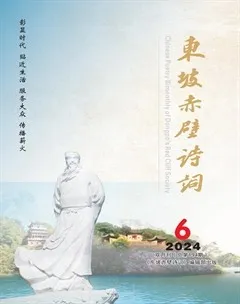平淡寄詩心
在多種詩歌風格中,有一種風格叫“平淡”。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稱之為“沖淡”,基本上都是一個意思。宋代梅圣俞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
所謂平淡,就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口言詩,不假雕琢,純任自然。如梅圣俞的“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丑枝”,皆是“平淡”詩風的名句。許紅娟田園詩近似這種風格。
“手理青絲織錦忙,繡輪明月繡朝陽。辮梢一甩銀鈴遠,裁片朝霞做嫁妝。”寫村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首二句平平而起,結句見意,有想象力。“辮梢一甩銀鈴遠”寫姑娘織錦動作,十分傳神,是難得的好句。整首詩作有民歌風。
“十畝良田獨擔肩,只身瘦影壓枝彎。春耕夏種秋收急,踩響雞聲踏月還。”寫留守老人田間勞作的艱辛,不言五更即起,月落還家,卻言“踩響雞聲踏月還”,這樣說就充滿了詩意。以“只身瘦影壓枝彎”來形容老人形象也十分貼切,是詩的語言。平淡并非直言、白話,而是苦思煎熬后得來的詩句。
“老牛卸甲已經年,夕照殘陽欲舉鞭。畝補銀錢何用贊,荷鋤猶勝逛公園。”當代農村最大的危機,是年輕人早已對土地失去了熱情。而詩中的這位老農,鄉土情結卻是如此固執,以致在科技取代了傳統農耕方式的今天,仍然堅持荷鋤巡田,作為休閑消遣,足見癡得可愛。詩寫老農的鄉土戀情,寫當代農村的變化,擺脫了尋常思路,取材典型,視角獨特,人物鮮活,是許紅娟田園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寂寂田中立,排排高院連。夜深無犬吠,冷月掛窗前。”寫空心村的悲哀,相互攀比惡果,掩卷思之,唯有嘆息。詩人雖然屏蔽了自我感情,只是客觀述事,但讀者仍能從中讀出詩人糾集于心中的憂思。用王國維的話說,這首詩是“以物觀物”,是客觀詩人之詩,可作為許紅娟平淡詩風的代表。
“白雪豐年,紅爐心語。飄香臘味和思煮。朔風小道望兒歸,山高路遠祈無阻。 "楊柳依依,北漂南旅。春秋歷盡經寒暑。近鄉忐忑步匆匆,娘親白發添幾許?”這首《踏莎行·盼》寫年關母子相盼團聚之情,母親是“朔風小道望兒歸,山高路遠祈無阻”,兒子是“近鄉忐忑步匆匆,娘親白發添幾許”,濃熾的情感以家常語出之,反而更顯感情的深摯。語言表面看雖未經刻意經營,但又是刻意經營才得來的,只是不著痕跡罷了。這首小詞又可作許紅娟平淡詩風的佐證。
平淡詩風作為詩歌的一種風格,歷來受到詩家的追捧。白居易一生追慕陶淵明,稱贊韋應物詩“高雅閑淡”。蘇東坡對平淡詩風也十分推崇,如稱贊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濃”,稱贊韋應物、柳宗元“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可見,能達到平淡詩風境界的,都是詩學修養、品格修養十分深厚的詩家。許紅娟離此當然路途遙遠,但她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需要提醒的一點是,平淡與枯槁貌似而神離,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前人批評梅圣俞詩貌似平淡,實乃枯槁。錢鐘書批評梅圣俞詩也說:“他‘平’得常常沒有勁,‘淡’得往往沒有味。”習“平淡”詩風者當以此為鑒。
許紅娟的詩,似村女出門,淺描眉黛,薄施脂粉,閑行小徑,在春風里挑野菜,在秋日里摘黃花,偶爾粲然一笑,也能動人。
(作者系國家一級劇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理事、湖北省戲劇家協會理事。曾任黃岡市文聯主席、黃岡市作家協會主席、本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