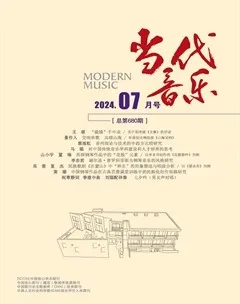論傳統音樂研究中音樂及人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摘 要] 從注重音樂形態(tài)的分析到關注音樂行為的研究,再到深入文化構成的闡釋,最終通過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以獲得對“人”與族群社會的研究路徑與可能性方向,是近年來我國傳統音樂研究的目光轉向和范式轉換。本文擬從傳統音樂研究的理論認知、實踐范式和成果具現三個層面闡述傳統音樂研究中音樂、人與文化之間的整體性關系。
[關鍵詞] 傳統音樂研究;音樂;人;文化
[中圖分類號] J607"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4)07-0199-03
中國傳統音樂是指“在中華大地上歷代產生并大多流傳至今,以及在古代歷史場合中由外族(包括現屬于我國的少數民族和國外民族)傳入并在我國生根發(fā)展的音樂品種和音樂作品,具體來說包括在歷史上產生、世代相傳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當代中國人用本民族延續(xù)下來的固有方法、采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創(chuàng)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態(tài)的音樂作品”[1]。我國以傳統音樂為對象的研究由來已久,在其漫長的研究歷程中,傳統音樂的研究在研究視角、研究側重、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與進步,并在此基礎上促生了傳統音樂研究中以“音樂——聲音形態(tài)為主體;人——音樂事象的操縱者為主旨;文化構成——音樂產生和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背景為統一體”的理論認知、以“客位切入——以客位視角切入研究對象;主位體察——參照主位角度定位研究對象;文化思考——進入音樂作為文化的學術思考”的實踐范式和以“音樂表演——作為一種文化行為;音樂持有者——作為一種文化真實;音樂理解——作為一種文化認同”的成果具現。
一、傳統音樂研究的理論認知
理論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縱觀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學術發(fā)展歷程,其理論認知完成了從注重音樂本體,到音樂本體與音樂持有者并重,再到注重音樂存在和表演的時間與空間背景的整體性研究的目光轉向。
(一)音聲主體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側重對音樂本體(音樂形態(tài))分析的歷史由來已久,尤其是在“歐洲音樂中心論”和西方音樂分析方法的影響下,偏重于對孤立音響與音樂作品的分析和視聽一度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主流,這里并不是對“孤立音響與音樂作品分析和視聽”研究持完全批評與否定的態(tài)度,因其恰恰是了解傳統音樂的律制、宮調、音階、樂譜等基本樂學的重要方式。但是對傳統音樂內含的音樂思想、哲學、審美等相關民族思維方式、價值判斷等不同的理論層次,甚至是對中國傳統音樂的“體系性”特質的研究,僅僅對“孤立音響與音樂作品分析和視聽”是不夠的。音樂的聲音形態(tài)和表演形態(tài)是通過人的音樂行為來具體呈現的,對傳統音樂音聲本體進行深入的研究,要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通過人外顯的音樂行為和音樂行為中內蘊的語言音調、審美選擇和民俗背景進行研究,以獲得對傳統音樂的整體性認知。
(二)行為主旨
有學者認為:“一切人文科學的性質,就是均不能停留在‘對象’成品的層面觀察,而必須從人作為文化締建者的心智活動去考慮,即人是音樂的象征與意義表達的‘編織者’與闡釋者。”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并賦予音樂獨特的文化象征意義,音樂不能在人的控制和行為之外存在,這也就說明了在傳統音樂的研究中人以及人的音樂行為的重要性。主觀上的“什么時候表演”(when)、“表演什么”(what)、“誰來表演”(who)、“怎樣表演”(how)的決定性因素都是客觀的“人”,而人的音樂行為是以音樂聲音形態(tài)和表演形態(tài)為表征的音樂過程的具體呈現,另外,這個過程的呈現亦包含了其背后的音樂組織行為。人的音樂行為(包括音樂表演行為和音樂組織行為)、音樂意識和音樂表演的時間與空間背景,構成了傳統音樂的全部內容。從人的音樂行為(包括外顯和內蘊兩個方面)“更容易全面解讀那些存活于民間的、有著生動之生命體驗的音樂之文化涵量”[2]。這與中國音樂學家郭乃安“音樂學要把目光投向人”[3]的愿景、楊民康“音樂研究怎樣‘把目光投向人’”[4]的探討、趙書峰“民族音樂學為何要研究人”[5]的闡釋等等一脈相承。因此,結合具體的時間和空間背景對音樂表演中的人,確切地說是對人外顯的音樂行為進行研究,是深入了解并揭示傳統音樂深層次的精神內核和文化內涵的重要方法。
(三)文化構成
我國傳統音樂的形成與建構是長期的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文化間的“濡化”與“涵化”的當代歷史格局,產生并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與人們的民俗節(jié)慶、婚喪嫁娶和生產勞動如影隨形,特別是有語言無文字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更是起著記述族群歷史、傳授生活技能等重要作用,并因地域、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等不同,形成了具有豐富樣態(tài)的中華民族文化。因此,中國傳統音樂是以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傳統中國來定義的一個范疇。將傳統音樂置于特定歷史背景與文化語境中研究,有利于在歷時與共時的角度研究傳統音樂的過去與現在。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利亞姆在1964年提出的“music in culture”“music as a culture”,強調將音樂置于文化中進行研究,或將音樂作為文化之一種,是“民族音樂學進入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后,所獲得的重要交叉學科理念和具體的深層內容指向”[6]。而日本民族音樂學家山口修強調的“重新構成音樂內部結構和脈絡結構并將音樂事象視為文化構成中的一環(huán),從各個側面來認識文化動態(tài)的本質”,與中國傳統音樂根植于中國特定文化背景的歷史現實與當代格局不謀而合。
因此,中國傳統音樂的研究就是通過對音樂——音聲主體和人——音樂行為的整體性研究,理解特定人群的文化構成,以揭示其社會生活的結構和族群文化的特性。
二、傳統音樂研究的實踐范式
隸屬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具有不同文化屬性的音樂傳統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統一體。在傳統音樂的研究中,研究者由于與研究對象所處社會、族群、階層的不同,使研究存在著“局內—局外”“主體—客體”的文化角色差異。為消解差異的影響,傳統音樂的研究可分以下三個階段進行。
(一)客位切入
“客位切入”是傳統音樂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是針對“音聲本體”的研究階段。在傳統音樂的研究中,音樂、人、文化是作為統一體存在的,無法割裂任一元素對其他內容進行整體性研究。以“客位”為視角、以“音樂”為焦點切入研究對象,是作為“局外人”的限定身份研究傳統音樂的有利方式。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存在著包括族群、信仰、習俗在內的較為豐富的多元文化,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流動與變遷,音樂常常成為信仰儀式和民俗活動的情感表達手段。“客位切入”是將傳統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通過對其音聲主體的分析,達到對傳統音樂基本樂學的認知,并依據人的音樂行為和音樂表演的語境達到對傳統音樂的表征層次的理解,從而進一步管窺這一地區(qū)人們的真實生活與文化屬性。
(二)主位體察
完成第一階段——傳統音樂研究的“客位切入”階段,為更為深入地研究傳統音樂,則需要進入體驗并參照局內人的“主位”觀念和認知角度,即針對音樂持有者的研究階段。美國學者胡德提出的“雙重音樂能力”是“主位體察”階段較有代表性的論斷,胡德的“雙重音樂能力”,就是讓西方的學者去親身體驗西方音樂之外的音樂,以此在經驗上擺脫西方音樂中心判斷,形成真正的多元文化觀念。音樂持有者(或稱“局內人”)的音樂行為遵循著一定的音樂心理和音樂組織管理等規(guī)約,是基于“局內人”文化理解基礎上的意識形態(tài),并因個體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教育背景等綜合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差異性。以主位的觀念和“局內人”的認知角度去體驗音樂行為,并試圖借用“主位”的觀念建立“局內人”對音樂事象的理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證實所研究的傳統音樂是作為一種藝術的存在,還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存在。而后,根據研究對象的基本性質,施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策略。這既是傳統音樂研究中行為主旨的深化,也是主位體察研究范式的體現。
(三)文化思考
將音樂事象視為一種文化,已成為當下音樂學界的共識。“文化思考”是傳統音樂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進入“音樂作為文化構成”的學術境界,也是傳統音樂研究成果具現的重要過程。前兩個階段分別通過客位切入和主位體察完成了對音聲本體的分析與研究、對音樂持有者的音樂行為的“局內”認知,研究者完成了對傳統音樂的“描述”和“闡釋”,第三階段則進入最為重要且最有價值的“自反”階段,即文化思考。通過對音聲主體的分析、音樂行為的體察實現客位向主位、描述向闡釋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思考,進一步實現音樂觀察向文化理解的轉變。因此,傳統音樂研究的三階段實踐范式,既是研究過程的遞進,也是研究層次的深入;既有對音樂、人、文化的整體性關注,也有“主客位”“局內外”的雙視角介入。
綜上,傳統音樂研究的實踐范式中,“客位切入、主位體察、文化思考”,既是完整的研究傳統音樂的過程,也是研究層次的逐步深入,更是將音樂、人的音樂行為以及音樂作為文化的整體性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具體呈現。
三、傳統音樂研究的成果具現
在“音聲主體、行為主旨和文化構成”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傳統音樂“客位切入、主位體察和文化思考”研究的實踐范式,完成了文化理解基礎上的學術思考,即音樂——音樂的聲音形態(tài)和表演形態(tài),作為一種文化行為;人——音樂行為的締建者,作為一種文化真實;文化構成——音樂理解,實現文化認同的愿景。
(一)文化行為
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歷史文化下產生和發(fā)展的傳統音樂,與人們的民俗節(jié)慶、婚喪嫁娶和生產勞動如影隨形,具有仰天敬神、記述歷史、教育教化、娛神娛己的功能。一些在固定節(jié)日、固定場合、有嚴格表演程式的傳統音樂的類別,如宗教儀式音樂、民俗節(jié)慶音樂等,不僅是一種藝術表演形式,更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行為。如客家山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度被認為是不正經,甚至是傷風敗俗的下流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傳統民間文藝在文藝政策的影響下,被納入到文藝建設的軌道,從而有了積極且正面的形象。至此,以客家山歌為代表的傳統民間文藝已不僅僅是表現男女愛情故事的自我娛樂,而是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相結合的藝術文化形式,其表演也成為一種文化行為。因此,傳統音樂的聲音形態(tài)和表演形態(tài),既有藝術的成分,也有文化的成分,即傳統音樂的表演是具體的人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中,以音樂表演為主要形式的文化行為。而在這個文化行為過程中,音樂——音聲主體、人——音樂行為、文化構成——音樂表演的時間和空間的統一體,三者共同構筑了傳統音樂的文化行為。
(二)文化真實
傳統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人賦予傳統音樂獨特的文化象征意義。人——音樂的持有者,是傳統音樂存在的載體,人的音樂行為、音樂意識和音樂作品,構成了音樂藝術的全部內容,而音樂行為的具象性決定了人是傳統音樂研究的中心和主旨。傳統音樂的生產生活特性,決定音樂持有者的音樂能力是基于文化理解基礎上的自然習得,其音樂行為也是基于自身特點在某個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具體呈現,并在音樂事象呈現的過程中以其主觀能動作用賦予音樂藝術強大的生命力和積極的價值意義。“苗年”是苗族人民的傳統民俗,是為悼念苗族始祖蚩尤、慶祝豐收、祭祀祖宗神靈的集體性和紀念性節(jié)日。每至苗年,苗族家家戶戶、男女老幼紛紛參與到苗年的慶典中,苗族人民對歌群舞、斗牛跑馬,苗寨蘆笙齊鳴、熱鬧異常,每一個苗族人民都是苗年文化的承載者,通過一致的文化行為展現共同的文化心理,以此塑造并映現作為文化真實的苗族人民。因此,作為音樂文化持有者的人在整個音樂表演過程中是文化真實的存在。
(三)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的基本意義是對群體文化的認同感,或者是一種肯定的文化價值判斷。”[7]全球化、現代化在促進社會轉型的同時也引起了文化危機,促使文化認同成為重要的時代課題。對傳統音樂的研究,一方面是延續(xù)傳統以保證未來文化創(chuàng)造的“根脈”,避免文化危機造成的文化斷裂,另一方面也是對由“歐洲音樂中心論”引起的文化霸權的抗爭和自我文化生存權利的維護。傳統音樂研究“音聲主體、行為主旨和文化構成”的理論認知和“客位切入、主位體察和文化思考”的實踐范式,構建了以“音樂—人—文化”為整體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并最終達到了傳統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和音樂文化持有者作為一種文化真實的認知,并不斷促成中國傳統音樂的文化認同格局的構建。
文化行為、文化真實和文化認同分別代表著傳統音樂研究中音樂、人與文化的研究成果的直觀體現以及三者在傳統音樂研究中的整體性關系,即音樂表演形態(tài)是音樂文化持有者在具體的文化背景中的音樂行為。
結" "語
在傳統音樂研究中,“音樂”“人”與“文化”三者兼具歷史性與同一性交叉、同一性和當下性融合之關系,即“樂”“樂人”“樂事”三者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當前,我國傳統音樂的研究已經逐步實現從單純的注重音樂形態(tài)分析到關注音樂表演形態(tài)與音樂行為、文化背景之間關系的理論認知轉向和實踐范式轉換,即以“音聲主體、行為主旨、文化構成”的理論認知和以“客位切入、主位體察、文化思考”的實踐范式,實現“文化行為、文化真實”的研究格局,不斷推動實現“文化認同”的研究愿景。傳統音樂研究的理論認知、實踐范式和成果具現,無不透視著“音樂、人與文化”在傳統音樂研究中的整體性關系。
參考文獻:
[1] 蕭梅.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述要[J].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09(02):58-73.
[2] 楊曦帆.區(qū)域音樂研究實踐——再論民族音樂學在“藏彝走廊”學說中的探索[J].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5(01):108-114.
[3] 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J].中國音樂學,1991(02):16-21.
[4] 楊民康.音樂研究怎樣“把目光投向人”?[J].音樂研究,2019(01):40-42.
[5] 趙書峰.民族音樂學為何要研究人[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0(04):7-12.
[6] 伍國棟.音樂學的學科跨界研究——以民族音樂學為例[J].音樂研究,2014(01):17-23.
[7] 崔新建.文化認同及其根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4):102-104,107.
(責任編輯:韓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