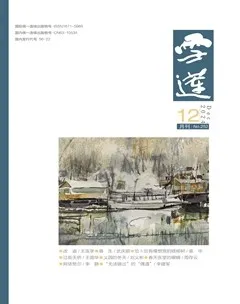扎根故鄉與輾轉遠方之間的行吟者
【作者簡介】張紅,青海省民和縣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會員。詩歌、評論發表于《青海日報》《中華詩詞》等報刊。
七月已是熱烈的季節,夏云暑雨的飄逸和浸潤,也不曾留意。窗外流水落花,山色涳濛,不似江南的煙雨,卻是夏都的情絲。
法國批評家圣佩韋在《新星期一漫談》中說:“不去考察作家而要判斷他的作品,是很困難的。”“王偉,男,二十九歲,身高一米八五……”(《尋人啟事》),“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王偉的溫文儒雅,是詩人身影在腦海中的記憶。“詩言志,歌詠言”,談吐之間,娓娓道來,筆墨所至,飽含情愫。“我,一個而立之年的男人……想在詩里活成意象……”(《自畫像》),“我熱愛詩歌寫作,它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詩歌寫作始于我的大學時代,在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習漢語言文學的四年時光里,我懷揣詩歌的夢想翻閱了圖書館里能找到的中外詩集,在這些詩集中認識了許多有代表性的大詩人,他們都在為詩歌這門藝術而堅守、探索和奉獻……詩歌寫作是寂寞的,而為之堅守、探索和奉獻更是艱苦的……詩歌寫作卻是詩人生命的寄托和延續……”作為生活于都市和鄉土、傳統與當代的時代歌者,他的詩歌創作既是對自己出生的故鄉、傳統文化的皈依,也是對精神家園的追慕。
“……著名詩人兼詩歌評論家陳超老師,他是我大學時期的導師,受其‘生命詩學’‘歷史想象力’‘先鋒詩論’的詩學影響,并在聆聽其‘現代詩研究’課和私下對我的詩歌寫作指導中,讓我對詩歌有更深的認識,寫作方面有明顯的提高,也助我漸漸走向成熟寫作的階段。”與恩師陳超的流光印跡在詩人生命長河中不舍晝夜的點滴匯聚,孕育了他詩性泉源的源頭活水。“當初,轉院的初衷除熱愛文學,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能學習陳超老師的現代詩學……”“我與陳老師從《現代詩研究》課開始有了交集……”“從那時開始,我經常求教于陳老師……我把自己覺得寫得可以的詩歌打印在A4紙上拿到陳老師面前請教……我迫不及待地盼望下節課的到來,希望陳老師對我的詩歌可以給予較高的評價。有一次,給陳老師的六首詩歌……陳老師把寫得好的句子畫出來,針對每首詩寫上評語。每一次的評語都切中我詩歌寫作上的軟肋,醍醐灌頂般使我突然醒悟。”“陳老師見我交卷便把我叫到教室門外的走廊里,用關愛和期望的語氣對我說:‘你有寫詩的天賦,以后好好寫作,寫出自己滿意的詩歌后可以發到我的郵箱,我白天忙沒有時間查看郵件,一般晚上會回復信件。’”“我的詩歌寫作的提升離不開陳老師的悉心教導和點撥……畢業后,我一寫出自己滿意的詩歌就給陳老師發過去,每次都會在晚上收到陳老師的指導意見和今后讓我學習的方向……”
“有德者必有言”,王偉作為“80后”詩人,對腳下這片熱土的摯愛是他寫作的“根”,他深愛這片文化融合、風情各異的土地,因此,注定要為他書寫文字。“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時代的創造者。在人民的壯闊奮斗中,隨處躍動著創造歷史的火熱篇章,匯聚起來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詩。人民是文藝之母。文學藝術的成長離不開人民的滋養,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我們“80后”一代人與時代同行,本已是宇宙中的點點星光,歲月的印記已然成了不用書寫的詩行。
《江湖》分為四篇,分別是“行走江湖”“四海為家”“笑傲紅塵”“偏安青藏”。共收錄詩人十余年創作的八十余首詩歌,盡是詩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真情流露。第一篇“行走江湖”共29首詩歌,第二篇“四海為家”共15首詩歌,第三篇“笑傲紅塵”共12首詩歌,第四篇“偏安青藏”共31首詩歌。“每一篇的主題依次是江湖元素、異鄉時光、青春愛情、高原生活。之所以以‘江湖’命名,是我把自己當成一位行走江湖的書生,在詩歌的江湖里拜師學藝、游蕩四方,并在‘刀光劍影’中闖天涯。我力圖在詩歌中加入一些江湖元素,使我的詩歌有些陌生感和獨特性。”
什克洛夫斯基告訴我們,陌生化程序是一種藝術程序,因為一旦對事物使用這種陌生化程序,不僅在讓去感覺此事物時真正感受它,而且還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通過采用陌生化程序,事物在藝術作品中鮮明突出其本來面貌,就使讀者不得不去感受它,專心致志,聚精會神,流連忘返,樂而忘歸。不僅是江湖元素,就是上海、黃浦江、上海灘、南京路、和平飯店、7號地鐵(《相忘于江湖》),紅旗大街495號門口、石家莊(《今夜,我睡了大半個中國》),長沙(《通往長沙的道路很別離》),河北師大文學院(《最后的行程》)這些習以為常的地名在詩歌里也變得異乎尋常地突出和顯豁,使我們從熟悉中感覺到對象的異乎尋常、非同一般,使人為之震顫、使人重新回到觀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
當代的我們,故鄉也許不止一個,我們生活過的地方可能都是故鄉。故鄉對于我們有一種特別的情分,只因生于斯長于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里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后有時也要想念到他。北京、上海、長沙、石家莊之于詩人可能也有難以割舍的故鄉情節。但對于青海,他要告訴我們的,并不單單只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還有那寫不盡的疼痛與熱愛。
詩人直面生活與自然凝然默思,將過往潛入內心深處,將個人真切的感悟轉化為一代人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體驗與思考。天地大美、三江之源、巍巍昆侖、唐蕃古道、民族風情、卓瑪姑娘、帳篷湖光、草原牛羊、街頭巷尾、良師益友、父老鄉親、女兒雅嫻……皆沉潛于意識,躍動于筆端,融鑄于詩行。異地求學、京滬打拼,砥礪奮進、眷戀故土、成就事業、營造家園、孕育生命、回首往昔、澄明燭照、百川入海、逸情江湖、泛舟詩海……這件件樁樁遂成了我們一代人心路歷程的色調。表現這些主題時,是努力追求形象的、生動的。詩人的見聞、知識,被調動起來構成具體而富于個性的詩歌形象,并編織成有明朗色彩的生活畫面。并且,這些生動鮮明的圖景,與詩人的不加控制的激情交融在一起。是當代人在當下生活中所感受的當代的情緒,用當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當代的詩形。詩人濃烈真摯的情感,對時代和歷史所做的思索,從比較開闊的角度去反映一代人親臨的世事過往,并以在生活中提煉的某種思想作為構思的線索,用最原始的語言捕捉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在一個維度上抒發了我們的心聲,從廣闊的歷史進程和詩人的生活道路上,描繪了我們身處其中的時代形象,表達了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詩人往往從小處落墨,從一個具體的角度或側面,表現觸動過他的事物,但他的詩并不停留在局部生活現象的表面上:它們不是清晨草葉上雖晶瑩但微細的露珠,而是生活長河中波浪濺起的明亮水花。詩人明了他的努力方向,從他所描寫的點點滴滴上尋找、揭示有時代內容、時代色彩的形象和思想,把平凡的事物寫得不平凡。詩中的思想,是要靠真摯的情感和美的形象來表現的。他從生活點滴揭示具體事物所包含的社會內容的寫法,不是靠對生活現象平淡的記錄,也不是靠一些思想概念的綴合。他對事物,尤其是自然景色有敏銳而細膩的感受力。他時刻睜大著對生活感到驚喜的眼睛,迅速抓住事物的某些特征,并與他豐富新鮮的聯想、比喻的才能結合起來,使他在描繪景色,勾勒人物身影時,做到語言精煉,落筆自然,而詩人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情,也自然地蘊含在這些動人的描繪中。
艾青指出“樸素是對于詞藻的奢侈的擯棄;是脫去了華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掙脫了形式的束縛的無羈的步伐;是擲給空虛的技巧的寬闊的笑”。詩人樸實地去捕捉每一個形象,尋找、錘煉每一個字句,頑強地追求著“深刻到家、深刻到淺易的程度”的藝術境界。在親切的日常生活調子里舒卷自如,敏銳、精確,而又不失它的風姿,有節制的瀟灑和有功力的淳樸。詩歌大量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選取了許多詩人生活中最常見的意象:青稞酒、文成路、塔爾寺、格桑花、郁金香、瞿曇寺、青海湖、鳳凰山、德令哈、巴音河、藏羚羊、柴達木、經幡、岡拉梅朵、金銀灘草原、卓瑪姑娘、青海“花兒”、鍋莊等等,從而形成親切感,詩歌的語調平靜,不動聲色,確實是一種“有節制的瀟灑”。這藝術表現上的親切、溫和、含蓄,既吸收了波德萊爾、魏爾倫、艾略特詩的特點,又與中國“哀而不傷”的詩歌傳統相通,以真摯的感情作骨血,白描的色彩、青春的感傷、精致的藝術,鋪張而不虛偽,華美而有法度,這是真正美麗的詩,永遠天真而自得其樂的詩人,“往往叫你感到,他之訴苦,只因為他太愉快了,需要換換口味”。
王偉是一位具有哲學氣質的詩人,他的詩常給人“于平淡中出奇”之感,就是因為善于對日常生活現象進行哲學的穿透和開掘。《你是我今生夢想抵達的遠方》《最后的行程》《肉刺:遺址——悼念恩師陳超》《我思故您在》等詩篇接觸到了許多現代哲學命題,他所表現的是一些生命的追問,是哲理的沉思,將外在的生活經驗化為內在的生命體驗,用平淡掩深摯,從感嘆出辛酸,將抒情理性化。“廣大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才能把握時代脈動,才能領悟人民心聲,才能使文藝創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雋永的魅力。”詩人的大愛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情感的直錄,《站大腳的人——寫給農民工兄弟》《爺爺的馬車》等詩作通過哲學的思索演繹,從中重新發現我們民族的歷史、生命和文化深邃的內蘊,力圖在當代背景下,表現出一種深藏在普通人民身上的堅韌強勁的民族精神和古老民族的頑強生命力。
詩人重視從中國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中吸取有表現力的語言、形象。表現了詩人向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和現當代文學名家汲取藝術養料的獨特眼光與巨大熱情。“千字萬言難抒意,誰人能消萬古愁/呼朋引伴且為樂,把酒當作逍遙客”(《夢回大唐》),“一日看盡長安花”(《在文成路想起公主》),“采菊南山下”(《紙上江湖》),“此地空余黃鶴樓,白云千載空悠悠”(《天上江山第一樓》),“腳踏青云梯兮欲雨,心臨湘江水兮生煙”(《通往長沙的道路很別離》),“出紅塵而不染”(《遇見你,我的思念很詩歌》),“可惜人面不知何處去,可嘆桃花依舊笑春風”(《久別的鄉村,久別的鄉親》),“哪怕霧霾壓城城欲摧”(《過路旅人的憂傷——致黃金時代》),“春色滿園關不住”(《貴德,貴德》),“今夜,我跛腳的馬蹄悲鳴,我不是歸人而是過客”“輕輕地我來了,正如我輕輕地走”(《通往長沙的道路很別離》),“關心糧食和蔬菜”(《自畫像》),“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明月裝修了出租屋內的鄉愁”(《時光的側影》)。
詩歌組織得嚴密整齊,重視行與行、段與段之間大體上的對稱。抒情方式上,采用鋪張渲染、反復詠嘆的方法,來達到雄渾、熱烈、濃郁的藝術效果。“在美麗的西寧,我寫三首抒情詩……/在美麗的西寧,我寫三首抒情詩……/在美麗的西寧,我寫三首抒情詩……”(《西寧抒情》),“在哪里,是那里……/在哪里,是那里……/在哪里,是那里……/在哪里,是那里……”(《天上金銀灘》)。詩歌在整體鋪張的詩風基礎上,也注意局部的凝練含蓄。發揮那種清新動人的富于生活實感的描繪方式和想象方式,又使對這些生活現象的描繪,帶有象征色彩,并加強詩歌抒情的哲理內涵。采用內心獨白的技巧,表現詩人微妙的心理活動乃至一閃念的潛意識,增加了作品象征意義的豐富性。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告訴我們:“文學對每個現代而言都是當代的”,理解的歷史性構成了我們的偏見。秘魯作家略薩指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又是一個每位讀者可以從中發現不同含義、不同特色、甚至不同故事的潘多拉的盒子。”對王偉詩集《江湖》的品讀可能算是這眾多“偏見”中的之一吧。
“一切有追求、有本領的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不斷發掘更多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現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風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創新,努力創作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身處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有這樣的期許,我們是幸運的。期待詩人“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著不朽之華章。
普魯斯特筆下的馬賽爾曾向我們述說:“隨著年華流逝,一切物質的東西都要被時間銷蝕,最終灰飛煙滅,只有感覺到的、經歷過的東西才是真正的存在。雖然那種由人的心靈感受到了的東西,可能沉睡在意識的底層,或者被現在的其他感受所覆蓋,但他們不會在歷史長河消失,有朝一日,在某種外界感受的激發下,會從心靈深處浮現,上升到意識的表層,此刻,昔日復活,時光重現。”伴著窗外的雨聲,合上書頁,靜坐窗前,歲月不停在眼前閃過,曾經以為,老去是很遙遠的事情,凝神靜思,才突然發現,年輕似乎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會心一笑,便自語道:“時光好不經用,轉眼之間,已然半生。”好在“時光流淌而記憶雋永,生命有限而藝術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