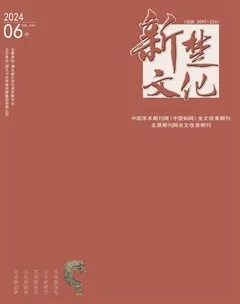《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倫理選擇
【摘要】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被掩埋的巨人》書寫了記憶碎片化的個體與群體的記憶困境,及由此引發的倫理問題。個體的差異導致了小說中人物面對的不同的身份認同危機與倫理選擇的困境,本文采取文學倫理學的批評方法,對小說中人物的倫理選擇進行分析,探究石黑一雄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以記憶遺忘為主題所要揭示的深刻思想與人性反思。
【關鍵詞】《被掩埋的巨人》;記憶;倫理選擇
【中圖分類號】I106.4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7-0045-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7.014
【基金項目】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五育并舉”視域下文學審美教育的改革與實踐(項目編號:JLJY202262756196)。
《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于2015年3月出版,該作品是石黑一雄的第七部長篇小說。“記憶”一直是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中心主題。這本長篇自面世以來褒貶不一,卻不影響瑞典學院將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彼時國際性關注度并不高的石黑一雄,這與他作品中一向展示的濃厚的社會責任心有所關聯。在《被掩埋的巨人》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以探索記憶的形式進行書寫,并對民族仇恨問題展開探討,這體現了他對國際人文的關注。背景設定在中古世紀亞瑟王所統治的不列顛,亞瑟王在獲得勝利后,對撒克遜的村子展開了大屠殺,并讓魔法師梅林對母龍魁瑞格施予魔咒,使讓人遺忘的迷霧籠罩在大陸之上,從而遮蔽了歷史的殘酷真相,營造出了虛假的和平。主人公是不列顛老夫婦埃克索(Axl)和比特麗絲(Beatrice),他們為了尋找自己的兒子而一起離開村莊,在路上遇到了來自東方的武士維斯坦(Wistan)、亞索王的騎士高文(Gawaine),并在旅途中逐漸發現有關失憶的真相。在這部小說中,忘卻的迷霧吞噬了人們對于戰爭的傷痛,而探尋記憶則代表著復仇的延續。在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看來,這是一次讓他們無法輕易取舍的倫理與人性的兩難困境。該作品借助記憶為構筑,高度關注國際背景下軍事沖突與和平安全風險和進而形成的人類文明生存環境的問題,在遺忘的洪流中揭露出個體身份的困境;立足于人類文明生存環境從倫理學層面對人本身展開反思,有助于我們從人類過往歷史悲劇中汲取經驗教訓,對人類發展的未來提供價值幫助。
一、失憶迷霧下的倫理困境
在小說開篇時看似寧靜祥和的村莊卻發生著奇怪的事情,人們總是在遺忘過去發生的事情,前一秒還在尋找孩子,下一秒卻開始為其他事情爭吵起來。“過去消失在一片迷霧之中,就像沼澤地上的霧氣一樣。這些村民就從沒想過要去回想往事——哪怕是剛剛過去的事情。”[1]7村莊中的人們并不知道為何會失憶,也不去探究原因,主人公埃克索夫婦也同樣迷失在失憶的迷霧中,他們忘記了自己兒子的長相與聲音,也記不起為什么兒子沒有在他們的身邊。迷霧遮蔽了人們的記憶,并帶來了各種倫理困境。
以文學倫理學批評視野解讀作品文本需要從人物倫理身份的建構出發,并找尋身份認同危機造成的原因,以此來研究倫理問題。“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往往都同倫理身份相關。”[2]小說中角色的倫理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在情節發展推動的過程中,倫理身份會發生轉變,對自我身份的喪失或建構會導致角色在倫理困境中作出倫理選擇的不同。由于失憶迷霧的存在,記憶以碎片化的形式被漸漸拼湊起來,對于身份認同的混亂,使得角色難以作出倫理選擇。研究文本中的倫理問題有助于對作品主題及作家所表達的價值的進一步了解。
主人公埃克索夫婦因為兒子的失蹤失去了作為父母的倫理身份,對于自我的認知有所缺失,正是這一原因導致他們對尋找兒子一事的迫切。但在尋子的旅途中,又再次面臨了他們夫妻這一倫理身份的危機。當他們得知擺渡船夫會問要上島的夫婦關于他們最珍貴的回憶時,他們的內心是恐懼的,因為迷霧奪去了記憶,埃克索和比特麗絲間沒有了過去,又該如何能夠證明他們對彼此的愛呢?“我在想,沒有了記憶,就沒有了源頭,我們的愛會不會慢慢枯萎、死亡。”[1]44對于他們二人來說,曾經的甜蜜回憶是能證明他們對于彼此愛的最有力證據,如果連在一起的記憶都不記得,又怎么能確認對方的心意。從這一點來說,埃克索夫婦的追尋記憶之旅不僅能找到兒子的線索,又可以使彼此的愛更加牢固,否則夫妻之愛就可能枯萎甚至消亡。
隨著旅途的不斷延伸,埃克索夫婦越發接近事情的真相,迷霧導致失憶的真實原因也呼之欲出,這一切竟都是由母龍魁瑞格所造成的,在比特麗絲知曉真相后,當即就希望以母龍的死來尋回自己失去的記憶:“埃克索,你聽到了嗎?迷霧是那條母龍造成的!只要有人能殺掉它,那我們的記憶就可以恢復啦!埃克索,你怎么這么安靜呢?”[1]154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對于她來說,殺掉母龍不僅可以恢復記憶,還可以重新建構自己作為“母親”這一倫理身份。而且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他們找回曾經相愛時的回憶,確立忠誠于彼此的愛人身份。埃克索對于恢復記憶之事卻并不如比特麗絲那般激動,像是在害怕什么一般:“你這么確定不要這迷霧嗎?有些事情藏起來,不放在心里,難道不是更好嗎?”[1]157喬納斯神父的話語縈繞在埃克索心里,對于迷霧所帶來的失憶究竟是好還是壞,他內心中有所猶豫,在之后的旅程中,記憶的碎片不斷拼湊起來,原來遺忘的記憶并不都是美好的,其中也包含著傷痛,埃克索與比特麗絲的情感早就出現過問題,他們之間沒有比特麗絲認為的那樣恒久的愛,甚至還發生過激烈的爭吵,而他們的兒子因為厭倦了爭吵離開了他們,卻死于一場瘟疫。也就是說,他們作為父母的倫理身份已經失去了,而且在遭遇情感背叛后,又失去了作為丈夫的倫理身份,對于埃克索來說,這場遺失記憶的迷霧為他重新帶來了作為父親和丈夫的倫理身份,因此對于殺母龍這件事情,他的內心才如此抗拒。“愛這個東西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又是基于什么?是不是基于共享了共同的回憶呢?當直面死亡的時候,愛又會變成什么樣?愛是否是一種能夠超越死亡的強大事物呢?”[3]在個體面對過去的傷痛記憶時,要如何與過往經歷達成和解,個體記憶的形成是需要在人際交往中形成的,埃克索夫婦的個體記憶源于彼此共同的經歷,以及對他們記憶中的兒子的回憶,如果他們是完全孤立的個體,那么記憶對于他們來說也無從考證。
二、尋憶終點的倫理選擇
在埃克索還是亞瑟王忠誠的騎士的時候,他曾為了保護在戰爭時期的撒克遜村莊不受傷害而奔走,并與撒克遜人簽訂了法律,被當地人稱為“和平騎士”受人敬仰,然而在戰爭打響后,亞瑟王下令讓騎士屠殺村莊中的小孩老人,并希望以此根絕復仇的種子,這是埃克索另一次覺得自己遭到背叛,亞瑟王的指令使得他成為一個背信棄義之人。他將記憶的碎片逐漸拼接在一起,終于勇敢地承認了自己亞瑟王騎士的身份,并揭開高文爵士的偽裝,指出其母龍守護者身份,至此埃克索已經斬斷了籠罩他記憶的迷霧,點亮了黑暗過去,重建了自我身份。
“今天下令對那些撒克遜村莊動手時,我舅舅肯定心情沉重,他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別的方法獲得持久的和平。想想吧,先生。你憐憫的那些撒克遜男孩,很快就會成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為今天喪生的父親報仇。那些女孩的子宮里很快會生長出更多的武士,這屠殺的魔咒永遠不會破解。你看看復仇的欲望有多么強烈!”[1]216對于高文來說,出于一名騎士的倫理身份,他必須忠于自己的君主,所以他對于亞瑟王的決定盡管有所疑慮,但依然去堅定地完成命令。先前他與同伴一同前去屠龍,而如今卻成了巨龍的守護者,對外宣稱自己身負屠龍任務以掩人耳目,這當然不能被世人理解,他作為騎士的倫理身份得不到認可。在文中高文的兩次浮想里,他其實已經認識到了當年的倫理選擇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但依然在內心中希望亞瑟王的決定并沒有錯,自己作為執行命令之人也同樣是正確的。“倫理選擇按照某種社會要求和道德規范進行選擇,按照做人的道德目標在特定的倫理環境和語境中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是在教誨和學習過程中進行的”[4],在面對以埃克索夫婦為首的失憶者的反對時,他的內心中的天平便開始傾斜,認為戰爭確實造成了很多錯誤。在第二次浮想時,他想起了當年屠龍戰死的戰友臨死前的請求,甚至想到了自己死前的樣子還有戰馬的下場,這意味著他的內心或許早已承認了維斯坦的主張,盡管如此他最后還是選擇作為一名亞瑟王的忠誠騎士而死,他曾見識過仇恨所帶來的因果:“這時候她來了,站到他眼前,盾牌丟在一邊,她的眼神讓我脊背發涼,超過那可怕戰場上的一切。然后她的鋤頭下來了,不是掄起胳膊甩下來,而是輕輕地鋤一下,接著是第二下,好像她是在刨莊稼一樣……但她不再聽我說話,又去做她那可怕的事。”[1]214戰場上柔弱的女孩被仇恨意志所驅使,對著撒克遜士兵的尸體一遍遍揮舞著武器以宣泄這份怒火。在母龍魁瑞格的迷霧中,這大屠殺的記憶得以遺忘,暫時掩埋了仇恨的巨人,“死者安息于地下,地上早已覆蓋著怡人的綠草。年輕一代對他們一無所知。我求你離開這個地方,讓魁瑞格的作用再發揮一段時間”[1]294,為了守護這虛偽的和平,高文與維斯坦決戰于巨人冢,在最后一刻他還在祈求維斯坦可以讓這和平再持續一陣。高文保護魁瑞格的這一倫理選擇雖然被認為是站在惡的立場,但其本身目的是為了和平的延續,哪怕這份和平是虛假的。而堅定的屠龍者維斯坦則是出于另一種倫理選擇,將民族集體放置于第一位,拋棄了個人情感,誓要讓不列顛人付出代價。維斯坦這一選擇雖然看似是為了民族利益,但卻會引起新一輪的仇恨循環,甚至可能演變成兩個民族間無休止的戰爭。
三、直面歷史的傷痛
在維斯坦與高文于魁瑞格前對峙的時候,二人之間進行了短暫交談,雖然想要達成的目的不同,但他們的行為都有其合理性。維斯坦在與埃克索夫婦踏上旅途前對自己的任務是十分堅定的,但在這段經歷后,他對自己復仇的狂熱有了迷惘:“維斯坦從坑里爬出來,花了很長時間,令人感到意外。最后,他終于來到兩人面前,顯得垂頭喪氣,一點兒凱旋的模樣也沒有。”[1]304失憶的迷霧終于消散,維斯坦并未流露出目的達成的開心之情,相反,疑慮和憂郁的種子在他內心不斷發芽。是否應該將復仇的怒火同樣對準不列顛人的小孩和老人?該如何才能實現自己想要的復仇?在這一連串的思考中,維斯坦完成了他的倫理選擇。
維斯坦曾讓男孩埃德溫承諾自己會仇恨所有不列顛人,他意圖將埃德溫培養成一個新的戰士,一個比他更絕望的戰士。在先前迷霧影響下,埃德溫只是盲目聽從維斯坦的指揮,但在恢復記憶后,他開始嘗試自己作出選擇:“維斯坦肯定沒打算把這對好心的夫婦也包括在內吧。”[1]310埃德溫即使背負了民族仇恨,也還保留著自我的判斷,并未被仇恨的因果所掌控。在這次旅程過后,他同樣也在建構自己作為撒克遜人的倫理身份,對他之后的倫理選擇也會有所影響。青年一代對于歷史的傷痛選擇記憶,那么民族歷史文化也會被傳承,青年們不會再盲目地生活。而也正因為遺忘,不列顛和撒克遜這兩個仇視彼此的民族才能安享短暫的和平。遺忘在集體生活中起著積極的影響,不僅遮住了戰爭的傷疤,還試圖填補戰爭所帶來的裂痕,成為兩個民族和解的催化劑。在母龍魁瑞格死掉之后,這片大陸的人們會記起黑暗的過往,作者并未交代之后的情節發展,這一開放式的結尾使讀者可以開闊想象延續故事,但我們從書中的情節線索來看的話,新一輪的戰爭、仇恨及宗派暴力,仇恨的種子會再一次播撒在每個人的心中。石黑一雄對于記憶與遺忘的主題又一次發問,對于歷史我們是該遺忘還是該銘記?亞瑟王利用遺忘的迷霧使得撒克遜民族暫時忘記了仇恨以及受害者的身份,關于暴力事件的記憶雖然可以壓制,但卻無法完全抹去。“為了厘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系。對歷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會再犯以前的過錯。”[5]在歷史問題面前,領導階層不應該只想著如何篡改歷史記憶,而是要直面歷史對兩個民族間所帶來的傷害,如若對過去發生過的事情熟視無睹,也會造成二次傷害,就如維斯坦對于失憶迷霧的憤恨,本就因為本民族遭遇屠殺一事而心生仇恨,對方甚至意圖掩蓋這一事實真相,這不會抹平受害者所遭受的苦痛,在真相揭露后,只會讓仇恨加深。集體記憶的缺失會讓個體缺失歸屬感,埃克索夫婦在小村莊中生活時,總是有著一種茫然無措的感覺,并不知道為何自己會待在這里與撒克遜人一起生活,個體可以構成集體的記憶,卻難以對其產生影響,所以對待集體記憶,要以一種理智客觀的態度去審視。
四、總結
石黑一雄以記憶遺忘為主題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對故事進行刻畫描寫。他通過寓言式寫作,搭建了一個中世紀背景的奇幻隱喻性世界,并刻畫小說人物的種種困境,深入挖掘人物內心與情感狀態、在倫理困境時所作出的倫理選擇的不同,其意義是想讓人們思考文本中的倫理意義與價值。石黑一雄在談及該小說創作契機時曾說,自20世紀90年代前南斯拉夫發生種族清洗以來,他開始思考社會記憶和集體遺忘。他看到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也看到了人們面臨災難所做出的選擇。他通過這部小說對讀者提出發問,對于黑暗不堪的歷史,是該記憶還是遺忘?以我的理解來看,石黑一雄是認為要對歷史進行記憶的,不管是怎樣傷痛的歷史,人們都要承擔起自己的倫理責任,只有正視歷史的問題,才能作出正確的倫理選擇,得以構建正確的倫理身份,在倫理層面實現自我超越,對當代社會有所警示與啟發,這顯示出了石黑一雄對于世界與人文的高度關注。
參考文獻:
[1]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M].周小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2]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J].外國文學研究,2010,32(01):12-22.
[3]陳婷婷.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訪談錄[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7(01):105-112.
[4]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價值選擇與理論建構[J].中國社會科學,2020(10):71-92+205-206.
[5]徐賁.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J].法制資訊,2009(02):33-35.
[6]吳玲英,郭龍.論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記憶書寫[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6(02):151-158.
[7]韓偉,胡亞蓉.記憶的責任與忘卻的沖動——對《被掩埋的巨人》的文學倫理學解讀[J].外語教學,2018,39(06):102-107.
[8]唐曉芹,石云龍.記憶、遺忘與寬容:《被掩埋的巨人》中的人文思考[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3(04):140-144.
作者簡介:
姜兆軍(1997-),男,吉林長春人,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高紅梅(1974-),通訊作者,女,遼寧岫巖人,博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