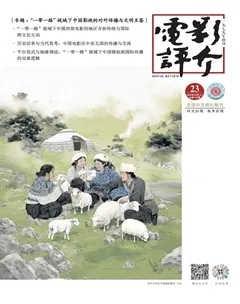“一帶一路”視域下中國西部電影的地區 合拍傳統與國際跨文化互動
【摘 要】 本文以比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對中國西部電影不同時期的合作拍攝模式進行梳理分析,旨在探討中國西部電影的地區合作傳統與國際化發展范式。中國西部電影的合拍模式從地區間電影分工的合作,走向國際間創作觀念的融合,是其創作路徑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一步完善。在延續優勢互補的地區合拍傳統基礎上,中國西部電影以共通互融的影像創作探尋國際間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深入挖掘中外合拍電影的共同體創作思維,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注入新活力。
【關鍵詞】 “一帶一路”; 中國西部電影; 武俠題材; 共同體美學
2024年正值中國西部電影誕生40周年,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語境下,對中國西部電影的地區合拍傳統與國際合作互動進行梳理分析,無疑會對當下中國西部電影的國際化傳播發展路徑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與啟發,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互動帶來更多可能。
一、中國西部電影的地區合拍傳統
中國西部有廣袤壯闊的自然景觀與底蘊雄厚的文化資源,在為中國西部電影提供創作靈感的同時,也吸引著北上的中國香港影人來到西部地區,開啟與中國西部電影的合作交流。在地區間長期創作互動中形成優勢互補的電影合拍傳統,實現中國香港影人對西部文化的民族身份探尋與別樣美學表達。
(一)港人北上的文化尋根
中國西部電影泛指1984年后,以中國西部自然地域空間為基本敘事表征、反映西部地區人民生活狀況和生存狀態、具有強烈的西部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內涵,同時以現代性的電影語言為其聲像載體,具有濃郁的民族氣息和強烈的西部地域文化為其特色的電影流派。[1]在中國西部電影自身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存在與中國其他地區電影進行合作互動的傳統,特別是中國香港電影人北上所帶來的電影創作經驗,為中國西部電影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建置的歷史可追溯到秦朝。秦始皇平南越后,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香港地區隸屬南海郡番禺縣。[2]鴉片戰爭后,中國香港在列強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下淪為日本與英國的殖民地。直至1997年香港才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但長期的被殖民歷史使得當時的香港居民對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出現迷茫與焦慮。中國西部電影與中國香港電影的地區間互動,正是源于香港影人對于民族身份認同的北上追尋以及對于影像空間探索的藝術追求。1992年以后,李惠民、徐克、王家衛和劉鎮偉等香港導演紛紛將電影的創作視角聚焦在廣袤原始自然環境的中國西部地區,開啟中國西部與中國香港的電影文化互動,相繼拍攝出《新龍門客棧》(李惠民,1992)、《東邪西毒》(王家衛,1994)、《刀》(徐克,1995)、《大話西游》(劉鎮偉,1995)、《七劍》(徐克,2005)、《神話》(唐季禮,2005)、《龍門飛甲》(徐克,2011)、《西游降魔篇》(周星馳,2013)、《西游伏妖篇》(徐克,2017)等電影作品。
德國電影理論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認為,“與其說電影反映顯見的信條,不如說它反映的是心理習性——那些多少會向意識維度延伸的處于集體心理深層次的東西”[3]。綜觀中國香港電影人北上合作拍攝的中國西部題材電影,從《新龍門客棧》《東邪西毒》到《神話》無不透露出近似性的深層集體心理。由李惠民導演、徐克監制,瀟湘電影制片廠參與合拍的電影《新龍門客棧》,其故事背景發生在西部大漠的荒涼客棧內,不同勢力為搶奪“忠良之后”而進駐龍門客棧。客棧老板金鑲玉不斷游走在東廠宦官、千戶駐軍與忠良俠客三股勢力之間,其身份的角色定位有著復雜的不確定性。在東廠宦官的金錢誘惑下,金鑲玉可以毫不猶豫地出賣忠良俠客。但在忠良俠客的情義感染下與其并肩作戰,共同對東廠宦官進行絕地反擊。從社會心理學的維度解讀《新龍門客棧》,可以發現電影中亂世孤島式的龍門客棧與動蕩年代下中國香港所處的時代環境相類似。游走在多方勢力之間缺乏身份認同的客棧老板金鑲玉,則更多映射出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市民對于身份認同的困惑迷茫與渴求找尋的深層集體心理。
電影《新龍門客棧》中導演流露出的社會心理投射并非個案,無論是《東邪西毒》中燒掉自己的沙漠酒館、不再因愛恨情仇而自我放逐的歐陽鋒,還是《大話西游》里逃避自己孫悟空身份的至尊寶對重新踏上取經之路的選擇。北上來到西部地區的中國香港導演群體,在20世紀末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面對著原始粗獷的西部環境,往往在其合拍電影作品中投射出對民族身份認同的迷茫與尋找,以渴望民族身份認同的深層次集體心理,實現北上香港影人文化尋根式的社會心理探索。
(二)電影創作的優勢互補
中國西部雖然在整體經濟發展態勢上不如中國東部地區富庶,但其自然環境資源與歷史文化內涵卻有著別樣的韻致。中國大部分高原、雪山、戈壁、沙漠都在西部,為中國西部電影的影像表達賦予粗獷壯闊的文化底蘊。這種多元化的自然文化資源在助力本地電影人展現獨特地域影像風格的同時,也吸引著一批中國香港影人北上,來到更加廣闊的西部尋找創作靈感。西部空間廣袤原始的自然氛圍為香港影人提供電影創作的文化環境,同時港人北上所帶來的電影攝制經驗推動中國西部電影的商業類型化發展,形成西部地區與香港地區之間優勢互補的電影合作創作傳統。
在香港導演徐克的創作生涯中,武俠題材一直是其鐘情的創作類型。從處女作電影《蝶變》(1979)推動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開始,陸續拍攝《蜀山:新蜀山劍俠》(1983)、《笑傲江湖》(1990)與《黃飛鴻》(1991)等武俠題材電影。徐克的武俠電影從不缺少快意恩仇的俠客故事與酣暢淋漓的武打設計,其所需要的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承載俠肝義膽、快意恩仇的“舞臺”。1992年,徐克開始北上與中國西部電影合拍互動,相繼創作出《新龍門客棧》《刀》《七劍》與《龍門飛甲》等武俠電影。
中國西部廣袤雄壯的環境空間氛圍,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徐克武俠電影中的俠義氣質表達與視覺畫面張力。電影《七劍》主要講述禁武令時期天山劍客為保護武莊百姓而下山,與風火連城等邪惡勢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徐克在該影片中的俠義精神表達不再是江湖武林的快意恩仇,而是上升到為國為民的俠之大義。電影《七劍》的俠義故事則在新疆北部的高原雪山、荒漠戈壁與雅丹風蝕地貌等環境中展開,粗糲壯闊的西部空間為楚昭南和楊云驄等七位劍客與風火連城等人的對決營造出大氣雄渾的環境氛圍。當七位劍客首戰告捷,策馬揚鞭在黃沙飛揚的荒漠戈壁之時,七位劍客騎在馬上的大全景畫面在太陽東升的自然光線渲染下形成畫面剪影,為國為民的俠之大義形象躍然于充滿意境的畫面之上。
北上的香港電影人群體借由中國西部的廣袤自然環境探尋影像畫面突破的同時,也帶來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推動中國西部電影的商業類型化發展。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中國香港地區,其經濟發展速度一直處于亞洲前列,帶動傳媒、影視與娛樂等行業的快速發展。香港電影人向來重視電影作為文化產品的商業價值,也由此探索出香港電影類型化的電影制作經驗。所謂類型指的是“由熟悉的、基本上是單一面向的角色在一個熟悉的背景中表演著可以預見的故事模式”。[4]香港電影在長期類型化電影攝制模式中積累出對動作片與喜劇片的電影創作經驗,在香港影人北上合作拍片的時代契機下與中國西部電影形成交流互動,拍攝出《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大話西游之仙履奇緣》《西游降魔篇》和《西游伏妖篇》等充滿動作元素與娛樂精神的類型化合拍電影。
電影《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和《大話西游之仙履奇緣》是1995年劉鎮偉導演、周星馳主演,由西安電影制片廠合作拍攝的《大話西游》系列電影。周星馳彩星電影公司與西安電影制片廠在導演、制片、攝影和剪輯等方面展開全流程合作攝制,開啟了中國西部電影與中國香港電影的深度化合拍互動。該系列電影延續周星馳電影的無厘頭喜劇風格,以戲謔荒誕的喜劇橋段解構傳統文化,顛覆觀眾對傳統人物形象的普遍認知,具有一定的后現代主義意味。
從《賭圣》(元奎,1990)、《武狀元蘇乞兒》(陳嘉上,1992)到《唐伯虎點秋香》(李力持,1993),周星馳主演的無厘頭系列電影具有較為明顯的商業化類型片創作傾向,通過搞笑元素、動作元素與類型化故事模式的配合創作出一部部經典喜劇電影佳作。周星馳無厘頭喜劇電影的故事敘述模式通常為困頓不堪的小人物被挑釁欺侮,經歷自身艱辛努力最終出人頭地的故事。《大話西游》也沿用此類敘事模式,山賊出身的至尊寶逃避自己孫悟空轉世的身份,在經歷與白晶晶和紫霞的愛恨情仇后,選擇接受責任放棄所愛重新踏上取經之路。導演在類型化敘事模式下融入無厘頭風格的喜劇橋段與個人命運的現實反思,解構西游記小說中大眾對于孫悟空、唐僧與豬八戒等角色的文化認知,以荒誕搞笑的無厘頭喜劇表演展現一些人物悲情式的命運抉擇,為中國西部電影的發展注入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內涵與商業類型化電影的創作思路。
(三)西部文化的別樣表達
自香港影人北上拍攝電影開始,中國西部電影與中國香港電影的合拍互動經歷從提供場地和人員,到地區間電影攝制部門的深入交流合作,相繼創作出諸如《新龍門客棧》《東邪西毒》《大話西游》《七劍》和《神話》等經典佳作。但不同的文化生活環境導致中國香港導演對西部景觀與西部文化的呈現,相較于西部本土導演而言存在一定差異,構成北上香港影人別樣的西部文化表達。
“主位方法”與“客位方法”是文化闡述的兩種不同視角,參照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地方性知識》中對主位與客位概念的論述,主位方法指以局內人的視角,從文化內部來觀察和分析文化;客位方法指以局外人的視角,側重從外部來觀察和分析文化。它代表著一種用外來的觀念來認知、剖析異己的文化。[5]對比相近時期相似類型的作品,《雙旗鎮刀客》(何平,1991)、《東歸英雄傳》(塞夫,1993)與《新龍門客棧》《東邪西毒》呈現出不同視角的西部文化闡述。其中《雙旗鎮刀客》與《東歸英雄傳》是西部本土導演拍攝的作品,借由西部角色在西部原始荒蠻土地上的掙扎與抗爭,以文化主位的視角表達對西部文化的眷戀與反思。《雙旗鎮刀客》中主人公孩哥所面對的危險不只是飛沙走石的自然環境與實力懸殊的無情反派,更是復雜人性交織下的險惡江湖。導演何平通過孩哥在原始西部環境下的抗爭與成長,實現對西部精神的表達與民族文化的思考。
香港作為中國的沿海地區,其自然景觀的多樣性不足與中國西部比較。當香港影人北上面對充滿荒漠戈壁、崇山峻嶺與歷史古跡的中國西部地區,在影像呈現上更多以文化客位視角實現對西部文化的駐足與探尋。西部的大漠景觀在《新龍門客棧》與《東邪西毒》中對于角色是神秘且危險的,不明身份的江湖人士在大漠中相識與爭斗,在一切問題解決后離開沙漠。如《東邪西毒》中大漠酒館的景觀對于主人公歐陽鋒而言,既是他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生存場所,也是他逃避過往愛恨情仇的心靈之地。導演王家衛在《東邪西毒》中對西部沙漠環境的呈現更多凸出其逃避世俗情欲的虛無與孤寂,為角色塑造自我逃避的精神流浪之所。
在北上香港影人的西部文化作品中,人物與環境之間不再是沖突對抗的關系。而是以一種流浪者的客位視角,展現香港影人對西部文化的探索與獵奇。這也使得西部景觀在香港影人參與的合拍電影中更具港式寫意美感。北上的香港影人在與中國西部電影的合作互動中,以客位視角探尋西部文化別樣的情感表達與美感呈現,為中國西部電影帶來多元化的創作視角與文化面貌。
二、中國西部電影的國際跨文化互動
電影作為一種訴諸觀眾視覺與聽覺的直觀影像,在國際跨文化傳播交流與文明互鑒中具有直觀化通俗性的表意優勢。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發展背景下,中國西部電影充分吸收地區間電影合拍的創作經驗,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展開跨文化交流的國際互動,通過有著共通性敘事主題與包容性文化視角的西部影像,探索中外合拍電影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的跨文化創作追求。
(一)中外合拍電影的西部呈現
“一帶一路”是基于“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共建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相互合作的倡議。“一帶一路”作為新時代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公共服務產品和“中國方案”,不僅是共建國家政治經濟往來的商貿通道,更是各國家間交流互動的文化橋梁。中國西部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起始點(西北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段(西南地區),在當下“一帶一路”倡議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與使命。“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西部電影的發展帶來新的時代機遇,推動中國西部電影中外合拍創作模式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不斷提升中國西部電影在文明互鑒與跨文化傳播中的突出作用和藝術地位。
自中國香港地區電影人北上以來,中國西部電影吸收了豐富的電影合作拍攝經驗,形成中國西部電影優秀的地區合拍傳統。2013年,中國西部電影開始嘗試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建立起電影合作的國際跨文化交流。以中國與外國合作拍攝的創作方式,展現發生在中國西部地區的中外文化互動,創作出《夜鶯》(費利普·彌勒,2013)、《天將雄師》(李仁港,2015)、《狼圖騰》(讓·雅克·阿諾,2015)、《大唐玄奘》(霍建起,2016)和《長安·長安》(張忠,2024)等優秀的中外合拍電影。
不同于經濟成因推動的香港影人區域電影合拍模式,“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外合拍電影的創作路徑,更多要考量國際間多元化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需要以包容性的文化視角探尋共通的情感價值表達。中國西部地區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有著聯系緊密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淵源,為西部地區的中外電影合作提供堅實的創作基礎。通過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探尋當代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電影文化互動中的共同語言與情緒共振,以展現西部地區的中外合拍電影助力于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國際跨文化交流。
從中法合拍的《夜鶯》與《狼圖騰》、中印合拍的《大唐玄奘》到近年來中伊合作的《長安·長安》,中國西部電影在延續現實主義創作路線的同時,積極探索以電影為載體的國際文化互動。以求同存異、兼容并包的電影創作視角挖掘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絲綢之路故事,探尋源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歸屬與情感共鳴,為中國西部電影的國際化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求同存異:共通性的敘事主題
不同國家間的地域差異,孕育出各個民族不同的文化心理。“一帶一路”倡議所包含的國家橫跨亞歐非等多個大洲,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心理具有一定的差異性。然而,從文化人類學的維度來看,各個國家的文化既存在差異,也具備一定的共通性。人類學進化論派代表人物愛德華·泰勒、安德魯·蘭和詹姆斯·弗雷澤等學者一致認為“正如人類生理機制普遍一致,全人類的心理本質也是共同的”[6]。生存、死亡、親情、友情與愛情等都是人類普遍關注的人生主題,能夠在國家間的跨文化交流中激發不同民族人民的話題關注與情感共鳴。
“一帶一路”視域下中國西部電影的國際化轉型與延伸,需要以求同存異的文化交流姿態,處理中外電影合作拍攝時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尋求電影表達的文化共通性。回望中國與法國、意大利、印度以及伊朗等國家在中國西部地區所合作拍攝的電影主題表達,《夜鶯》《狼圖騰》《大唐玄奘》和《長安·長安》等影片具有共通性的敘事主題。分別從親情、生存、信念和愛情等維度探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振,以求同存異的共通性電影敘事主題,為各個國家間的國際交流合作搭建起文化互動的橋梁。
電影《狼圖騰》是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在中國西部地區拍攝的中法合拍電影,主要講述來到內蒙古草原插隊的知識青年陳陣,在與牧民相處的生活中逐漸接觸狼群,歷經人類與狼群的諸多斗爭糾葛后,油然而生對生命與自然敬畏之情的故事。導演讓·雅克·阿諾借由發生在中國西部草原的電影故事,表達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共通性的生存反思。通過人在殘酷自然生存法則下對生命的敬畏之情喚起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觀眾之間的情感觸動,為中國西部電影的國際間文化交流找尋到求同存異的文化互動母題。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藝術,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打破文化隔閡、促進區域互動的重要作用。中外合作拍攝的電影攝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電影的跨文化交流屬性,通過對共通性的電影敘事主題挖掘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共同的文化認知與情感狀態,以求同存異的文化互動范式,探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電影交流的跨文化互動和文明互鑒,成為新時代中國新西部電影的重要藝術拓展路徑。
(三)兼容并蓄:包容性的文化視角
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延續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在構建當代絲綢之路經濟帶政治互信、經濟共融合作模式的同時,也勾連起絲綢之路共建國家間文化的互動與交流。以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的文化共生范式,應對文化帝國主義單方向價值輸出的文化話語霸權。“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合拍電影承擔著推動絲綢之路共建國家間文化交流的使命,以影像為載體探尋不同國家間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文化互動關系。
電影理論學家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上對電影符號進行分析,認為“電影是一種沒有語言系統的語言”[7]。電影影像作為直觀性的視聽符號,在表達面的“能指”與內容面的“所指”之間存在肖似關系。這就使得視聽符號的語言結構相比于文字符號的語言結構而言更具有直觀通俗性,從而更利于使用影像進行國際間的跨文化交流與互動。視聽符號雖然在“能指”與“所指”的一級符號系統中存在肖似性的短路關系,但在“外延”與“內涵”所構成的二級符號系統中恢復其語言結構的符號屬性。麥茨認為“只有在內涵的能指同時利用了外延的能指和外延的所指時,內涵的所指才能確立”[8]。也就是說外延的能指與外延的所指共同構成內涵的能指,在電影中指代畫面與聲音本身存在的意義。內涵的所指則為潛藏在電影畫面與聲音之下的深層含義,內涵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共同構成電影符號。回觀中國與印度合作拍攝的電影《大唐玄奘》,導演霍建起在玄奘形象的文化符號塑造中以包容性的文化視角,呈現中印之間的文化互動。佛教文化雖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國經歷長期本土化演變后逐漸形成注重慈悲平等的禪宗佛教文化,與以四諦和八正道為核心強調禪修與解脫的印度佛教文化有所區別。玄奘形象在影片中便是中國本土佛教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交流互動、文明互鑒的較為真實化、形象化符號載體。
從影片的歷時性結構來看,初出長安的玄奘法師代表的是中國本土佛教文化。到達天竺后玄奘法師的佛學理念、僧衣服飾與所處的寺廟建筑環境漸漸發生變化,被融入了更多印度佛教的元素。導演霍建起在講述玄奘西行的電影中,并沒有一味地彰顯中國佛教文化的區域影響力,而是以兼容并包的文化視角來呈現中國與印度之間佛教文化的互動交流。既有玄奘法師一路西行時對于本土佛教文化的踐行與弘揚,也有到達天竺后對于印度佛教文化中佛學理念的討論與文化環境的展現,以包容性的多元文化視角呈現不同國家間佛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
從影片的共時性結構來看,玄奘法師以平等慈悲為懷拯救眾生的行為貫穿整部電影,無論是在西行路上為街邊被處決的罪犯蓋上白布替其超度、放過對自己心生殺意的隨行徒弟,還是天竺游歷時給犯人讓路、拯救被詛咒的奴隸夫妻,玄奘法師在到達天竺接觸學習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時,也用實際行動在印度土地上踐行中國禪宗佛教文化的平等慈悲,將中國佛教文化帶向印度。
電影中玄奘法師在不斷接納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時,堅持踐行中國佛教文化中平等慈悲的觀念,由此構成的影像呈現成為電影中玄奘形象的外延能指,以玄奘的符號形象確立中國與印度佛教文化交流互動的外延所指。外延能指與外延所指相互結合構成內涵能指,確立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之間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發展的內涵所指。通過多元性文化視角與表意性影像符號,喚起古代絲綢之路周邊國家的歷史文化記憶,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文化交流互動。
三、中國西部電影的共同體美學探索
共同體美學是中國電影理論界對中國電影現代化發展進程整體性的回顧與展望,也是對中華民族“和”文化在電影領域的繼承與延續。在“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西部電影堅守現實主義的創作導向,通過中外合拍創作中質樸感人的現實題材電影故事與共通共融的影像美學風格,挖掘電影與不同國家觀眾間的情感共鳴與審美共性,實現對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創作探索。
(一)共同體美學的文化溯源
“共同體”概念最初由社會學家滕尼斯(T?nnies)提出,用來形容以血緣、感情和倫理為紐帶的共同生活方式。中國電影維度的“共同體美學”探討于2018年由《當代電影》雜志發起,通過對電影語言以及中國電影理論現代化與再現代化的討論,“共同體美學”的電影觀念被逐漸傳播和接受。整體而言,共同體美學是基于傳統電影實踐與電影技術發展之上,圍繞電影本體、電影現代性以及電影與觀眾關系等方面對中國電影美學觀念進行的審視與反思。
從文化溯源的維度來看,中國電影學者群體對于共同體美學的提出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文化的延續與傳承。中華“和”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貫通古今。從儒家學派提倡的“禮之用,和為貴”以及“君子和而不同”、道家學派提出“天人合一”的觀念,到現當代學者對于“和合”文化理論的提出,以及國家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倡。“和”文化貫穿于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與當下,并隨著時代演進被賦予更多的內涵。
“一帶一路”倡議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中華民族以“和”文化為核心的交流互動傳統,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建立起“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和平發展的平等合作理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政治互信、經濟融合與文化包容的共同體關系。電影作為各個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載體,以中外合拍的電影攝制模式進行跨文化交流可以進一步拓寬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文化互動屬性,從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文化互動與交流。
中國西部電影作為建構“中國電影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延續現實主義電影創作導向的同時,通過共通性的敘事主題與多元性的文化視角,探索“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外合拍電影的創作路徑,展現現實主義電影故事迸發出的情感共鳴與電影合拍模式下藝術風格的互融互通,以求同存異、兼容并包的電影文化創作視角,為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現實題材的情感共鳴
早在1956年,中國電影理論開始探討電影與觀眾之間關系。電影理論家鐘惦棐先生在《電影的鑼鼓》中認為“電影——這一群眾性最強的藝術……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觀眾的聯系,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9]。這與2018年中國電影理論學者群體對“共同體美學”的探討中重視電影與觀眾的關系,提倡電影與觀眾共情的論斷遙相呼應。
中國西部電影自誕生以來便一直秉持著現實主義的電影創作導向。從早期的《人生》(吳天明,1984)、《黃土地》(陳凱歌,1984)與《野山》(顏學恕,1986)等影片中對人與環境的現實反思,到《秋菊打官司》(張藝謀,1992)、《二嫫》(周曉文,1994)與《美麗的大腳》(楊亞洲,2002)中對于女性形象的現代呈現,再到近年來創作的《塬上》(喬梁,2017)對于生態環境的現實主義書寫,以及《撥浪鼓咚咚響》(白志強,2020)中對于未成年兒童生活狀態的客觀展現。中國西部電影真切地關心現實生活,關注人物在現實環境中的生存方式與觀念變遷,在延續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同時,不斷豐富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主題呈現與內涵表達。
相比于科幻神幻的電影題材而言,現實題材電影更加關注當下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生活狀態與情緒感受。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可以使得觀眾在觀看此類電影時能夠感同身受,獲得源自自身現實生活體驗的真實觸動與情感共振。對現實題材電影的創作堅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中國電影的“共同體美學”建設,在敘事維度拉近電影故事與觀眾的情感距離,以扎根于現實的電影故事喚起觀眾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
由張忠導演、納基斯·阿貝耶監制的中伊合拍電影《長安·長安》在中國西部電影誕生40周年的契機下,于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正式首映。電影從一趟國際旅游專列“長安號”開始講起,以回憶與現實的時空閃回來展現女留學生阿雅娜的跨國戀情與秦腔夢想,實現傳統民俗與現代城市、東方文化與中亞文化的巧妙結合。將“愛情”和“夢想”的共通性敘事主題融入女留學生乘坐跨國列車找尋自我救贖的現實題材電影故事中,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電影創作的多樣性文化呈現與共通性情感表達進行藝術探索。
“一帶一路”視域下中國西部電影的中外合拍嘗試,延續中國西部電影自《人生》以來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電影創作傳統,通過共通性的敘事主題關注現實生活,以中外合拍現實題材電影的創作模式喚起絲綢之路共建國家觀眾的情感共鳴,為中國電影的“共同體美學”發展探索更多的創作路徑。
(三)藝術風格的互通互融
敘事和表意是電影傳達信息的兩種系統路徑,敘事結構與技巧模式在一部電影中相互勾連互動,共同構成電影整體的藝術形式風格。電影理論家大衛·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認為“風格是組織電影技巧的形式系統,任何一部影片在創造風格方面都要依賴于特定的技巧,這些技巧由電影制作者在歷史環境的限制里進行選擇”[10]。不同國家的電影創作者對于影像美學有著不同的藝術追求,“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合拍電影面對多元化的電影受眾群體,需要在藝術風格的呈現上適當調整,滿足不同國家觀眾間多樣的審美趣味,以互融互通的合拍電影形式風格,探尋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藝術表達與美學價值。
電影《夜鶯》是由法國導演費利普·彌勒執導,在中國西南地區拍攝的中法合拍電影。電影主要講述老人志根為兌現與過世妻子的承諾,帶上無人照顧的孫女任幸和準備在妻子墳前放生的夜鶯踏上回鄉之旅的故事。影片敘事結構與導演本人的代表作品《蝴蝶》(費利普·彌勒,2002)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在講述有著隔閡的老人和小孩在經歷自然之旅后相互和解的故事內核,這是費利普·彌勒所擅長講述的法式溫情故事結構。但在《夜鶯》的敘事形式系統中,導演在法式溫情故事的結構框架下融入中國家庭倫理元素,踏上自然之旅的爺孫不再是向外探險,而是一場回到廣西老家的尋根之旅。原本有著隔閡的爺爺、兒子和孫女三代人也正是在這場尋根旅途中相互和解,廣西老家對于爺爺志根而言既是承載著鄉愁的眷戀之地,也是三代人相互和解的親情回歸之所。
《夜鶯》的電影技巧形式系統也延續費利普·彌勒在《蝴蝶》中的法式浪漫影像風格。導演在《蝴蝶》中通過大縱深的自然暖光遠景畫面與明快小提琴配樂的結合,來呈現老人與小孩踏上自然之旅的浪漫溫情故事。電影《夜鶯》作為中法合作拍攝的電影,在電影技巧模式的呈現中將導演費利普·彌勒所擅長的浪漫溫情影像風格,與中國西南地區特有的山水景觀以及少數民族文化相融合。同樣是有著大縱深的自然暖光遠景畫面,展現的卻是志根與任幸爺孫二人游走在桂林山水、龍脊梯田與深山竹林之間,共同經歷侗族古寨的風土人情。電影配樂則采用更具中國特色的二胡、古琴與笛子等傳統樂器。導演以中西結合的創作視角,在其所擅長的浪漫現實主義影像風格中融入中國自然景觀、少數民族風情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元素,在電影的敘事形式系統與技巧形式系統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中西文化間互通互融的秀美溫情風格效果,以兼容并包的電影藝術風格呈現,實現對中國與法國電影觀眾群體間審美趣味的兼顧。
綜觀中國與法國、意大利、印度以及伊朗等國家的電影合作拍攝,來自不同國家的導演雖有著不同的影像風格追求,但在合拍電影的創作模式下對中國西部地區的影像書寫呈現出中外結合、共生共融的影像美學創作姿態。中國西部電影在國際跨文化交流中對審美共性的藝術探尋,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文化交流屬性,以多元包容的影像美學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文化互動與藝術交流。
結語
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電影的文化交流作用日益凸顯。中國西部電影的合拍模式有著與香港影人合作的地區合拍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演化出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互動的中外合拍模式。這使得中國西部電影的合作拍攝創作路徑從地區間電影分工的交流互動,走向國際間電影觀念的創作融合與跨文化傳播。
一方面,中國西部電影在與中國香港影人的地區合拍交流中形成優勢互補的創作傳統,北上的香港影人通過中國西部地區多樣性的自然文化資源找尋民族身份認同與藝術創作突破的同時,也為中國西部電影帶來商業化類型化的電影創作經驗,形成香港影人對于西部文化別樣性的客位表達;另一方面,中國西部電影在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國際文化互動中,通過共通性的敘事主題講述質樸感人的現實題材電影故事,以包容性的文化視角探索不同國家間觀眾的文化記憶與審美共性,形成互融互通的影像美學藝術風格。以求同存異、兼容并包的電影創作觀念,為中國電影“共同體美學”的發展建設注入新的活力。
從地區間的創作互動到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是中國西部電影的合作拍攝模式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一步創作嘗試。創作者應深入挖掘中外合拍電影文化共同體的創作思維,通過共通互融的敘事策略與美學風格探尋國際間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拓寬其在合作路徑、文化視角與影像語言等維度的文化交流屬性。以電影為橋梁連通國際人文互動,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
參考文獻:
[1]張阿利.中國西部電影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55.
[2]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訂版)[M].北京:中華書局,2006:181.
[3][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國電影心理史[M].黎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
[4][美]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型電影[M].馮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
[5][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M].王海龍,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17.
[6]鄭凡.震撼心靈的古旋律:西方神話學引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3.
[7][法]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的意義[M].劉森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58.
[8]彭吉象.影視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75.
[9]鐘惦棐.電影的鑼鼓[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53.
[10][美]大衛·波德維爾,克莉絲汀·湯普森.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第5版)[M].彭吉象,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