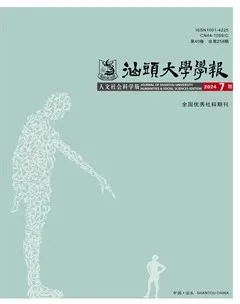薛道衡《昔昔鹽》的再闡釋
摘 要:“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昔昔鹽》詩中名句。歷代詩評家主觀化經驗化的點評對名句生存的整體篇章鮮有關注。“意義回譯”缺少了生命生活的直觀空間,淡漠了自然景物的自然性與“人”的痕跡——思婦隨景物變化自然細膩的情感轉換,使得今人但知美之為美卻不知美之何以為美。《昔昔鹽》整體的藝術風致、情感思理也不應被忽視。詩話、史書多記載隋煬帝妒殺薛道衡,名句經典化歷程烙上了深深的煬帝印跡。是以作家創作時調動的思辨、美感深度、修辭的想象力、意象的表現力、語言使用的新鮮性被遮蔽;“以破敗的環境描寫刻畫思婦的凄涼心境”的當代闡釋具有學理性即具體深入的分析,然人云亦云中“落”字作為“開始”的意義失落,其背后昂揚的精神也隨之失落。再闡釋《昔昔鹽》全詩及“空梁落燕泥”,將細讀文本并借鑒美學批評以揭示:詩篇以巧設轉折的技法建構了基于人普遍的情感與認知的主觀時空結構;名句將生命的本質力量注入具體意象,形成了富有生命氣息的“人化”自然并達成了不同歷史情境下對自我處境的積極昂揚的關照與認識,因而得以成為千古名句。
關鍵詞:“空梁落燕泥”;薛道衡詩歌;《昔昔鹽》
中圖分類號:I2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225(2024)07-0032-10
收稿日期:2024-01-30
作者簡介:韓健豪,男,江蘇徐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文學闡釋學碩士研究生。
李 丹,女,四川夾江人,文學博士,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空梁落燕泥”的經典化歷程在中國古詩詞的闡釋史上非常典型,與野史傳聞密切相關,以傳奇性收獲了關注度。唐代劉餗筆記小說集《隋唐嘉話》: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見妒于隋煬帝,是有關《昔昔鹽》最早的記載。宋代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司馬光《資治通鑒》、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等重要的詩話與史書收錄了這條傳聞。可見,薛道衡作詩見罪煬帝的公案推動了后世對“空梁落燕泥”的關注。唐代趙嘏、清代乾隆更以薛道衡《昔昔鹽》每一分句為題,擬作五律組詩“昔昔鹽”二十首。野史生動、鮮活的敘述籠罩著詩句的接受進程,遮蔽了其“理念”的美。黑格爾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其義:文學藝術的美感是“理念”,形式是形象,“理念”蘊含在形象之中并借之展現出來。[1]文學藝術借形象展現“理念”的過程是具體、直觀、感性的,而被展現的“理念”是概念與客觀存在的統一,并非抽象、空洞的代表主觀意志的情感,更偏重文藝作品引人思索考辨從而產生的理性愉悅。情感是主體統一在有機生物上的表現,與情感表現一起顯現出“靈魂”。情感是“靈魂”的表現形式。情感與“靈魂”的統一才能構成文學藝術的顯現內容——“理念”。李澤厚先生提出“美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這一觀點的大意也被黑格爾、馬克思論述過,因此本文將使用這一美學觀點對詩歌形象進行深入闡發。
之前有關薛道衡《昔昔鹽》的闡釋基本停留在藝術風格、意象美感、音韻格律等外在形象層面。對《昔昔鹽》全詩及“空梁落燕泥”的再闡釋必須立足文本再出發,對遮蔽于詮釋史中的詩歌的形象、情感與理致進行發覆,從而管窺詩人在訓致繹詞、揮墨運斤的創作中觸及的靈魂深度。
二、前人對《昔昔鹽》的闡釋
古代文人較少提及《昔昔鹽》全篇。范晞文在《對床夜語》中感嘆“空梁落燕泥”過于有名、時人不知其出處,引述了《昔昔鹽》全文;胡應麟在《詩藪》中評論《昔昔鹽》“大都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除此之外,沒有關于《昔昔鹽》全篇或其中詩句的評述。可見,古代文人僅發現了《昔昔鹽》篇章的韻律和諧、對仗工致之美。
古代文人十分重視“空梁落燕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余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于后世,膾炙于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胡仔激賞“空梁落燕泥”并認為僅此一句足令薛道衡留名后世。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永叔詩話稱謝伯初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昆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峻潔”是對形象美感的主觀概括,主要指詩句的文辭簡練、風致清新、氣象開闊,有一種令人喜悅的情致而非平淡無味的客觀描寫。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物相停然,覺下語韻勝,以得景之佳也。故詩人賦物,取其景之最勝者。二語悠然雅韻,凡實境自成,真情自涌,此是詩家第一義。若點綴推故,雖極精工,終非其至,此謂要道不煩。”陸時雍也認同歐陽修的看法,認為:詩句韻律和諧,富于韻味,形成了十分自然可感的意境。
《詩藪》評《昔昔鹽》:“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匯集于后,俾初學知近體所從來……如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胡應麟激賞“空梁落燕泥”的合律性。古代文人的點評集中于宋明兩代,主要以主觀化、印象式的藝術概括說詩歌某一妙處卻不作詳談。古代文人大多學養深厚、泛覽詩書,有較佳的藝術品味。因此他們的評點往往切中肯綮、頻見真知、清要簡練,如牖中望日。其評點集中在“聲韻”“文辭”“意境”“情感”等印象批評層面,對《昔昔鹽》整體篇章不夠重視,也缺少對名句的具體、客觀的學理分析。
今人學者對《昔昔鹽》的闡釋主要體現為文學史論著中具有一定學理性的籠統評述。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認為:《昔昔鹽》風格頗似梁陳,其閨怨題材常見于《玉臺新詠》,其思婦形象也受前人作品影響。“這種藝術上的渲染、暗示,在南朝作品中也不時可以發現,薛道衡這兩句盡管工巧自然,卻很難說有多大新意。其成為名句,或許正是煬帝的忌恨在客觀上起了宣傳作用。由此,全詩也隨之為人傳誦”。今人學者認識到《昔昔鹽》對前人作品的接受,關注到非文學因素對文學傳播、接受活動的影響。隋煬帝妒殺薛道衡,源出筆記小說《隋唐嘉話》。《隋書》并未記載此事。河東薛氏是清貴顯赫的山東士族。雖然薛道衡之子薛收在《隋書》修撰前去世,薛氏家族仍有薛元敬等子弟出任高級官僚。與薛收并列“秦王府十八學士”的孔穎達參編《隋書》,應能收集到充分、可信的史料。煬帝妒殺薛道衡的傳聞并不可信,卻被重要的詩話及《資治通鑒》收錄。這助推了“空梁落燕泥”在后世的接受。將詩句經典化的原因歸納為“小說家之言”,無疑遮蔽了詩歌文本的美感,也忽視了文學接受活動對審美、情志的重視。
葛曉音評價:《昔昔鹽》在融合南北詩風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風格,尋找新穎的構思方式和藝術形象,突破了當時沿襲舊題舊意的樂府格套,具有華美輕靡的艷情風采。“薛道衡通過細膩的觀察找到了新的更有表現力的角度:暗窗上布滿蛛網,顯示出女子無心灑掃屋塵,甚至無心倚窗守望的慵懶,這就比寫庭中不見履跡更深地揭示出內心的絕望。以燕子春天雙雙飛歸反襯女子虛度青春的孤獨,在齊梁詩中亦屢見不鮮,此處卻從秋天燕子離開,只在空梁上落下幾點窠泥這個小小的細節著眼,將思婦春天見雙燕歸來的怨慕都包容在深秋燕去之后的惆悵里了。”[2]葛曉音以學理性的評述判定名句“以破敗環境的描寫刻畫思婦的凄涼心境”,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人云亦云中,“落”字作為“開始”的意涵及背后的昂揚精神失落了,使人但知為美、卻不知美之何以為美。葛曉音的解讀仍有可商榷之處:一、詩歌的時間,是從春至秋,還是處于春日季節的當下?二、“空梁落燕泥”,是深秋燕去的惆悵,還是乍而生發的富于光、熱的希望?
今人學者雖有了些具體深入的學理分析,但脫離了歷史語境、缺少了切實體驗,在“意義回譯”(指讀者閱讀傳世文本,以當下語境中產生的認識,對作者之意進行闡釋)的過程中,并未真正進入抒情主人公和抒情者生命生活的直觀空間,產生真摯的共情體驗,而是以思婦遭遇見證者的視角,將富有生氣的生活空間當作故事發生的“彩色幕布”,忽略了景物變化上體現的細膩情感痕跡。
三、《昔昔鹽》全詩再闡釋
重新闡釋《昔昔鹽》全詩,將以整體關照、實證的方式探討詩歌敘事的具體時空,借此揭示:《昔昔鹽》采取插敘的敘述方式,從當下回憶過往;在變動的觀察視角、生新的多樣圖景背后,存在一處固定的敘述方位。通過對詩歌的敘述方式、思婦所處方位的分析,能夠發覆詩人隱藏于具體直觀的美感形式下的創作邏輯,并意識到:當思維進入詩歌語言的“迷宮”,將從感性體悟演變為理性思索,給接受者帶來參與還原藝術場境的興奮和愉快。意識活動具有雙重性,包括情感反應和理性認識,在《昔昔鹽》文本中突出表現為情感寓于意識流動——抒發的情感涉及對境遇的思考,因而具備理致、體現出“理念”的特質。
《昔昔鹽》全詩如下[31]:
《昔昔鹽》: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1. “巧設轉折”與時空變換
《昔昔鹽》前兩句寫女子所見的景象。“金堤”,黃土壘成的堤壩,常見于河湖邊,有較大規模,非庭院之景。“垂柳”言柳樹枝葉繁茂,垂落下來。“覆”,柳樹枝葉,能覆蓋堤壩,突出枝葉繁茂。“蘼蕪”、“芙蓉”、“桃李”都是春夏常見的景物。詩歌未言明開花或結果,故不能因“芙蓉”便斷定為“夏天”。“花飛桃李蹊”或可解作“桃李之花,飛于林間”,大致在春末夏初。根據“水溢”二字可知,近期雨水較多,大概是谷雨前后。雨水增多,萬物茁壯生長,故有垂柳掩堤、花飛水溢。觀察事物的角度主要是俯視、遠望。從較高的地方望去,忽視了植株間的參差錯落,看到蘼蕪的整齊。柳樹遮蔽堤壩,故為居高望下所見。“溢”是滿而出的意思,池沼滿滿都是水甚至淹沒了原來的邊際。若駐足岸邊,觀察池水,往往只能從局部的視角注意到漲落、波瀾,無法有如此廣闊的視角。女子觀察景物的視角暗示其位于高處。從此觀之,女子應位于門樓上的窗戶邊。
另外,從文字學的角度更能進一步推斷出:窗戶是朝南方向的。“穿壁以木為交■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為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牖”作為接受陽光照射的通道,應是朝陽一面的窗戶。“‘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皇侃疏‘牖,南窗也’。”[3]從文獻可知,“牖”一般指代朝南的窗戶。古代民居,坐北朝南,宅院大門往往朝南而設,故“牖”是最能受陽光照射的窗戶。《說文》曰‘在墻曰牖,在屋曰囪’。墻,《康熙字典》引述:“《說文》本作墻,垣蔽也。……《爾雅·釋宮》:墻謂之墉。《書·五子之歌》:峻宇雕墻。《詩·墉風》:墻有茨。〔傳〕墻,所以防非常。”墻具有較強的抵御、防護作用,應處于宅院外圍,并非是臥室、閨院等地的房壁、擋板。“墉”“墻”同義,《康熙字典》認為“筑土壘壁曰墉”,同時“《禮.王制》〔注〕:小城曰墉。”“《釋名》: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也。”根據《康熙字典》及引述文獻可判斷:墻、墉是宅院最外面的土壁,較高、厚,起保護庭院的作用。按照《禮記》所言,墻的規模較大,甚至能與小型的城池媲美。這也佐證女子優渥的家世。此等規制的墻壁一般會設置附帶窗戶的門房或門樓,以便于觀察、聯絡外界。“牖”作為朝南的設于外墻的窗戶,充當窺探院外的渠道。結合思婦居于高處,《昔昔鹽》的“牖”位于門樓上朝南一側。
“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按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盤龍”是銅鏡上的裝飾,“隨鏡隱”指鏡子因長久不用而隱藏在匣中;“彩鳳”是錦幔上的花紋,“逐帷低”言帷幔不上鉤而長墜。帷幔不上鉤而低垂,有一種落寞、慵懶的氣息。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多疏于懶散、缺少精氣。這句詩渲染了相思的愁苦。女子因落寞孤獨而放棄裝飾自己、收拾閨閣。“采桑秦氏女”,羅敷采桑,以言辭巧拒使君追求,勤勞、聰慧、堅貞不二;“織錦竇家妻”,蘇蕙織錦、作回文詩,賢德、聰慧、機敏多才。女子以羅敷、蘇蕙自比,不會放任臥室布結蛛網,更不會房門大敞、由燕子多次進出。女子所處的位置應是她不常到的地方。這個地方能激起對丈夫的思念、看到院外的風光,應是自家門樓上的小房間的窗戶旁。
除開頭前兩句外,最能體現時間季節、空間位置的是“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葛曉音認為該幕發生于深秋,燕子在空梁上落下幾點窠泥。這種判斷是有待商榷的。第一、全詩沒有任何跡象能佐證“深秋”的說法。蜘蛛網,一年四季都有。落下“窠泥”也可能是春天、夏天,不一定是秋天,況且深秋一般不會有燕子。第二、“窠泥落于梁木”的行為不具備生活邏輯。“窠”,《說文解字》謂“空也。穴中曰窠,樹上曰巢。從穴,果聲。〔苦禾切〕”“窠泥”是指鳥巢的泥土,非常微小、輕盈。時值秋日,燕子不再筑巢,為何將泥土落在梁木上?“窠泥”落在梁木上面,屋子的窗戶已結蛛網,說明:此屋乏人清掃、積累塵土。女子站在梁木下,如何能看到梁木上面的幾點窠泥?若女子看到了窠泥,則表示窠泥有一定體積,應是燕子多次勞動所形成的,不大可能是“幾點”。這種情況更常見于春日燕子搭建巢穴,而非深秋飛走前。第三、從訓詁學的角度說,“落”除“落下”外更有“落成”的意思。據《康熙字典》“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落”有“宮室始成”之意。綜上所述,“窠泥”落于屋梁多是燕子的筑巢行為。從結果分析,“窠泥”累積的成果是燕巢的筑就。雖然燕巢未必完成,但有了體積、略顯雛形也可借之代稱。“空梁落燕泥”可以解釋為“空蕩的梁木上新落成了一個燕巢”。從藝術性的角度看,“落”不應解釋為“落下”。按照葛曉音所闡釋的內容,“落燕泥”形成了較為肅殺、清冷的氛圍,與“暗牖懸蛛網”形成句意的合掌。
“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匯集于后,俾初學知近體所從來。……如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都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4]薛道衡《昔昔鹽》是永明體影響下的新體樂府詩,為齊梁調。①后人以律詩的成就評價“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故此詩句應全然符合律詩規范為上。律詩對仗的要求是避免出現合掌現象,令上下句保持句意的不同,形成錯落、靈動的應和。上下句都繪寫肅殺、凄冷之景象,意思重復,形象板滯,有損詩歌的美感,為推崇律詩的評論家所不贊賞。因此,“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發生的時間應是春季。可見:兩處帶有時空指向的詩句都發生在同一處地點的春天。
“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前年”與“今歲”對仗,在相近時期的詩歌中常見。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六三前年暮,四五今年朝”,“六三”是十八歲,“四五”是二十歲,故“前年”是今年往前推算兩年的年份。蕭綱《從軍行·其一》“前年出右地,今歲討輪臺”,說的是貳師將軍李廣利第二次征討西域。第二次征討西域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因此“前年”之說同于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前年是今年往前推算兩年的年份,可知女子至少經歷了兩個春天。“采桑秦氏女……倦起憶晨雞”僅是女子日復一日的毫無變化的深閨生活常態,是所處當下內心意識活動主導的回憶陳述,無法定位到具體的時間。如果開頭兩句和“空梁落燕泥”的春天,并非一年之中、一日之內,往往應取相互對照、參見變化的意思。為何一句寫戶外春景,一句寫室內陳設,既沒有對比、變化,句意也重疊冗余?
全詩實際寫的是同一天的一個地方。在實寫明媚春景后,以虛筆宕開,講述自己的遭遇。夫婿離家已有兩三年。長久垂淚、收斂笑容、徹夜難眠,都是自己無論季節更迭的恒常遭遇。從登樓所見的春光世界,到回憶中的幽暗閨房,至當下目睹的蛛網、梁木。實則卻在一日之中。詩歌運用了插敘手法,虛實結合,敘述流轉。從開闊遼遠、愜意慵然的暖日春景,突然邁入狹小幽閉的閨閣,疾快鋪陳悲思、愁怨,感觸于當下的“空梁落燕泥”后,女子的思緒飄飛到塞外、未來,進入更為廣闊的宇宙時空。
2. 意識流動與抒情高潮
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鐘嶸《詩品》“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劉勰《文心雕龍》“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德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西晉至南朝梁代的文論觀念凸顯一種“感物”——心靈受外物形象之感發而生出某種情感,此后情感以文學的形式展現。這是六朝文論中重要的認識,也反映了當時人們認為文學得以生成的心理機制。因而,以“感物”的視角分析《昔昔鹽》的整體篇章會發現全詩有十分自然的意識流動。
前兩句的春日景象是溫馨明媚、愜意安詳的。柳樹覆蓋堤壩、芙蓉池水漫出、雨后蘼蕪葉子繁茂,在春日陽光下,生新可愛,溫暖愜意。林間花飛,原本微小的細節卻被思婦敏銳地捕捉,寫活了思婦的悠閑安適與心情的空靈愉悅。開頭兩句僅是刻畫物象,但畢肖的筆法展露出對良辰好景的喜愛。萬物得時,饒有生機。情感表露于詩歌,造就了輕松愉快的氛圍。短暫的愉悅卻被久積心中的孤寂淹沒。“關山別蕩子……倦起憶晨雞”,幽居空閨令女子悵然自失,眼前浮現孤寂度日的景象。敘述流轉,疾快若奔,詩歌為真摯的情感牽引,縱橫鋪敘,氣力飛騰。
“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迅捷一轉,開啟回憶,渲染具體的情形,如空房獨守、容笑恒斂、玉淚長垂、睡夢飄忽、難眠輾轉。在密集的言說中,時間以強勁的力度迅速剝奪了女子的所有,從笑容、睡眠到精氣甚至容貌。春日暖意洋洋,惠風和暢,天晴月朗,雜花散芳。被相思所困的人只得悵恨于難挨的凄涼。四行詩句以驚人的速度展現了離愁對思婦的步步緊逼,與首句春景形成突兀的反差,將女子置于生活的寒冬、運命的深淵,也興發作者對思婦的憐憫。短短數句一變溫馨氛圍為刺骨的寒涼,一改惠風的和暢作銷魂的肅殺。愈是春日,愈見悲冷,可謂力透紙背。郁積的情感在“空梁落燕泥”處以轉折的形式得以迸發。
“空梁落燕泥”以忽焉一轉令女子的思緒,躍出簾幕重重的閨房,擺脫苦悶、煩郁的牢籠,直面望夫幽居的普遍性境遇,興發貞剛、樂觀的情調,懷著美好的希冀、追問堅守的結局。作為體式上的“轉折”,“空梁落燕泥”令敘述、抒情波瀾起伏,使詩歌結構搖曳多姿,更添生新、蘊藉之感,又增高雅、清麗之態。不同于借意象言情述志的幽微隱約,此詩句抒情較為直率,以顯見的樂觀情致一反層層鋪敘的愁苦。在情感的變換中,抒情性達到了高潮。“空梁落燕泥”后,詩歌迅速收尾,留下“那能惜馬蹄”的輕輕抱怨,不再言說,戛然而止,令讀者繼續遐想。前文鋪敘的煎熬、苦痛被全然消解;所有不好的預想化為對夫婿不體恤行為的嬌嗔。
“宮體詩著力描摹婦女的內心世界,或襲用樂府舊題,或即事自創新調、有描寫思婦月下懷人……語言聲調更趨華美,內心世界展示得更蘊籍豐富。”[5]宮體詩關注幽微情感的生發、轉化,力圖通過形式技巧的形式,使得情感婉轉、曲折流露從而情意連綿、感喟深沉。《昔昔鹽》似不出宮體詩格套。然以巧設轉折的方式加快敘述的速度、增添拗勁,避免了為文造情的造作,不見頹弱、纏綿的氣息,令詩歌氣力充沛、情感真切。
《昔昔鹽》作為解曲,其演唱的節奏、聲律形式也服務于情感的抒發、氛圍的營建。
敘事性的片段在演唱時較容易被聽眾理解。思婦自敘身世,沒有使用晦澀的典故,基本以明白曉暢的語言講述日復一日的遭遇。因此,演唱的節奏得以加快。音樂的開頭往往輕緩。描寫景色的詩句,如果較快帶過,將不利于聽眾聯想、體悟。“暗牖懸蛛網”是插敘回憶后、對現實的回歸,是敘述方式的變化,更是時間、空間的轉折,所以必須略微放緩速度、加以強調。“前年過代北……那能惜馬蹄”,抱怨丈夫、期盼團聚應是一種明快的作結。節奏因意識活動有所區別,而情感在緩急交替中呈現得愈發明晰。
清代徐大椿《樂府傳聲序》:“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曲。”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初盛唐詩人,率先為樂府,然后以樂府為詩。樂府在漢魏雖有曲譜,而至唐代則久已亡佚,故唐人為樂府,不過效法歌詞,并不能依照樂府曲調。”木齋、侯海榮也認為初唐樂府主流是不入樂的。[6]按斯言,薛道衡《昔昔鹽》在唐代大抵不能用曲調《昔昔鹽》演唱。現有材料不能證明:樂府詩《昔昔鹽》在北齊、北周、隋朝時代已經去樂。故本文仍以樂府詩歌的音樂性為評判《昔昔鹽》的標準之一。即使《昔昔鹽》不入樂,詩歌的敘事內容和韻律也可作吟詠的憑據,令其富于音樂美。音樂美將以愉悅聽覺的形式在文本之外,悄然展開意義,令氛圍浸潤情感,使聽眾性情搖曳。
《昔昔鹽》稍有不合律之處,但處處體現對聲韻美的追求。每句詩依照五言律詩的四種句式,總符合格律規范。上下聯則易“失粘”,且遠不符合近體詩的句數要求。《昔昔鹽》中,“水溢芙蓉沼……織錦竇家妻”“飛魂同夜鵲……空梁落燕泥”“暗牖懸蛛網……今歲往遼西”平仄完全合拍,壓齊聲韻,可分離出來,作規范的近體詩。“空梁落燕泥”簡短凝練,但從聲韻角度探析,起承接之妙用,在聲音之外悄悄展開詩義。“空梁落燕泥”所在句與上句、下句都相粘,承轉流暢,可作兩首“近體詩”共同的部分。該句也是兩種不同情感的轉折——由傷感到樂觀、釋然。聲韻的流轉順暢,伴隨著情感的轉接自然。《昔昔鹽》是解曲,起收尾作用,避免樂曲演奏拖沓、冗長。誦讀詩歌時,自“飛魂同夜鵲”始,語速加快、文氣順暢、韻律和諧,如行云流水,至“一去無消息”處,借輕輕的反問戛然作結。入聲字“落”,突然短促,語氣一緊,富有力度,對“燕泥”起強調作用。“落”“北”“一”,在末尾三句,均勻分布,間或短促有力,令文氣充沛、有變化,易于升華情感,同時避免入聲多以致拗硬、阻塞。
“空梁落燕泥”具有鼻音韻母ɑng[ɑ?耷]兩個、ɑn[ɑn]一個;“暗牖懸蛛網”,有一個ɑng[ɑ?耷]、兩個ɑn[ɑn];“前年過代北”有兩個ɑn[ɑn]、一個ɑi[ai]。帶有鼻音韻尾的字錯落分布。細致品讀,鼻音的松弛、慵懶之感,回環往復,方落又起。聲韻上的力度、變化、輕躍,體現出自然、和諧的美感。詩人似乎以獨特的聲音形式提醒讀者反復體味深切而真摯的情蘊。
《昔昔鹽》以“巧設轉折”的形式暗含了時間、空間的變化,并呈現出意識流動,從而真摯抒情。時空變換蘊含了精微的構思、高超的氣力,體現了詩人對精巧結構的追求。這種精巧的敘述結構絕非生澀地炫技,而是以意識流動的形式使詩歌情感抒發更為自然。正是在水到渠成般的自然、融洽中,意識活動悄然展開,抒情性逐漸凸顯,并在“空梁落燕泥”時令詩歌的藝術效果達到高潮。
詩篇有客觀具體的時空標志。能借助對其的考證,追溯作者在構思寫作、創造形象時調動的深刻思辨,體悟作者對客觀景物特征與結構的深切把握——賦予了自然景觀“人化”的屬性。從詩的藝術真實分析,《昔昔鹽》的敘事超越了具體的客觀時間,也不隸屬某個特定的地點。在意識活動的驅使下,詩人和思婦的才能、天賦、欲望以本質力量的形式①改造了外在的客觀世界,令自身的生命底色、情感思考化入到“人化”的自然環境中,形成自然特質與自我風貌的混一,建構了基于人普遍的情感與認知的主觀時空結構——也是思婦存在、生活的場域。
詩中自然意象,“象”外有“意”,超越了自然事物本身,躍升為人自然性情的直接載體,產生了自然性②。自然意象的互動拼接形成具體可感的景象場面。不宜“片葉遮目”、將其視作人物抒情的“彩色幕布”,而應從整體與聯系的視角出發認識到生命生活的直觀空間。從春日美景、閨房擺設到燕巢梁木,處處具有思婦個人的色彩和烙印,就連想象中的邊地也在充當思婦心靈神游的場域。隨景物的變化,思婦情感自然發展、細膩轉換,并在自然意象上留下了“人”的痕跡。“美和藝術的根本特征之所以是形象,就因為美和藝術起源于“理念”要把自己顯現為感性形象的需要。”[7]“理念”是人的自由心理活動,需要借助感性形象得以認識與關照。詩中場景自情感意識被喚醒后,流逝變動,在真摯澄澈的情感作用下,于意識思索的升華過程中成為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生命生活的直觀空間。在直觀空間中,思婦通過對“燕泥”這一“對象化”產物的“體悟”完成自我命運的認知。通過對詩歌整體的發覆,可見作家創作時調動的思辨深度。
四、名句“空梁落燕泥”再闡釋
——兼論其何以成為千古名句
“空梁落燕泥”能夠被經典化且成為千古名句,主要在于:人成功地發現并選擇自然對象,將全部生命的本質力量灌注進去,創造了富有人性光輝、熾熱情感、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形象。“空梁落燕泥”抒發的是積極樂觀、貞剛的情感,并非葛曉音認為的“以破敗的環境描寫刻畫思婦的凄涼心境”。“燕泥”由“燕”與“泥”兩個意象合成,具有高妙的意象表現力,體現了修辭的想象力和語言使用的新鮮感。
不考慮同義詞的情況下,生物屬性的“燕”僅在《詩經》中出現了一次,即《國風·燕燕》。
據《毛詩箋傳》“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燕,鳦也”,《國風·燕燕》未繪寫成雙之燕,而是以燕子(更可能是孤燕)的飛翔比喻親密無間的友人的分離,寄托一種離愁、傷感。燕子承載了友人間的情誼。莊姜、戴媯的情誼和夫妻別離具有相似性。東漢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燕子”在詩歌中首次以象征夫婦之情的形式出現。南朝閨怨詩貫以成對出現的燕子象征忠貞、圓滿、熾熱的愛情,而在變換難測、世事多瑕的現實中常用以抒寫夫妻別離的思念、牽掛。鮑令暉《古意贈今人》“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誰為道辛苦,寄情雙飛燕。”,王樞《古意應蕭信武教》“人生樂自極,良時徒見違。何由及新燕,雙雙還共飛。”,劉孝綽《春宵》“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月帶園樓影,風飄花樹香。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床?”,庾肩吾《詠得有所思》“佳期竟不歸,春物坐芳菲……不及銜泥燕,從來相逐飛。”,蕭綱《金閨思》“游子久不返,妾身當何依。日移孤影動,羞覩燕雙飛”,“燕”既會讓獨守空房的女子不平、“羞惱”,也給她們帶來希望——她們希望燕子能為自己“傳書報信”,欣羨于燕子的幸福因而內心稍得紓解。
“《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郭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詩》云:燕燕于飛。《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涏涏是也。……《詩》云:燕燕于飛者,《邶風》衛莊姜送歸妾之詩也。云一名玄鳥者,案《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其色玄,故謂之玄鳥是也。云齊人呼鳦者,案《商本紀》云:簡狄行浴,玄鳥隋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諸緯■言: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是玄鳥又名■也。”據《說文解字》,“燕”也有“玄鳥”的意思。“燕”在古代早期文化里有生育、繁衍的意義。愛情的象征義后來居上,也自然兼有了生育子嗣的意涵。
“燕泥”意象能夠給詩歌注入樂觀、積極、貞剛之氣,更多依靠“泥”這一意象。《玉臺新詠》所有有關“銜泥”行為的詩句,羅列如下:《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鮑照《詠雙燕》“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泥覓新知。”,《春月二首》“春蠶方曳緒,新燕正銜泥。野雉呼雌雊,庭禽挾子棲。”,劉孝綽《古意》“春樓怨難守,玉階空自傷。對此歸飛燕,銜泥繞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傍雕梁。故居尤可念,故人安可忘。”。從動作的性質分析,“銜泥”是為了筑巢,是一種有強烈主觀意圖的行為。筑巢非一日可就,須得無數次堅持、操勞。風吹雨打、人獸侵擾,燕子面臨“殘酷”的生存境遇,卻從未放棄對安身之所的積極營建。《玉臺新詠》有關“燕泥”的詩歌都將燕子銜泥與“新”聯系起來。不難理解:梁上燕泥指涉的不是深秋的惆悵而是告別過去的嶄新的開始。
“燕泥”作為自然形態的巢穴,是燕子棲息、繁衍之所。“燕泥”的精神屬性來源于人對其結構、特征的深入把握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主體意志的投影,增添了生育、愛欲、忠貞甚至孤傲等人性特征。“泥”源于原始的自然,與人工制作相對,通常給人十分新鮮清新的感受,是對“燕泥”富有想象力的修辭——令雕琢形成的巢穴與原始自然的泥土形成了形象上的深度關聯。因此,“燕泥”意象既能發揮“燕”的意義,又可擺脫束之臺閣的浮麗俗艷,更貼近健康自然人性的審美趨向,洋溢著自由生命的感染力。中國古代傳統的解讀認為自然景觀“燕泥”觸發了思婦的情感,但在這一“感物”機制的背后應該認識到“燕泥”是被注入生命之力的自然性景觀,并非“意義回譯”時脫離歷史語境浮現的單調形象。是以思婦能借助“燕泥”實現對自我處境的新認知。“燕泥”——一個承載積極昂揚精神的意象,在昏暗斗室中散發光熱,與布塵的梁木、黑沉的房頂形成和諧、溫馨的美感,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女子閑散度日,無可聊賴,懷著尚未絕望的心境,飽受愈發深沉的相思折磨。賢德、才思、勤勞、善感……,她的美德似乎并未帶來美好的結局,更令她想起收于木盒中的精美銅鏡,進而困于個人的愁郁。精巧的銅鏡當被欣賞、使用時,才具有本體的價值;不被使用、藏于木匣時,只是一塊等待生銹的金屬。此前,女子經常來到窗邊并從高處眺望,一次次的失落后呆在閨院以逃避一切。尚未絕望的思婦再次臨窗,深覺時間迅速流逝——窗戶長久不開合,已結上蛛網。窗戶為界,窗外是正天好時的暖意春色,窗后是蕭條、冷寂而壓抑的亭閣樓臺,似乎是一熱一冷的兩個世界。
“落”作為動詞,體現了修辭的力度,充盈著文學語言的新鮮性。“落”字有多重的意涵。其表示“開始”的義項是不太常用的,一般見于“新屋落成”“宮室始成”之類的語境。燕巢建成與“宮室始成”“新屋落成”具有相近性。“落”字最常指代“落下”。其冷僻義項在“空梁落燕泥”中的使用既能夠延長人們審美反應的過程,形成陌生化的效果,也產生了文本闡釋的開放性、含混性的特征——不少的文人學者將“落”訓為“落下”,也能描述出一番美感。“落”是入聲字。入聲的特點是短促迅急、有力度。“落燕泥”強調視線對“燕泥”的倏然察覺。“落”的“突然出現”,打破了蛛網的“阻攔”,使春天以不可擋的力量推進至思婦的狹小世界,并以強勁的生命氣力將女子從欲墜深淵的絕望中拽出,以融化一切堅冰的暖熱提醒她春天已經到來,以獨特動詞的強勁力度感給詩歌語言帶來了新鮮氣息,以“燕泥”這一靜態的形象關聯燕子銜泥的動態過程給困頓中的思婦以勉勵。《玉臺新詠》有關“燕泥”的詩歌都將“燕子銜泥”與“新”聯系起來。不難理解:梁上燕泥指涉的不是深秋的惆悵,而是告別過去的嶄新的開始。
女子的思緒從狹窄的閨院天地,飛躍至前年、今年、代北、遼東的時空坐標中,游依動遷,進入一個宏闊的宇宙空間。在此之前,詩歌中尚未展現出女子如此強烈的時空意識。她開始直面這個世界,重新以樂觀的心態抱怨丈夫不愿歸家,想象、期盼著丈夫歸家的那一天。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賦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是作為秉賦和能力、作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為自然的、有形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的情欲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在他之外存在著的。但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這是表現和證實他的本質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對象。”人的本質力量,一是自然力、生命力,這些力量表現為人的稟賦、能力、情欲;一是受限制、受動的自然、有形體、感性、對象性的存在。這些也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是美的載體。思婦的情欲是盼望與從軍的丈夫早日相見、消除離別、過上兒女滿堂的幸福生活。這是兼備物質屬性與精神屬性的盡善盡美的本質力量,屬于復合型的結構。
詩人作為抒情者,通過塑造思婦這一抒情主人公實現自我的傳記表達。思婦(詩人)發現并選擇了“對象化”的最佳載體,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化入自然景觀,令其成為活的形象、顯現出主體自身的特質,并以“燕泥”的“人化”自然達成對自我處境的積極昂揚的關照與認識。詩歌情感主題的表現并非抽象概念的陳述,也絕不是脫離理性節制的宣泄,嚴格遵循著情理合一、以理制情的原則(名句的情感抒發,有深刻的構思)。詩歌呈現出異于同時期宮體詩的生命生活的時空——藝術世界,洋溢鮮活的生命氣息,充斥著人的真實的‘痕跡’,隨處可見立體飽滿、有生命活力的形象。“空梁落燕泥”的“燕泥”作為“人化”自然,除了寄托積極樂觀、貞剛忠誠的情感,還在于以蘊藉的形式展現理性的思考。當作為本質力量的欲望、能力、稟賦被無力掌控的黑暗現實壓抑時,詩人逐漸體歷了低沉、苦悶到抑郁、恍惚甚至不安的心境,也將尋求一種自我安慰和自我實現。于是,“燕泥”這一積極情感的載體以孕育希望的特點成為了理性思索的答案——面對無意義、無希望的人生,唯一該做且能做的是堅持自己的理想、保持向上的人生姿態。
人的本質力量的復合結構在社會歷史的變化中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例如:偏向于自然層面的物質屬性也能指代薛道衡等文人輔政恤民、安邦定國的政治抱負——這種近乎文化本能的欲望受制于黑暗專制的封建制度,而精神層面是歷代儒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道德堅守。在這種情況下,薛道衡將自己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思索化入具有相同結構的思婦游子敘述,遙旨深遠,真摯感人。
薛道衡生于東魏,歷仕北齊、北周、隋代,經逢亂世,深蒙北齊鮮卑皇室猜忌,不得重用;深膺儒學、精研禮制,卻目睹高卑易位、禮樂崩弛;正直忠誠、不善逢迎,也因此受官場排擠、觸煬帝逆鱗①[32]。幽暗冷寂的閨房隱喻詩人所處的動蕩、黑暗的社會,托寫其寓居其間的無奈、冷落,而“燕泥”則是詩人牢牢抓住的希望。即便如女子責問丈夫“路遠不歸”般,希望或許是渺茫、虛幻的,但一絲微光足以支撐他對理想的堅守,便能讓他以樂觀、剛強的態度對待早已銅墻鐵壁般禁錮自己的世界。
思婦思念丈夫、幽居苦悶,也象征在亂世中不得志、感時傷世、前路迷惘的詩人。以思婦為詩人代言,用女性的口吻婉轉陳述,以堅貞守節、樂觀度日隱喻:在安危禍福前,堅守節操、獨善其身、不渝初心,更感人至深、蘊藉悱惻。帝王的冷血猜忌、政治爭斗的黨同伐異、災疾的不時而至、時局的風雨飄搖將薛道衡置于“被安排”的境地。明哲保身、守正持節、樂觀入世或是薛道衡在熱切理想與冰冷現實間達成的最佳抉擇。
“燕泥”這一意象承載樂觀、剛直、昂揚的精神,體現薛道衡最為積極的本質力量。“空梁落燕泥”通過“燕泥”這一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展現積極昂揚的精神以及面對困境的哲理——面對沒有意義、看不到希望的人生,唯一該做且能做的是堅持自己的理想、保持向上的姿態。“燕泥”作為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其自然屬性是穩定的。由于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欲望、稟賦、能力,無論古今都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名句“空梁落燕泥”在漫長的文學接受歷程中都能與人的本體生命互動、契合,在昂揚的精神基調下演繹出新的時代內涵,令讀者的閱讀視域與文本視域不斷融合,形成具體情境下的個性化詮釋。詩歌自然也成為了古今樂道的千古名句。
[1]趙炎秋.形象詩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0.
[2]葛曉音.八代詩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7:297.
[3]皇侃.論語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3:134.
[4]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1.
[5]曹旭.論宮體詩的審美意識新變[J].文學遺產,1988(6):66-74.
[6]木齋,侯海榮.論初唐樂府詩的去音樂化現象[J].學術交流,2011(11):155-160.
[7]蔣孔陽.德國古典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71.
(責任編輯:孫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