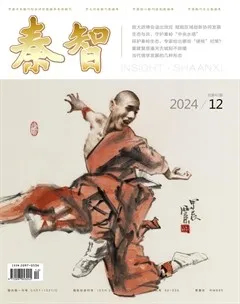馬克思的平等思想哲學辯證
[摘要]一般對馬克思的平等思想解讀都局限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不涉及到馬克思早期思想轉變,并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將平等視作觀念論的產物。但實際上,馬克思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就存在平等思想,并在對鮑威爾的深刻批判中深化了其平等思想。馬克思不僅將平等視作共產主義思想重要的理論范疇,而且認為平等是社會現實需求的體現。因此,對于馬克思而言,平等不再是觀念論的產物,而是人類解放的現實訴求。
[關鍵詞]《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平等" " "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12.007
平等是一個哲學概念,是古今哲學家都在討論和分享的理論資源。《論猶太人問題》是馬克思在1843年根據鮑威爾的論著回應的評論性文章,對平等觀念進行闡發和解讀,并以此批判了鮑威爾哲學。
一、馬克思對鮑威爾哲學的批判
學界一般將馬克思的1843年著作的影響推定到馬克思所讀的費爾巴哈的《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上。[1]馬克思當時作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員也在這次爭論中發表了他的看法,逐步明晰了自己的思想邏輯脈絡,并與早期德國思想家一道,對19世紀40年代早期法國共產主義者的理念進行了接納與融合。此時,馬克思受到了共和主義的影響,要求消除近代以來國家和社會界限,并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得到展現。[2]
馬克思的理論工作被當做現實生活實踐過程之中的變革追求,即基于烏托邦主義人類學的形而上學框架的理論構想。卡斯培認為馬克思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吸納造成的一種并不顯著的規范性倫理學前提資本主義批判。[3]馬克思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卻保留了上帝的位格,并且把人提升到上帝高度。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從這一路徑展開了對鮑威爾的批判。這種批判基于黑格爾哲學的遺產,也就是在《手稿》中所體現的異化論思想。這一方面是從費爾巴哈人本學的繼承而來,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對黑格爾哲學的深入研究。馬克思暗示了一種不通過任何政治機制而能夠實現人類社會的現實方案,便是通過烏托邦人類學和規范性倫理的建構秩序。
費爾巴哈在1842年注意到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確立了人的本質特性與人的分離,從而純粹將抽象的特性作為獨立的存在。[4]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本質主義的人類學方式,認為人是一種類存在生物,因此有可能作為類存在而實現自己真正的本質力量,在通過與鮑威爾關于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之間進行了討論與回答。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不能當作人類解放,宗教解放也不同于政治解放。
馬克思否定了通過任何宗教和政治機制就可以單獨完成人類解放的可能,而是人類解放是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根本性前提。[5]鮑威爾那里宗教本質與政治機制存在著形式上分裂,宗教是以一種先在的力量優先于政治機制,如果想要政治機制能夠有效的實現市民社會的平等形式,也就必然要求放棄宗教的理念,先實現宗教解放,才有可能實現政治解放。[5]
馬克思認為鮑威爾整個論證都是建立在某種哲學—神學的基礎上,不僅沒有理解當時的猶太教的歷史發展的現實狀況,更是忽視解放問題具體內涵的訴求。馬克思認為鮑威爾關于解決猶太人問題所提出的關于美國的政治與宗教關系的“新”提法,是擺脫舊世界的政治和傳統后出現的。面對美國這種國家是實現了宗教與政治國家的共存,所以當鮑威爾天真的認為通過宗教批判,將猶太人問題歸結于宗教問題;認為只有實現了宗教解放,才有可能成為政治解放的前提。馬克思分析了英法德美諸國的宗教與政治的解放問題,從而得出猶太教的產生歸根到底是社會性質的場域不一致而導致的。[5]
鮑威爾認為實現了政治解放就可以實現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即人類解放,實際上卻陷入了現實與理論的背反之中。即使將國家從宗教視域中解放出來,并不代表著現實的個人就能從宗教解放出來,并且還可能出現宗教與政治的一致性。即國家無法廢除宗教,兩者之間達成了一種相對的默契,并且即使國家政治是無神論批判性質,但是這仍然是抽象的迂回否定宗教,而不是直接的批判宗教,并且揚棄整個以此為基礎的現實生活。[5]
馬克思指出,宗教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關系具有共同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根源就是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沖突和危機,即宗教解放實際是政治生活的基本權利一種,而非一般權利。[5]政治解放不能揚棄宗教解放,宗教解放也不能揚棄宗教本身,而政治解放也不能推論出人類解放。人類的平等觀念也被視為一種異化觀念,正如指出馬克思認為平等觀念與社會環境有關系,而鮑威爾陷入這種對平等的執迷,更是因為受到了當時德意志思想政治環境的影響。
二、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抽象平等到現實平等
考慮到現代社會的歷史生活,宗教成為私人事務業已成為啟蒙精神的副產品,成為近代啟蒙以來法權政治平等的重要表現。一方面,宗教信仰在不斷的擴展與推進;另一方面,政治國家卻仍然占據根本優勢與其保持相對的距離,因而也就是造成了社會生活中人作為主體的多樣性的表現。
資產階級平等觀念容易引起人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誤解。伍德指出資產階級平等觀念力圖實現的平等理想,實質上是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這種理想已經而且將會繼續充當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工具,起到宣傳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6]顯然,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法權平等,本質上乃是基于政治解放所形成的一種抽象法權平等。然而,當這種抽象法權平等無法為市民社會中現實存在的個體提供根本性基礎時,其必然面臨被揚棄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作為19世紀中產生的社會改革與革命運動思想運動的重要思想流派,也對資產階級法權平等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科恩認為馬克思要求揚棄國家和社會的分裂,重建人類共同體生活。[7]《論猶太人問題》區分了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從而為實現人類解放提供一種理論路徑,人類解放也作為烏托邦人類學的一種形而上學允諾。馬克思要求內容與形式之間實現內在張力統一,而作為形式平等也就是法權平等的啟蒙生活是必然要求被揚棄的。馬克思正是對啟蒙運動中形式平等即法權平等繼承和揚棄的雙重批判后而得出的后啟蒙時代的現實平等。在《論猶太人問題》之后,馬克思也同樣發表了他對平等的看法。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認為只有實現了打破舊有國家機器,回歸現實的政治主體統治才能實現政治生活的現實平等;[8]只有政治生活的現實平等的得以實現,才能保證全體人的現實生活的統一和實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也以此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的同時保證分配有效性,即對現實平等進行了一種堅持和發展。
馬克思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反對啟蒙以來的宗教與國家形式上的一致來考慮的,國家政治視域下公民的宗教解放下的自由選擇是否是中立的和恰當的?選擇信不同宗教的宗教解放是否能帶來無神論的信仰呢?這顯然都是我們應該澄清和承認的傳統概念線索。
三、從《論猶太人問題》中的平等思想的兩個問題及其解答
現代社會是資本全球化的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無論是國家內部之間的階層矛盾,還是各個國家貧富差距的矛盾,正如胡薩米認為資本主義的財產權和收入分配的不正義,就是和不平等相關聯[9]。
我們要回應馬克思對于平等問題的一種回答,從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法權平等的激進批判得出兩個系統性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能夠得出關于宗教的價值與范圍中討論現代政治與宗教的一致性關系嗎?一個現代政治國家必須在哪種條件下保持與宗教的一致和統一呢?對于我們自身來說,在兩個方面有著系統性意義:其一,這些爭論并非是歷史問題,而是一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這一點馬克思的解讀更側重認可是社會結構的劃分;其二,這些爭論同今天討論其價值合法性的哲學家、社會改革家一樣,分享了近代以來的政治、宗教、思想傳統,也享有我們近代考慮的民族文化傳統。實際上,澄清線索有助于開展時代自身的范疇和理念。
第二個問題,涉及法權平等與現實平等,馬克思對民主制度的激進政治批判正是通過對兩者的區分獲得當下我們討論的系統性意義和價值的。伍德認為,馬克思潛在地將價值觀念劃分為兩類:一種是自由、自我實現,這些概念具有批判性功能;另一種是諸如平等、正義,這些概念僅僅屬于法權概念,無法被批判性地使用。伍德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法權批判,是因為資本主義阻礙了社會客觀歷史的進步而無涉道德層面的批判。
法權平等被認為是一種中立性概念,人們也必須認同法權平等帶來的正面積極效應,這也是當代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成就之一,法律被認為是超越于國家民族統一體優先的原則,建構了作為人類的人格區分認同體。我們認同馬克思關于法權政治批判也不無道理,的確法權平等不等同現實平等,并且法權被濫用于國家以及國家內部,造成了戰爭和一系列非法的、合法的毀滅,或者訴諸于人道或者非人道的事件。但另一方面,法權原則的擴張和另一方面現實平等作為反擊性的策略可以進行一定的調整,或許能夠給當代的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內在統一,提供一種無需論證的理解。平等思想的歷史性范疇的轉變以及烏托邦人類學視角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人類解放。可見,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真正關注的是每個人的需求的滿足,以及個體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此時,當通常意義上的平等實現的時候,平等的權利是否得到了遵循以及平等的分配結果是否得到了實現和不平等作為相互決定的因素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且不相關了。在烏托邦人類學視角中,人類達到那種理想性可達到的社會歷史境遇,平等也就不再是一種觀念性的存在概念。
四、結語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所闡發的平等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極為重要。其一,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對鮑威爾的平等觀念展開批判,對以往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政治解放進行澄清,指出其資本主義制度下平等觀念的邏輯矛盾,一方面是現實生活的不平等生活和法權觀念上的平等價值,另一方面則是政治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平等實現其平等限度極其有限。其二,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在思想史上主要是以哲學視野所展開的對鮑威爾的批判,而對現實和理想的平等理念分裂語境選擇了超越性的開闊性歷史性看法,將平等視作人類走向自身解放的范導性范疇。
參考文獻:
[1][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4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美]諾曼·萊文.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對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169.
[3]Robert C. Tucker.Philoph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M].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1972:22.
[4]黑格爾.黑格爾通信百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270-275.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46
[6]Allen Wood.Marx and Equality”,in John Miller(eds),Analytical Marxism[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86.
[7]J.L.Cohen,Class and Civil Society.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M].Ameherst,1982.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222.
[9]Ziyad I. Husami.Marx on Distributive Justice[M].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8,No.1.(Autumn,1978):32-41.
基金項目:黑龍江大學學生學理論學術課題指導項目:黑龍江大學學生學理論學術課題一類項目,項目名稱: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視域下的中國式現代化思想起源研究(項目編號:202303)
作者簡介:任平(1998.7-),男,漢族,黑龍江哈爾濱人,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