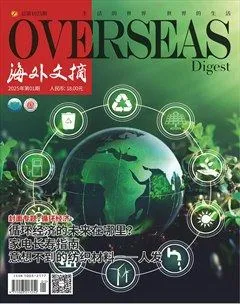兒童房:父母監管的法外之地?
當孩子深陷電子屏幕的誘惑時,家長該如何應對?嚴密監控能否解決問題?學校教育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 教育需要與時俱進 |
結束上午的授課后,迪特·呂蒂曼在辦公室里接受視頻訪談,講述他心目中與時俱進的學校應有的樣子。這位瑞士教育家教授德語、法語、數學以及沒有被納入任何教學計劃的“應對生活挑戰”課。
在蘇黎世開辦“尤特斯特拉斯綜合性初中”也是呂蒂曼的主意。從1981年開始,孩子們就被分成跨年級的小組全日制學習,六年級之前都不會有成績評分的壓力。學生可以帶手機進入校園,但每天早上都要放入衣服兜里,再掛在衣帽架上,只有學習需要時才能拿出來。學長學姐們也會給年紀較小的學生上課,并在這個過程中學到難得的一課。在“應對生活挑戰”課上,學生們分組討論生活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例如與父母分離、朋友之間發生沖突、憂慮或者驚恐發作等。呂蒂曼表示,學校是社會化教育“最重要的工具”,因為不同家庭背景、性格和資質的學生在這里共同學習。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除了數學和拉丁文之外,學生們還能學到團隊合作精神和協商解決問題的能力。
呂蒂曼是《童年,別太擔心》一書的11位作者之一。教育學、發展心理學、兒科、傳播學、政治學和心理學領域的專家們齊聚一堂、集思廣益,在以“為了孩子”為主題的智庫研究中將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匯編到一起。對于如何讓今天的孩子們健康發展,他們寫下了自己的設想。這本書能幫助成年人更好地理解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以及成年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 被高估的父母影響力 |
該書的觀點認為,父母往往會大大高估自己對后代的影響力。只有當父母停止以推土機的方式為孩子鋪路——有時可能是一條歧路,孩子們才有機會成長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個體。
兒科醫生奧斯卡·杰尼創辦了關于童年的研究智庫,這位蘇黎世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兒童發育科的主任是雷默·拉爾戈教育理念的后繼者,后者因其暢銷教育書籍《嬰兒時期》而聞名。拉爾戈主張在子女教育上應保持冷靜,停止揠苗助長。
杰尼認為,拉爾戈的理念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很久以前,他就已經發現,很多孩子過得相當糟糕,因為大人給他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導致他們缺乏安全感。兒童發育科的候診名單上有大約2000位小病人。他們的父母想知道:為什么自己的孩子總是吵鬧不休或沉默寡言?他是不是有學習障礙、得了多動癥或者發育遲緩?
杰尼注意到,在面對孩子的健康問題時,這一代父母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和無助。在個性化的社會中,父母幾乎要對孩子生活中的一切負責,同時還要面對與其他家長比較的壓力,因為總有孩子比自己的孩子更多才多藝。另外,他們還得幫助孩子抵抗數字世界的誘惑。
“這對父母來說當然是沉重的負擔,”杰尼說,“而父母仍然盡心盡力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這位兒科醫生認為,父母們的擔憂合情合理。很多研究表明,童年時期的經歷往往決定了一個孩子能否擁有美好的人生。
然而,并沒有可以確保童年幸福的秘訣。“我們不可能主動規劃和掌控子女的人生道路,也無法確保他們能夠成功。”杰尼說,“他們對什么感興趣或者學習何種職業技能,會受到他們的天賦及所處環境的影響。”只有在童年時期,孩子們才會乖乖聽從父母的教導——越長大,其他方面的影響就會越大。
“孩子年紀越長,父母對他們的控制力就越小。”杰尼說。作為一位父親,他也有同樣的經歷。他的經驗表明,大多數情況下,孩子們都能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父母能為孩子做的,就是成為他們堅實的依靠,隨時傾聽他們的憂慮和苦惱。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感受到“濃濃的愛意”。
| 數字媒體:禁絕還是擁抱?|
《童年,別太擔心》一書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孩子們有權使用數字媒體,刻板教條地限制使用并不能讓他們自動學會以健康的方式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打交道。
丹尼爾·瑞思是瑞士蘇黎世應用心理學院的媒體心理學家。30年來,他一直在研究兒童如何與多媒體互動。他表示,每一種新型溝通工具都會讓相應時代的父母陷入恐慌。以前的父母害怕閱讀大量書籍對孩子的影響,后來他們又質疑漫畫會讓孩子喪失對文字書的興趣,可能對孩子心智造成破壞性影響的電視購物更是被他們視作洪水猛獸。現在,父母們還不得不面對視頻平臺博主、游戲主播和電競明星對孩子的影響。瑞思認為,父母對數字媒體的懷疑是這種擔憂的延續,但又有一點區別,因為現在的孩子們在社交媒體上不只是單純的消費者,他們也產出自己的內容,因此父母還需要面對社交媒體應用中所有與之相關的潛在風險。
然而,瑞思對于數字媒體仍然持“謹慎樂觀態度”。他與其他專家一同為《童年,別太擔心》一書創作了《數字媒體世界中的童年》這一章的內容,并給出結論:禁令并不能讓孩子們學會抵制數字媒體無處不在的誘惑。他解釋說:“比起關注孩子們在社交媒體上花費了多少時間,更應該關注他們是否因此忽視了其他活動,比如進行體育鍛煉或與朋友們在現實世界中聚會等。”如果孩子們能夠很好地平衡數字媒體與現實世界,父母也就不必掐著秒表在孩子們的兒童房里計時了。瑞思舉例說:“就像如果孩子熱愛踢足球,我們也不會限制他每天只能踢一個小時球。”
德國的大部分兒童和青少年似乎都能把握好兩者的平衡。2023年一項名為“青年、信息、媒體”的研究中,有60%的12至19歲青少年表示,他們每周會多次與朋友聚會或參加體育運動。這些年輕人仍然會閱讀紙質書。與前些年的調查相比,甚至有更多受訪者每天都讀書或一周有好幾天會讀書。
受訪者每天的平均在線時間為224分鐘,高于2013年的179分鐘,但與2020和2021年相比,這個數字有所降低:2020年,這項調查的參與者每天在線的平均時長達到了近260分鐘。
這項研究同樣揭示了數字空間中存在的危險:1/3的女生和1/4的男生都曾遭受網絡騷擾,23%的受訪者在調查前一個月內通過數字媒體接觸過色情內容。瑞思表示,正因為存在這些危險,孩子們必須學會如何負責任地應用社交媒體,并在遇到危險時保護好自己。
而對于電子媒體會給兒童的認知發展帶來多大的損害,仍存在爭議。牛津大學下屬牛津互聯網學院的研究人員與美國同行合作,分析了數千名9至12歲兒童每日電子屏幕使用時間與他們的腦功能和腦發育數據。即使在那些每天屏幕時間遠超平均的青少年身上,也并未發現他們與其他孩子相比大腦發育受到阻礙的證據。這項研究沒能為“限制多媒體使用時間可以保護神經認知發育”這一論點提供支撐——研究者們在國際專業期刊《皮質》中這樣寫道。
然而,數字世界可能致人成癮。根據德國聯邦衛生部的數據,12至17歲的受訪者中有8.4%的人,18至25歲的受訪者中有5.5%的人表現出與電腦或互聯網相關的戒斷障礙。“社交情境常常會導致成癮行為,受到排擠的孩子可能會轉而在社交媒體上尋找歸屬感。”瑞思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父母需要密切關注孩子與社交媒體的互動。”
另一方面,在瑞思看來,如果孩子經常與現實生活中的朋友一起組團長時間玩網絡游戲,父母們則無須太過擔心。書中是這樣說的:“數字媒體本身對孩子來說無所謂好壞,待在電子屏幕前的時間也不能作為評判孩子能否積極利用數字媒體的核心標準。”我們應當從孩子的視角出發,理解他們所處的數字環境,而非僅僅基于成人的擔憂和臆測來作出評判。
兒科醫生杰尼說:“孩子們是世界更新的源動力。”社會的發展應當緊密圍繞實際需求展開。在制定法規時,我們應該如同對待氣候保護和性別平等議題一樣,審慎評估每項法令是否真正符合兒童的利益。
教育家呂蒂曼則希望家長能夠認識到學校作為社會基石的重要性。在德國和奧地利,孩子的社會出身往往是他們能否通過教育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這種狀況迫切需要改變。
編輯: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