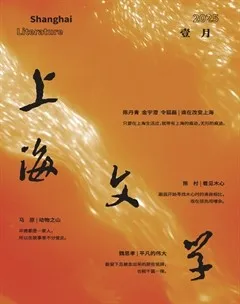當下青年寫作的“自我”理解、流動經驗與敘事新變
青年作家作為未來文學事業的生力軍,他們的成長一直備受矚目,很多刊物也都開辟了青年寫作專欄。如《收獲》在二○一○年便策劃推出“青年作家小說專輯”,這一扶持青年作家的專欄堅持多年,漸有口碑。另如《人民文學》的“青年新作輯”、《上海文學》的“新人場特輯”、《芙蓉》的“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十月》的“小說新干線”、《長江文藝》的“青年作家專輯”、《萬松浦》的“青年作家小說專輯”、《當代》的“青年創作專號”、《青年文學》的“現在出發·小說專號”、《草原》的“青年小說專號”、《花城》的“花城出發”、《山花》的“開端記”、《作品》的“超新星大爆炸”等等,也確有一批“九○后”乃至“○○后”的青年作家借助這些欄目脫穎而出,成為文壇矚目的新星。
本文以《上海文學》《收獲》《人民文學》《萬松浦》《長江文藝》五家刊物二○二四年度青年專欄(具體為《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人民文學》二○二四年第九期、《萬松浦》二○二四年第四期、《長江文藝》二○二四年第九期)所刊載的二十八篇小說為對象,嘗試對當下青年作家的小說創作略作解析。相對于數目龐大的青年作家群體,這樣掛一漏萬的解析當然個案意義更強,不過,從這些小說中提煉出的若干角度,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管窺青年寫作的某些新質與征候的。
一
“既然我們的前輩作家仍然在勤奮地寫作,“五○后”“六○后”,一本接一本,并且他們相比我們而言有著更豐富的經驗、更純熟的技巧和更廣泛的知識,那么青年作家寫作的價值和意義究竟在哪里呢?”這是小說家石一楓參加全國第九次青創會談及青年作家身份時提出的一個疑問(石一楓:《文眼、文心、文采》)。這個疑問當然是普遍性的,它所體現的不但是青年作家面對經典寫作的“影響的焦慮”,亦是針對自身寫作的“合法性的焦慮”:就“社會文化事實”層面而言,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發掘、擢拔新人是文學迭代更新的必然要求;就“審美事實”層面而言,前輩作家構建的審美秩序依舊安穩龐大甚至牢不可破,后來的作者既被這一秩序塑造,也逐漸被吸納為秩序的一部分。因此,青年寫作往往既是被詢喚的,也是被預制的;既是被期待的,也是被質疑的;既是被呵護的,也是被挑剔的。而這樣的雙重性,既是青年作家置身的外在情境,也被內化為寫作時一種復雜糾纏的心境。
在集中閱讀這二十多篇小說時,筆者最大的感受是,這些頗有才華的年輕人渴望綻放,也等到了冒尖的時機,他們懷抱小小野心嘗試“創造性的背叛”,在小說題旨和敘事的選擇上謹慎地標記出他們的不同,努力在文學花園里獲得一席之地,仿佛在印證埃斯卡皮說的:“當上一代的主力軍超過四十歲時,新一代的作家才會冒尖。當有地位的作家的聲望逐漸減弱、開始承認年輕作家的壓力的時候,即從平衡出現的時刻起,群芳斗艷的局面似乎才會到來。”(《文學社會學》)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有所猶疑的,他們深知前輩的期許,也了解比他們稍微年長的群體曾遭受到的批評及其癥結所在,他們小心翼翼地規避這些可能加諸自己身上的非議,努力以正向而非逆反的方式成為作家代際鏈條中被悅納的一環。在這樣的權衡之下,他們的寫作較為典型地呈現出一種“以自我為方法”的特質,而不再是“以自我為目的”的,其內核是個人經驗的問題化、隱喻化和時代化,其“重點是理解構成‘自我’的關鍵他者是社會性、經驗性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歷史來源和當前的行動中作出平衡,進而把關心的問題用自己的位置講清楚”(周芳、夏瓊:《“把自己作為方法”何以可能》)。
如果對比二十多年前“八○后”作家剛入文壇時的創作,就能看得更明白。在“八○后”最早的那些寫作者中,他們筆下的自我大多是一種沉溺式的自我,被敘事者牢牢拘囿在個人的經驗范疇之中,個體是出發點,也是終點,人物很少有對自我實踐的反思,也很少有外向的社會鏈接。而今天的青年作家,雖然也強調個人經驗,強調個體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但他們也注重在與日常生活的微觀互動中去觀察社會,注重“通過對生活世界具體的、物質的認識和實證的、經驗的描述,來嫁接個人經歷與宏大的社會問題”,因此,個體是出發點,也是通向廣闊具體世界的方法和路徑。“以自我為方法”就意味著以自我的位置為觀測點,通過將自我經驗對象化,將自己定位到所處的社會關系和時代之中去思考問題。如同卞之琳的《斷章》四句所昭示的那個情境,瞭望者同時被他人瞭望,個體始終處于主客觀的間性之中,個體是經驗的主體,也是經驗的對象。青年作家們所表現的這樣一種認知自我和世界的心智品質,有點類似米爾斯所談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這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是一種能“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并觀察二者間的聯系”的能力。
對此,陳薩日娜的小說《第一人稱》(《長江文藝》二○二四年第九期)通過不斷變換敘事人稱和角度,給出了一個帶有寓言意味的總括。小說的主人公華虛舟是一名高校教師,為了職稱,他委曲求全地討好院長,但還是未能得償所愿。小說時而用第三人稱,時而用第一人稱。還不止于此,某天主人公下班時遇到一陌生男子搭車,奇怪的是,他居然知曉敘事者所有的生活隱秘,原來他乃是敘事者的分身。與先鋒文學的前輩們不同,陳薩日娜不斷變化人稱、制造敘事分裂,考量的重心并不在后設的敘事技藝層面,而是借此探問如何才能獲得主體自我反思的深刻,答案就是在人際關系的生態中、在自我與他人的連接中去辯證地思考,就像小說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有天他發現他已經不是自己,事實上沒有‘自己’存在,他是所有他遇到過的人的集合。”那個搭車的分身通過與現實之“我”的交流,引領“我”正視生活的另面。小說的結尾饒有意味,經歷了車中對分身“自我”的艱難回應,“我”轉身看著他,“‘沒有人’,他低著頭呢喃道,‘外面沒有人,除了我們自己’”。小說由第三人稱敘事開篇,收束于第一人稱,看起來是對“自我”的重新回歸,但是必須看到,回歸的前提是第三人稱對第一人稱的拷問,是在經歷了“社會化的自我”這個必要的中介后才完成的。
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兔草的《渡觀音》(《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和倪晨翡的《七傷拳》(《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渡觀音》中的杜荷“幻想著某一日有人可以向父母道出她的死訊,而她則化為另一副面孔,在地球的另一端獨自生活”。她邂逅了與她有著同樣想法的蘇阿姨,兩個人決定各自到對方的家中宣布她們的死訊。杜荷開始像一個偵探一樣跟蹤蘇阿姨的兒子。在跟蹤中,她發現,蘇阿姨的兒子一直在假裝上班,實際上他并無班可上,只是四處游蕩打發時間。他和杜荷、蘇阿姨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都被浩大無邊的生活所吸附,想要保留自己的一點痕跡卻又找不到得體的應對之道,所以才選擇假裝死去或假裝上班。本質上,《渡觀音》講的是一個疼痛的故事,一個鄉下女孩在大城市討生活的艱辛,冷漠的家人對她的寄生,社會如巨獸對她既覬覦又敵視,成長的敏感與躊躇……所有這些在青年寫作中并不鮮見,但《渡觀音》通過引入蘇阿姨和她兒子的生活,以杜荷之眼觀人再反求諸己,在她的個體疼痛中寫出了他人“同此涼熱”的寬綽,或者說,她“在特定的條件下”“感受到共同體的存在”,這也讓小說中觀音的意象具有了真正慈悲的附著。
《七傷拳》在一個重組家庭的空間內部,聚焦青年成長中被拋棄的痛疼和孤獨,主題也談不上新鮮,不過在處理這個主題時,作者同樣將自我做了對象化的處理。敘事者與弟弟的關系正類似《第一人稱》中自我和分身的關系,而“七傷拳”是所謂傷人又害己的拳法,隱喻的也是自我與他人的關系處境,即作者自言的:“無論傷己還是傷人,都發生在這個家,涉及家里的每個人。”小說借由敘事的含混,有意模糊“我”與弟弟的記憶,在不斷反轉中告訴讀者,事實并非“我”是弟弟的參照,而是兩人“互為參照”,沒有弟弟這個參照物,“我”也不會艱難地啟開羞恥的心扉。
另一個典型文本是楊知寒的《飛煙》(《長江文藝》二○二四年第九期)。這篇小說通過三個人之間“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式的關系,揭示了個人主體性的游移。孤立地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行動的情由:作為新聞記者的孟還潮被一種自我功績意識激勵著,周顯聲要靠經營燒烤攤掙錢養家,李全則為了母親鋌而走險。合起來看,他們的行動卻宿命般地環環相扣:周顯聲燒烤攤繚繞的煙氣逼得李全母親找記者爆料,孟還潮實地調查被周顯聲威脅,而為了給母親治療眼疾的李全在街頭搶劫孟還潮時失手刺死了他。他們三人之間就這樣結成一張隱秘的蛛網,而他們每個人既是蜘蛛同時也是被蛛網俘獲的獵物。就說服力而言,《飛煙》不能算是一個好故事,畢竟人物之間的關系設置刻意到失真,但作家考量更多的肯定不是故事,而是人與人錯謬的巧合里包含的宿命及其內蘊的批判,即便是自以為正義的孟還潮也與周顯聲和李全一道處于一個“互害”型的秩序之中,主客的位置隨時逆轉,這恐怕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雷蒙德·威廉斯在討論情感結構時,提醒我們:很多個體的情感經驗常被當作私人性的、孤立的,但實際上這些經驗的背后充滿社會性。米爾斯也指出,重要的是區分“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這二者的不同:困擾是私人性的,產生于個體性情之中,而論題是公共性的,“超越了個人的局部環境和內心世界”。借用這些說法,當下的青年寫作者也正努力把前一代際寫作者認為是個人“困擾”、私人經驗的東西置入社會關系的“問題”情境中看待,以讓自己的寫作更開闊和及物。雖然他們的觀察還未必深入,思考也難言縝密,但這種在社會與個體的互動中理解自我的努力方向是值得鼓勵的。
二
流動性已經成為全球青年的日常狀態,中國年輕人在二十一世紀的遷移和跨國寓居也早已不同于前輩們辛苦的背井離鄉,而是全球化跨疆界的嶄新生活。傅懸的短篇《吃黃昏》(《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與孫孟媛的《螞蟻爬行》(《人民文學》二○二四年第九期)是兩篇可以對讀的跨國題材小說,關注的也都是中國新經濟背景下的流動青年,且都從“吃”與食物這個角度切入,思考當代青年在不斷加速的社會流動中脫域和再嵌的問題。兩個小說的主人公都試圖在資本與超大城市的擠壓之下,在家庭內部找到一個讓情感和鄉愁落地的空間據點,卻發現結構性的社會空間等級在新的流動格局中依然得到保留。跨國青年關于飲食的傷心故事,某種意義上是置身高度同質化的全球城市結構之中的青年人關于情感理解、身份塑造和性別協商的轉喻。
《吃黃昏》里的年輕夫婦住在紐約長島的豪華公寓。丈夫羅望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后在紐約的高科技企業當程序員,妻子美琪做了全職太太。“羅望是一個頂好的丈夫,辛苦工作,按時回家”,而美琪也是一個頂好的妻子,每日在家為丈夫烹制可口的飯菜。日復一日,丈夫甘之如飴,妻子卻隱隱有一種失落,她找工作的念頭漸漸熄滅,內心不得不承認:“丈夫就是她的雇主,照顧他就是她在這片新大陸上的新工作。”這一天,丈夫電告妻子要帶友人回家吃飯,卻忘記了當天是妻子的生日。美琪精心準備了一桌中國美食,不料卻因友人兒子對生姜過敏生出一場事端,那看似安穩錦繡的生活也終于展示了它殘破的暗角。小說的小標題不停在長島、法拉盛、波士頓之間轉換,標示這對夫婦置身世界的位置,可另一方面,美琪出入最多的空間卻是華人超市和中國式的廚房。美琪就這樣處于向世界敞開又被世界拒斥的流動點位上,于她而言,生活就是一種“歸屬感和流動的復雜交疊”。小說的結尾,美琪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覺,醒來收到丈夫的信息,朋友的孩子因為過敏的休克反應死去了,美琪感覺被子彈擊中又仿佛靈魂出竅,稍事盤桓,她“穿戴整齊,走出門去”。既然居住之地并不能嵌入并安妥個人,那就像娜拉那樣勇敢地走出去吧,只是她能走到哪里去呢?
《螞蟻爬行》里處于試婚階段的年輕伴侶把小家安置在新加坡的金文泰街區,準丈夫是在讀博士后,準妻子辭掉了國內工作專程到新加坡奔赴愛情。像美琪對羅望一樣,這個小說里的妻子也變著花樣給丈夫做飯,“廚房戰役令她既緊張又興奮”,“好像實現了自己作為準妻子的價值”。不料,家中儲備的食物引來螞蟻,這讓丈夫不快,他勒令妻子停止做飯,一日三餐都去食閣和學校餐廳解決。妻子無法忍受沒有煙火氣的家庭生活,偷偷買了米面糧油和各種調味品,做賊一樣偷偷為自己做飯,于是蟻群再度歸來,而且儼然成為橫亙在這對準夫妻之間的一道厚障壁。四處爬行的螞蟻不過是這對青年伴侶生活困擾的外顯形式,而他們的困擾對應的正是跨國流動經驗中身份與情感的自處問題。小說結尾,妻子沒有像美琪那樣選擇離開,而是告訴丈夫:“我看到一道閃電劃破夜空,劈開了眼前的混沌。”這道想象性的閃電在瞬間照亮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而在寂滅之后生活復又回到漫無邊際的日常。
兩個小說不約而同地選擇食物作為情節聚焦的中心,《吃黃昏》里的姜汁核桃燉蛋和《螞蟻爬行》里的蜂蜜水也因此成為各自小說中的“刺點”。如果說小說中紐約和新加坡城的生活構成一種絕大多數人想象中理想的跨國生活樣態,那么作為細節的食物卻跳出這一樣態成為直擊人心、刺痛讀者的所在,用羅蘭·巴特的話來說,就是這被捕捉到的時刻讓人產生了震驚、“頓悟”和“剎那間的空虛”。當然,巴特在《明室》中嚴格把“刺點”等概念限制在攝影的界域之中,但這不妨礙我們引申借用,“刺點”之所以讓人產生刺痛,“是因為在某個瞬間,一種隱匿的、獨特的創傷突然顯現”。在《吃黃昏》和《螞蟻爬行》中,這個創傷是女性被漠視的忍耐和被規訓的柔順,是遠隔萬里無從消化的鄉愁,是在流動的異鄉中對主體進行的具有高度象征性和深刻日常性的標注。
跨國之外,城鄉之間的往返構成中國境內社會流動的重要方式,這是近來青年寫作聚焦的主題之一,也是這一次各大刊物青年寫作專欄中最集中的題材,丁顏的《夾竹桃有毒》(《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徐佳貴的《拾夢者》(《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崔君的《在小山的陰影中》(《人民文學》二○二四年第九期)、尹林的《雪落在安靜的小院》(《人民文學》二○二四年第九期)、吳越的《呦呦鹿鳴》(《人民文學》二○二四年第九期)、若非的《溢補嗒啟》(《萬松浦》二○二四年第四期)等均借返鄉的框架或情節表達個人對“流動的地方性”的思考。
《夾竹桃有毒》中的母女兩人分別經歷了漂流的生活。母親弗米是藏族,她愛上回族商人馬明心,跟著他從林芝藏區私奔到了甘肅回族地區,“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族群到另一個族群”。女兒阿敏在父母與祖父母分家時被祖父母留在身邊,長大后跟隨姑姑在麥加留學。自幼的分離讓母女間一直保持疏遠的相處,直到留學歸來的阿敏陪伴弗米回到藏區,她才真正懂得了母親的孤獨和堅韌。阿敏跟隨母親的返鄉是一場個人的療愈之旅,也是母女親情的和解之旅,小說的高明之處在于規避了類似主題敘事的簡單化和雞湯化,深刻寫出了經歷流徙與離散的個體處理新舊情感關系以及轉換身份的艱難。小說有一筆很動人,阿敏在麥加陪伴祖父祖母朝圣時,每到人群過分擁擠時,就有人出來保護老弱高喊“媽媽”,阿敏心有所動,晚上夢見弗米,醒后覺得荒涼,卻也在心里植下走近她的根苗。麥加、臨潭、林芝,從世界到故鄉,信仰的虔敬和親情的渴望始終交織,阿敏的朝覲之路其實是雙向的。在返鄉的部分,小說一面寫舅舅洛桑的沉默、弗米和妹妹白瑪的爭吵、弗米對姨夫的訓斥,一面寫南迦巴瓦峰下桃花搖曳多姿,寫藏族小孩子的發式、打扮,尤其是他們腰間佩的紅腰帶,小說中的“刺點”時刻也隨之而來:“阿敏一下子呆立在原地,原來曾讓她挨打的紅腰帶竟是弗米說不出口的鄉愁。”這里既照應前文阿敏的記憶,也以遲來的見證銘刻母親試圖彌合身份撕裂的疼痛和倔強。小說將“豐富的內容熔于一個故事”,連綴多個時空,并借夾竹桃的意象,將母女內心隱忍多年的傷痛和終于走向達觀的穎悟,娓娓道來,體現了年輕寫作者不凡的才華。
相較之下,《雪落在安靜的小院》采用了當下較為典型的“農裔城籍”讀書人返鄉敘事的結構,筆墨上更為單純一些。臘月里,年輕的大學教授明堯跟著妻子一同到山西朔州鄉下探訪岳父母,感覺“鄉村是被摁實了心臟,感覺滿天星辰和這一窗剪影比霓虹街道、燈紅酒綠更有力量”。不過小說并無意美化詩性的鄉土對歸來者的撫慰,隨著敘事的深入和記憶的鋪展,小說城鄉對比的視野也逐漸顯現,城鄉流動中的身份遞變、階層想象、隱蔽的性別秩序,以及鄉土與親情的重建、高校“青椒”陷入考評指標的倦怠與反思等等,都被織入小說,成為意義的話頭。為了避免歸鄉的知識者選擇性的視角可能造成的遮蔽,小說敘事焦點是不斷轉換的,從明堯到岳父再到妻子,形成外來者、守鄉者和歸鄉者三種視點的互補。在轉到妻子時,小說著意寫了一筆,家里的黑山羊“煤大王”死了埋在后山,妻子帶著弟弟妹妹特意去了一趟,看到了父親給黑山羊做的小方碑,還看到墳前有不少放羊人放的新草,他們“大概都愿意來給煤大王掃掃墓”。對黑山羊的憑吊也像是小說的“刺點”,那個靠煤吃飯的年代已經過去,男人們在老去,他們的孩子到世界上去,情感表達和價值判斷的張力在無聲的憑吊中得到強烈凸顯。同《夾竹桃有毒》類似,《雪落在安靜的小院》也給了讀者一個和解的收束,雖然歸鄉的妻子又要離開,遠赴南方的大哥終于有了令人心安的消息,一場大雪紛揚而下,“落在安靜的況家小院”,但留下的人、離去的人和遠在天涯的旅人心中涌動的都是暖意。
通常來說,地方經驗構成作家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借用“戀地情結”的討論范式,如果說從“感知”到“態度”再到“價值觀和世界觀”,“地方感”必然會投射到作家作品中,那么新時代年輕人的地方經驗也一定因位置、背景UDUFlGjur+Jvp+NyDy06LA==、邊界和視野的位移為當下青年寫作的“地方性”帶來變數,正像鮑曼在討論“流動的現代性”時所談到的:“它們或‘流動’,或‘溢出’,或‘潑灑’,或‘濺落’,或‘傾瀉’,或‘滲漏’,或‘涌流’,或‘噴射’,或‘滴落’,或‘滲出’,或‘滲流’,千姿百態,不一而足。”倘若缺乏流動,地方感知難免景觀化和固化,其實等于剝奪了地方的獨特性,對地方“靈暈”的再啟需要適當的反觀和別處的參照,因此,在被廣泛熱議的新東北和新南方之外,跨國、進城、返鄉等多重流動的地方經驗交疊所塑造和呈現的微妙心理感喟,理應獲得更多關注。
三
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處于關于生活的一切都被信息所表征的情境中,這自然會導致敘事的衰敗和語言的變異,也意味著青年寫作者比前輩面臨更大的挑戰:一方面,他們要在敘事魔法失效的時代,找到勘探世界的支點,在信息和數據海洋之中,“尋找敘事的錨地”,另一方面,前輩在敘事實踐上幾乎探索了所有的領地,留給他們的創新空間極小,人工智能又在一旁虎視眈眈,而“能改變世界、開啟世界的講述并不由某一個體隨意創造出來,其產生基于一個有不同力量和參與者介入的復雜過程”(韓炳哲:《敘事的危機》),激活敘事的智性能量、維系小說對抗“存在的被遺忘”的尊嚴并不容易,他們需要找出突圍之路。
杜梨的《鵑漪》(《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是篇異質性很強的小說。作者在談及創作意圖時著意說到:“人類社會中層出不窮的欺騙、暴力、虐待與兇殺,幾乎讓新聞成為一種恐怖的‘舊’,見過各種可怕的現場,身為寫作者恐怕無法無動于衷。”言下之意正體現了以小說對抗信息吞噬的職志。《鵑漪》在征用科幻、懸疑等當下炙手可熱的敘述元素的同時,又通過煞有介事地杜撰古書,滲入后設小說的趣味,此外,它還借物候、鳥類、建筑和狹義相對論等內容,力圖“實現一種動植物與現實的有機結合”,以賦予小說更高的知識密度。小說故事腦洞大開,敘事極為自由,仿佛不為任何經驗或超驗的考量羈絆:女主人公花末具有入夢且在夢中棲居的能力,并可將夢中的靈感渡引到現實。她在試住一所兇宅時發現了空間裂隙,在裂隙中邂逅前任業主的妻子齊鵑,齊鵑向她道出失蹤實情,自己乃是被陷入科技迷狂的丈夫所害。花末將此托夢丈夫多荷果,失蹤懸案得以破解。米蘭·昆德拉認為“夢的召喚”是挽回小說末路的方式之一,在我們討論范疇內的二十多篇小說,幾乎每篇都寫到了夢,倚重夢境作情節和情感串聯的也有好幾篇,比如陳麗的《黃昏如期而至》(《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以及前文討論過的《夾竹桃有毒》等,但《鵑漪》對夢境的塑造還是顯得頗為不同,在杜梨這里,夢的存在不是昭告被壓抑的潛意識和欲望,也不是理解人性幽暗意識的入口,它既具有強大的變現能力,又可以讓“死生的交界”變得模糊,乃是小說存在的必要前提,這正回應了昆德拉召喚夢境的動機,借助夢境,小說“可以擺脫看上去無法逃脫的真實性的枷鎖”。
《鵑漪》中的知識性內容也很值得探討。小說將雪鸮、杜鵑、中華攀雀、《營造法式》、CPT原子鐘、高能粒子炮等等冶于一爐,彰顯了寫作者的博識多聞。這其實也是一種創作趨勢,正像一些批評家觀察到的,“今天的時代在文學教育上比過去更為完善和健全,年輕一代的作家明顯都有著良好的文學教育背景,他們在審美選擇上、在文學思維上更偏向于現代主義文學,因此多半也是采取知識性寫作”(賀紹俊:《知識性寫作與介入文學現場》)。也有批評者擔憂,青年寫作群體趨向“高知化”“精英化”,可能會導致一種“圍欄癥”,即被“成功寫作范式”這些訓導的內容“限制住想象力發揮,沒有成為真正的作家,反而成了‘圍欄里的文學愛好者’,養成一個‘作家的范兒’”,作家本該有的豐富、蕪雜、無拘無束自然受到了蔽抑(房偉:《當下青年寫作的“四種征候”及其反思》)。《鵑漪》的例子說明,博物的興趣、跨學科的開闊視野,可以幫助寫作者打開“圍欄”。何況,《鵑漪》也注意到知識性寫作與經驗性寫作的均衡,年輕人何以為家、居大不易、生育焦慮等現實問題始終構成副線,且對各種點綴的知識形成了必要的牽制。
郭誰的《尺八》(《萬松浦》二○二四年第四期)也是一篇知識性很強的小說。尺八本是中國傳統樂器,盛行于隋唐宮廷,約在七到八世紀時傳到日本,后在中國反而絕跡。一九三五年,客居日本的卞之琳偶然聽到尺八吹奏出猶有唐音遺韻的曲調,寫下了著名的《尺八》一詩:”像候鳥銜來了異方的種子,三桅船載來了一枝尺八……”郭誰的小說由此伸展,以尺八自下而上的筒口、一段、二段、三段、四段、吹口分為數節,分別敘述天啟元年倭寇與明軍作戰事,卞之琳羈留日本寫作《尺八》,七七八年遣唐使小野石根在海上遭遇風暴,六○八年大隋答禮使裴世清在奈良將各種樂器和珍寶贈給圣德太子,六二九年呂才被唐太宗召見為尺八定名,一二五三年日僧心地覺心在護國仁王禪寺習禪并學習吹奏尺八,一九一一年蘇曼殊在東京的“斷鴻零雁”之感,以及二○二四年一位接受化療的山東女子在尺八空靈遼遠的音色中獲得的生命穎悟。小說并未采用歷史編纂的元敘事,而是將一系列基于真實文獻的歷史知識和音樂知識碎片靠一幅尺八圖串聯起來,讓不同世代的人物形成潛在對話關系,在有限篇幅內將文明交流互鑒、傳統創造與轉化、對歷史意義的領受和個人心性的安置等多元主題措置裕如地融入,體現了寫作者構思的匠心。
在敘事上較為別致的還有錢杏的《進化論》(《萬松浦》二○二四年第四期)、舍木的《泛舟游》(《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張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館》(《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先志的《牙科診所內的占卜》(《上海文學》二○二四年第十二期)、穆薩的《獵人之死》(《收獲》二○二四年第四期)、岳舒的《闖入者》(《長江文藝》二○二四年第九期)等。《進化論》從一頭小香豬的視角展開,這頭豬有三個名字,伴隨三個名稱變化的是它從幸福寵物到流浪街頭再到成為種豬、淪為食物的“進化”的一生。作為一篇動物敘事之作,《進化論》與生態主題并無關系,作者大概受到王小波那篇著名雜文的影響,將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鋒芒內隱在豬的一生中,豬最終選擇一躍而起,寧愿死去也要表達對被設置的人生的拒絕,然而作為豬的主人的幾個人卻依舊困在森嚴的階層秩序里,兩相對照中的反諷是不言自明的。動物敘事無甚特別,但也的確通過隱曲的方式,提供了冷峻透徹地看待現實的窗口,揭開了人們習焉不察的常識世界之下的一種真相。舍木的《泛舟游》可能也受到王小波的影響。小說采用雙線敘事,一條線寫一個叫小陳的姑娘的職場之困,一條線用俚俗口吻敷衍鄭旦、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小陳與鄭旦由此成為對應的鏡像,她們試圖抗拒職場和使命對于個體那種體制化的壓制,卻又很難讓自己從中真正抽離。王小波式的“故事新編”不但讓小說內容擴容,也將戲謔的反諷帶入一個關于“規訓與懲罰”的現實主題之中。
如果說《泛舟游》是托言歷史來寫當下,那張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館》則是借徑未來以寫當下。《工作狂博物館》的背景設定于二○八○年,一位名叫申公雀的女性因為對工作和學習的狂熱而被放入博物館的透明玻璃柜中專門展藏,人們爭相購買申公雀的文創周邊,因為據說連她呼出的二氧化碳也能提升人的智力水平。作者在創作談中提及,這個小說源于她在校園內聽到一個女人“憤怒倔強還有點兒驕傲”的聲音,說自己“從小就想當工作狂”,于是作者“想象她會有怎樣的童年與家庭,但萍水相逢,她神秘莫測,我想不出來,小說展不開,后來我耐心耗盡,不想寫了,只想斥巨資給她造一座博物館”。作者的夫子自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青年作家如何規避閱歷不足的鮮活事例,也許在老輩作家筆下可能生長為一個自幼勤奮好學“積極生活”的人最終精疲力盡的故事,變成了博物館里令人啼笑皆非的裝置行為,變成了消費展覽品的狂歡。
先志的《牙科診所內的占卜》是直面當下的作品,小說用大量對話推進,這些對話基本省略了副詞和形容詞,情感節制,用語簡捷,其下自有豐饒,因為作者并不試圖通過對話給讀者提供更多信息,結合情節不同讀者對小說會有不同理解,這自然讓人想到海明威和卡佛。在主題上,《牙科診所內的占卜》同樣是一篇書寫疼痛的小說,它看似簡單,但其實堪稱一種以當下年輕人的生活和情感為內核的深層敘事。
《進化論》《泛舟游》《工作狂博物館》和《牙科診所內的占卜》在敘事上都體現了卡爾維諾所言的那種有意“減少故事結構和語言的沉重感”的輕逸。卡爾維諾說:“我開始寫作生涯之時,每個青年作家的誡命都是表現他們自己的時代……不久以后,我就意識到,本來可以成為我寫作素材的生活事實,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夠具有的那種明快輕松感之間,存在著一條我日益難以跨越的鴻溝。大概只有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難解;而這些特性,如果不設法避開,定將從一開始便牢固地膠結在作品中”(卡爾維諾:《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三十多年過去了,卡爾維諾談到的問題依然橫亙在青年寫作者心頭,表現時代的“誡命”永不過時,像一個會飛行的巫師那樣“機敏的驟然跳躍”是否就是當代青年寫作者回應這一“誡命”的方式,值得深入討論,其有效性也有待檢驗,但至少這提供了一種破壁的可能。
擴而言之,青年作家小說專輯也只是透視當下青年寫作的一扇窗口,上述的討論或許未必能構成真正的脈象,這些青年作家未來能走多遠也無從就這些小說下判語,但他們所體現的問題意識和試圖解困的努力需要更多同情之理解,他們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