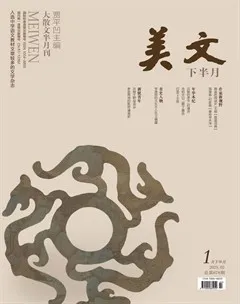海棠春
林壩子最好的海棠花開在秀珍家。
四月春是被天風吹來的,幾場雨過后,天風攜來高處的暖,林壩子冰凍的河面嘭地脆裂,那聲音驚動天地,震醒沉睡一冬的土地,萬物迅速復蘇,小燕子也匆匆趕回來,裝點林壩子空如錦緞的藍天。只消幾個日子的陽光普照和雨露滋養,秀珍院子的海棠花苞就舒展開來,薄如羽翼的花瓣露出嫩黃纖細的花蕊,在風里輕輕搖晃著。三五朵白花聚攏一處,把一根枝條擠得滿滿。花開得太盛,綠葉都被湮沒,遠遠看去,水桶那么粗的樹干上頂著一扇碩大的傘篷,那么白,白得像一場深冬遺留的雪,又像一大顆深海里沉睡的貝。還有那香清甜悠遠,讓人愿意久久地閉上眼。秀珍放在花下窗臺的筆記本夾頁里,就增了幾行詩句:“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我捂著肚子氣喘吁吁地從四一街跑上來,猛扣秀珍姐家門環。等她的時候,一樹的海棠花葉被盛大的天風撥動,沙沙啦啦,嗚嗚哇哇,像許多人吹起陶笛和竹簫的重奏曲。我正傾聽,秀珍姐端著洗衣盆,披一頭烏黑長發遠遠走來,她喊我:“二丫頭,你傻杵這干啥?”我回過神,才想起差點忘了最重要的事:“快走啊,秀珍姐,娃兒們都到學堂啦!”我拽著秀珍姐一路奔跑,跑過春天即將播種的干凈莊稼地,跑過小喇叭花正開的梧桐樹,跑到能望見熱熱鬧鬧的四一街。
明理學堂在雜貨鋪東隔壁的石頭房子開班了,名字是最有學問的莫老先生起的,寓意是:多讀書才能明曉道理,遇事才能分辨善惡真假,才好選擇自己要走的路,才能走得通達灑脫。辦學的經費由四一街上的商鋪按月出份子,商人喜歡做這種功在千秋的事情,都爽快地應諾下來。制木廠老板慷慨貢獻十六張紅桃木桌椅,箍桶匠專程去縣城搬回一桶白石灰,在黑黢黢的教室墻壁上刷出一方整整齊齊的白板,烙餅家火筒里燒紅的松木全做成了炭筆。林壩子的居民本來心生感激的,直到看到雜貨鋪的俏三娘用食指勾著幾條舊毛巾笑嘻嘻說:“恭賀明理學堂開張!”大家哼哼鼻子說:“商人嘛,還是重利嗇皮。”我真是看不慣俏三娘的小氣勁兒:“三娘,你該不會把你家抹腳布拿來了吧?”“臭二丫頭,又欠收拾了!”
明理學堂開張了。十六個學娃娃高高低低坐了一教室。秀珍姐站在講臺上說:“我是你們的老師,也是阿姐,叫我秀珍姐就行。”娃兒們笑著齊聲:“曉得!”秀珍姐轉身在白板上一筆一劃寫下“秦嶺”兩個大字,說:“秦嶺山大,橫跨陜甘,是黃河和長江的分水嶺,關中和陜南的分界線,古人稱作‘天下之大阻’。”娃兒們聽得目不轉睛,但也有些云里霧里。秀珍姐又在白板上寫下三個小字“林壩子”,說:“林壩子小,在秦嶺山南麓,寧安縣北部,蒲河經過,是我們生活的村莊。”娃兒問:“那秦嶺和林壩子到底啥關系?”回答說:“以門前大公雞為例,秦嶺是雞翅膀上最長的翼羽,林壩子是翼羽上一小根羽毛。”大概還是似懂非懂,但是從此娃兒們心里有了秦嶺、寧安、蒲河、林壩子這些名詞。
明理學堂沒有教學目標,當然也沒有學籍,更算不上正式的學歷。但是秀珍姐和娃兒們都熱情地教著學著。她教娃兒們唱歌,歌詞是:“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歌聲抑揚頓挫,緩慢幽然,能把人還原到許多年前的春天。秀珍姐嗓音真好聽啊,她把“問君”的“問”唱得繚繞回轉,好像真的要問一問才罷休,千愁萬恨就鋪展開來。孩子們甜甜的童音跟著唱起,四一街上的閑人都跑到學堂門口圍觀,三娘也跟著搖頭晃腦哼起來,她唱歌倒是比說話動聽多了。
四一街的商鋪每月按慣例湊份子,給秀珍姐發二十塊工資。秀珍姐挎著棉布袋去俏三娘的雜貨鋪買洗衣皂、雪花膏和好看的筆記本。鋪里有時剛進了新貨,貨架上擺著亮珠吊墜的翻花硬皮本,自帶時髦的小鎖和鑰匙,秀珍姐寶貝似的捧在手心,再配一支新的天藍色碳水筆。有時俏三娘也會把滯銷很久的黑皮本賣給她,我站在門口喊:“秀珍姐,快莫買了,這本子長得比鍋底還難看!”俏三娘扔一把水果糖過來,我接住幾顆就往外跑,臨走不忘再喊一聲:“千萬莫買啊!”秀珍姐仍舊會買,不管什么樣子,她喜歡紙和筆。
倘若還有余錢,買三兩青紅絲,二斤糯米面,一斤小麥粉,半斤白糖和紅糖,放在棉布袋里提回家做海棠糕。五月初的海棠樹,花在樹上開一半,地上落一半。明理學堂的娃們正好一片一片撿起來,放入樹下石桌上的竹籃。秀珍姐在灶房燒好柴火,用發酵了一夜的糯米小麥面做花瓣形的糕,青紅絲做蕊,一蒸屜出鍋,娃們一看,真像極了海棠花。秀珍姐用竹夾一塊塊擱到大藍釉瓷盤里,再把洗干凈滾動著水珠的海棠花瓣裝點在旁邊,左看右看都是最好看的!娃們蘸著紅白糖、蜂蜜、核桃碎、花生醬吃得津津有味。有海棠糕吃的春天才叫春天啊!
松林哥出現在明理學堂,大概是第二年春天。他正好初中畢業在家待業,恰逢四方鎮政府下了文件,將明理學堂納入義務教育階段。村委會聘請松林哥到明理學堂正式教課,每個月發四十塊錢工資。得了官方的文件,明理學堂才更像個學堂的樣子,門口刷上兩行鮮紅標語“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村委會把黑板安裝到墻上,又配了紅黃藍綠白五色粉筆。最重要的是,老師和娃們人手終于有了課本,松林哥照著教科書正兒八經教起拼音、寫字和算術來。
秀珍姐呢,也在學堂里繼續教唱歌和手工。這樣搭配起來,明理學堂有了完整的教學體系,大人和娃們都十分滿意。但偶爾也有波瀾,教學理念和方法不同,兩位老師難免起口角爭執,秀珍姐上完課就帶娃們去門口的空地玩,但松林哥一定要娃娃把生字都抄完,兩人在教室門口就吵起來。“不要以為你念完初中就了不起!”秀珍姐先發制人了。“學校就要有學校的制度,學習就該有學習的樣子。”“什么制度?什么樣子?只有你當得了老師?”松林哥讓娃們放學,留下秀珍姐聊了很久,直到月亮升到中天,他才送她到海棠樹下,她進屋后,他聞著海棠花的濃香良久未歸。
聽說這次吵架后,松林哥專門托人從四方鎮商場買回一條繡著玫瑰花的粉紗巾。紗巾送誰了呢?秋天的時候,秀珍姐脖上系了條一模一樣的。上課也有了變化,松林哥在語文課教王維的詩:“遠看山有色,靜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秀珍姐教唱歌,歌曲也成了這首詩,歌聲里多了些娃們唱不出懂不了的柔情,但是一唱一和依然婉轉美妙。而且明理學堂的規矩也立起來了,每天晨讀一小時以上,飯前要背詩,寫完作業才能出去玩,我在明理學堂真是學到了許多受益一生的好習慣。
第三年春天如期而至,海棠花又開得活潑燦爛,但是明理學堂遇到新的危機。為保障教學質量,整合教育資源,全國性取締偏遠鄉村小規模學校的政策文件下發到林壩子。受計劃生育影響,明理學堂的娃們只有自然流失的,沒有增長的,辦學規模愈發小了,村委會打報告給鎮政府說林壩子山高水遠,孩子們上學著實不便,能不能酌情保留學堂。但政策如鐵,最終還是按政策辦了,學堂學生全部編入清灣小學三年級班級,辦了整整三年的明理學堂就這樣落下帷幕。四一街人多有不舍,一直保留著明理學堂的教室,鑰匙存放在俏三娘那,她還跟以前一樣經常趴到窗口往里望。
明理學堂停辦以后,秀珍姐好些天沒到四一街來。我去她家看她
的時候,吹過海棠的風正翻動她窗臺上的筆記本,上面又多了兩行纖細秀麗的字跡“自今意思和誰說,一片春心付海棠”……我還清楚記得明理學堂開學那天,我跑到海棠花下等秀珍姐的情形,那天的天,多空多藍啊,像一張無限純粹的冰絲綢緞。我還記得海棠花白如雪,盛大美觀像一場夢幻,時間過得真快,三年一晃而過,我并沒有跟其他人去清灣小學,我覺得林壩子還有我未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