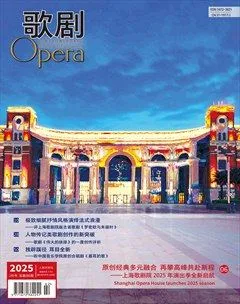極致細膩抒情風格演繹法式浪漫
中法文化之春——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 2024年12月30日晚,由上海歌劇院院長、著名指揮家、鋼琴家許忠執棒,上海歌劇院聯袂巴黎管弦樂團、巴黎愛樂大廳的十六位首席演奏家以及來自法國、西班牙的多位歌唱家共同合作的法國作曲家夏爾·古諾的五幕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半舞臺版),在上海大劇院隆重獻演,為觀眾奉獻了一場久久難忘的音樂饕餮盛宴。


雖說古諾的這部歌劇并非當下最熱門的劇目,但是從現場幾近滿座的上座率,仍能欣喜地看到申城觀眾所具備的頗高欣賞水平,以及歌劇愛好者們對這部歌劇的熱切期待。對于法國作曲家古諾,大部分音樂愛好者是通過他那首天衣無縫匹配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首前奏曲的《圣母頌》,才熟識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偉大作曲家。由此可見,古諾對于旋律的精深而獨到的創意,也是他在西方音樂史上躋身于偉大作曲家行列無可爭議的緣由。
同樣,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另一部《浮士德》,均是古諾留給西方歌劇史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古諾通過眾多精彩絕倫的詠嘆調和管弦樂細致入微的描繪性段落,將羅密歐與朱麗葉至死不渝、忠貞不屈和極致浪漫唯美的愛情,展現得深刻雋永又感人至深。弦樂細膩豐富的表現能力在這部歌劇中充分得以施展,木管及銅管的豐富色彩更增添了歌劇本身的戲劇性張力。同時,合唱在戲劇中作為評論、敘述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屢次在關鍵時刻推動戲劇發展。當晚的演出,無論是舞臺的精美設計和恰到好處的空間布局層次,還是藝術家們精彩絕倫的現場表演,均堪稱完美,令人不禁嘖嘖稱贊。

啟幕后,震撼的舞臺一目了然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充分彰顯了舞美設計上多維空間的縱深感。同時,虛實結合的舞臺布景,也毫不費勁地成就了視覺上的絢麗多姿。在這部半舞臺版的歌劇中,原本在樂池中放置的交響樂團被調整至舞臺中央,兩側則是弧形的樓梯,連接樂隊上方高處的走廊,使舞臺空間形成高區、中區、低區的多層結構,有效延展了舞臺空間,為舞臺整體更增添了錯落有致、縱橫交錯的層次性,也著實增強了在物理空間上舞臺聲音傳達的豐富性。舞臺兩側的弧形樓梯,除了用作戲劇動作表演的區域外,還成為合唱團固定的表演區域,也由此形成了合唱高、低聲區的空間變化,給合唱的整體聲音表達更增添了飽滿的表現力。此外,在舞臺的臺口處,還有最重要的舞臺布景——陽臺。陽臺的設計有意思的是,通過光影的反射效果,將陽臺內房間里的一系列戲劇動作,投射到另一側臺口的圍墻布景上,延伸了舞臺的表現空間,同時,還通過光影效果,將陽臺后羅密歐在夜幕下攀爬陽臺的場景生動地加以表現。虛實結合的舞臺設計還不僅體現于此,本部歌劇的舞美設計,使用了電子屏幕來切換不同的戲劇場景,在虛實結合、動靜結合中,實現了靈活多變的舞臺場景切換和調度,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一部典型的法國抒情歌劇,該劇最感人至深之處,來自作曲家夏爾·古諾對音樂的嫻熟駕馭能力和音樂戲劇的精準拿捏,通過調動序曲、詠嘆調、管弦樂、合唱、重唱等各種音樂手段和形式所詮釋的極致細膩抒情的歌劇風格。無論在歌劇創作還是藝術歌曲、宗教作品中,古諾都表現出獨特的個性,尤其是他創作的旋律通常迷人且高貴,精致細膩的和聲、華麗豐富的配器,展現出他極高的音樂天賦。同時,作為法國浪漫主義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遵循了浪漫主義的主要音樂特色,熱衷于聲音、樂器、調性、和聲的精細化處理和色彩的豐富變化,賦予作品夢幻般的想象力,在唯美的抒情性中創造每一個戲劇情感的“音樂瞬間”,強調人聲和器樂中“天鵝絨般”絲滑、流暢、輕盈的迷人音色,即便是在戲劇性矛盾的音樂展現中,也賦予深刻的藝術性處理和充分的浪漫主義色彩,而絕非粗野狂暴的音響。不是音樂材料之間的激烈搏斗和猛烈沖撞,而是在寬廣綿延的音樂展開過程中,呈現因有節制的音樂對比而產生的張力和緊張感。

在莎士比亞的眾多劇目中,《羅密歐與朱麗葉》是最有影響力的傳世名作,深受民眾喜愛,因此也被改編為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劇中兩個家族之間不可調和的家族矛盾,導致兩個相愛的年輕人注定承受不可避免的悲劇性結局。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古諾用一種無限洞察力、幻想力,以及美妙、精致、溫柔的音樂語言,喚起的純粹而無限美好的愛戀之情,并將其以莫扎特式的明亮單純與舒曼音樂中敏感細膩不安的詩性語言完美結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詩性作品。這部歌劇的亮點,不在于激情或情緒化的嘩眾取寵,而是由精致的管弦樂色調和柔美溫和的眾多半音階式的旋律所產生的由心底升騰的無盡溫柔,以及弦樂部分深邃極致的綿延悠長旋律所帶來的夢境般的愛情想象,為世人呈現出愛情最真切的永恒美。在眾多表現浪漫愛情和充沛情感的戲劇段落中,古諾將美麗且富有情致的旋律發揮到了極致,也成就了眾多曼妙、充滿活力和優雅氣質的詠嘆調,充分施展了作曲家超凡的獨創性和音樂能力。

序曲段落中,樂隊一開場就演繹了戲劇矛盾沖突的段落。恢宏的銅管帶入戲劇緊張的氣氛,令人為之一振。緊接著弦樂的各個聲部快速而激烈地穿插在賦格的段落中,最終推向由銅管引導的高潮部分。之后,合唱以令人無比傷感惋惜的旋律,評論這對彼此相愛的戀人不幸的一生,感人至深。弦樂也同時奏出如泣如訴、無比柔美的抒情性段落。從中可以看到,古諾的管弦樂配器技術極為嫻熟,致使這一段充分濃縮并綜合了歌劇中的戲劇沖突和唯美精致的浪漫主義旋律。在合唱虔誠動人的旋律中唱出朱麗葉那無與倫比的美麗動人時,主人公便踏著輕盈靈巧的步伐,閃耀地綻放在舞臺中央,以單純、自信的姿態,展現對生活充滿期待的美好愿景。伴隨著朱麗葉而歡騰的舞曲音樂,也生動形象地襯托了這原本美好的一切。當羅密歐第一次見到朱麗葉時,瞬間便為她著迷,唱出一曲愛情詠嘆調,宣泄其純正的法式浪漫情懷,讓觀眾一同沉醉在人類最美好的愛情之中。作為愛情的回應,朱麗葉唱出了著名詠嘆調“我愿生活在美夢中”(Je veux vivre Dans ce rêve),用激動的心情表達了自己對美好愛情的向往。靈巧的花腔唱出抒情的曼妙旋律,音樂中又略帶忐忑的心情。頻繁的離調、轉調和半音化的旋律,使原本大調的調性變得模糊,最后連續的模進旋律,將旋律推向華麗的花腔旋律的高音,在激情和奔放中,展現了朱麗葉勇敢奔赴愛情的堅定決心。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第一次二重唱,音樂中的旋律帶著對愛情和對方的渴望而產生的激情,也有彼此間情感控制所流露的溫存和小心翼翼。旋律中的輕盈溫柔與熾熱激情形成了情緒上和音樂材料上的對比,更增添了兩人之間情感的濃度,也為后續悲劇性的結局做了鋪墊。
第二幕序曲是古諾音樂風格和個人氣質的集中體現。夢幻曲般的旋律和恰如其分的轉調令人如癡如醉,充分展現了他作品中獨特而出眾的溫柔、夢幻和豐腴的情感,這些精致優美的旋律和富有表現力的配器,以及樂器之間的默契與配合,成功地傳達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真切而復雜的情感。這一幕中(同時也是全劇中)最感人至深的段落,莫過于陽臺約會的美好愛戀了。管弦樂與人聲交織在一起,在羅密歐一次次熱切的呼喚中,模進式的音樂跌宕起伏,以按捺不住的激動心情,將劇情推向高潮。同樣的詩情篇章出現在第四幕的序曲,古諾將難以名狀的苦楚和至純至真的詩意相結合,用悲情式綿延悠長的旋律,在弦樂聲部的推動中,成為戲劇悲劇性情感的催化劑。第三幕是本劇戲劇結構和情緒的轉折點,兩個家族間的沖突在此集中爆發,戲劇性矛盾在這里達到了高點,同時也預示著整部歌劇無可回避的悲劇性結局。如果說前兩幕的戲劇情節和戲劇色彩是甜蜜而明快的,那么在經歷第三幕的戲劇沖突后,第四幕和第五幕就急轉而下,集中呈現出悲劇性的憂傷且陰郁的戲劇色彩。




從第四幕開始,音樂集中表達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焦慮、憂愁、恐懼、猶豫、糾結、憐惜和相互依戀、疼愛、不舍的復雜情感,頻繁轉調甚至遠關系調性的變換加劇,半音化的和聲與多變的音樂織體也隨之越來越復雜,不協和和弦的頻繁使用、減七和弦的模進等音樂推進方式,也使整部戲劇的戲劇氛圍更為陰森可怖。羅密歐與朱麗葉兩人的重唱段落里,連續下行的旋律,表現出兩人的無助和憂傷。音樂伴隨著兩人之間糾結、猶豫的情感糾纏,不斷呈現迂回、糾葛、纏繞和各種反復的情感推進的狀態,表現了音樂進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最終在不可抑制的強烈愛戀的強有力的推動下,在去留問題的糾結猶豫之間,羅密歐的愛戀之情沖破了一切,以赴死的決心將情感濃度推向最高潮。隨著劇情的推進,家族的仇恨持續演變,朱麗葉最終找到神父,希望幫助她擺脫困境。在神父給出的“毒藥”面前,朱麗葉的情緒繼續在生死中糾結,最終,在著名的“毒藥詠嘆調”中,唱出了她為了愛情沖破一切桎梏,沖破一切家族的仇恨,直至沖破生死的藩籬,為自己的摯愛勇敢地將毒藥一飲而盡,在音樂強有力的高音中,將堅韌不屈的為愛執著的品質展現得至高至上,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第五幕序曲,似乎是一曲為愛低吟的挽歌,唱出了整部戲劇悲劇性的哀怨惆悵的旋律。在這一幕中,最精彩的戲劇性情節,莫過于當羅密歐發現朱麗葉時,誤以為她已經身亡,悲痛下將真毒藥一飲而盡。羅密歐服毒后,朱麗葉慢慢蘇醒,當羅密歐看到朱麗葉生還,當朱麗葉也看到眼前的羅密歐時,二人欣喜若狂,暢想遠走高飛的幸福生活。然而,隨著羅密歐的毒藥發作,這對苦命鴛鴦痛苦的悲劇結局最終還是來臨了。最終,在悲痛欲絕中,兩人雙雙奔赴黃泉,演繹了悲劇性的升華“愛之死”的感人段落。悲傷的旋律在管弦樂的襯托之下,追憶往昔美好時光,也對死亡充滿恐懼。整段戲劇情節和音樂峰回路轉,跌宕起伏,可謂“到底不懈之筆”,無論從音樂的角度還是從戲劇的觀賞性而言,都是最精彩的戲劇收尾,給人以無盡的感慨和唏噓。觀眾最后的熱烈掌聲和激動的呼喊,也正是對這部劇成功上演最好的現場反饋。
由許忠執棒、張慶新執導的這一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無論在舞臺聽覺還是音樂聽覺上,都給人以絕美驚艷的感覺。這部歌劇的呈現,最考驗演員功力的地方,在于戲劇音樂和情感的變化過程,伴隨著迂回曲折的復雜戲劇情節和動作展開,如何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地表現,通過全劇中層次豐富的音樂和舞臺的各個要素,綜合性地將細膩多變的戲劇情感和跌宕起伏的戲劇矛盾發展過程,以最雋永最動人的方式傳遞給觀眾。本場演出中,無論是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與巴黎愛樂大廳、巴黎管弦樂團的16位首席演奏家們共同呈現的管弦樂部分,還是中外優秀的歌劇演員們與上海歌劇院合唱團的唱演部分,都全情投入,以嫻熟精湛的音樂表現技術,富有深度地表現戲劇人物心理和情感狀態,以最深刻細膩的方式,展現了歌劇的藝術形象,管弦樂演奏、獨唱、重唱、合唱,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
除了音樂展現之外,舞臺設計和視覺呈現也具有很強的觀賞美感。舞臺設計搭配燈光設計,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進行了諸多巧妙的光影設計和色彩分區,使舞臺充滿了奇幻的變化和層出不窮的視覺沖擊力。其中,光影的反射效果,以及用紅色的燈光所表征的殺戮和鮮血,都恰到好處地推進了戲劇矛盾展開。舞蹈場面融入歌劇是法國抒情歌劇歷來的傳統,華麗的舞蹈增添了視覺的觀感,成為歌劇舞臺上的一抹靚麗色彩,也渲染了舞會上優雅、祥和、歡樂的戲劇氛圍。
在音樂的表達上,指揮家許忠將管弦樂的聲音調配得極具感染力,在戲劇人物的內在動作和情感的描繪、戲劇情境的鋪陳和推進戲劇關鍵情節的發展上,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在多個場景音樂和序曲段落中,弦樂部分對于聲音的控制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貫且富于變化的弦樂運弓,使整個弦樂聲部具有了天鵝絨般絲滑綿醇的聲音,柔美酣暢的音色凸顯了整部歌劇高貴、典雅、圣潔、純真的氣質,將古諾的音樂抒情細膩的美感,通過管弦樂和人聲的演繹,到達了近乎完美的境地,讓人聽罷如癡如醉。銅管和木管的音色,也如弦樂一般柔美絲滑,沒有一絲生硬和矯揉造作,恰到好處地映射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兩位主角的形象與氣質。尤其在陽臺約會的場景中,管弦樂的演奏鋪墊了兩人無比真摯純潔炙熱的愛戀,弦樂部分的整體音色和控制力,以及悠長綿延的長氣息的旋律之下,連貫的聲音表現堪稱完美演繹。每件樂器在指揮的調度之下,都盡顯其獨特的音色和出眾的音樂表現力,形成一幅細膩抒情又龐大奔流的音樂畫卷,展現出極其細致考究的豐富音樂層次和情感深度,充滿了對戲劇情感的深度詮釋,更體現了演奏家們精湛卓越的演奏實力。
歌劇中,演繹朱麗葉的女高音萊昂諾爾·博尼利亞(Leonor Bonilla)和飾演羅密歐的男高音托馬斯·貝廷格(Thomas Bettinger)均是非常出色的歌劇演員。萊昂諾爾·博尼利亞是一位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出生于塞維利亞,以其卓越的演唱技巧和舞臺表現享譽國際歌劇界。托馬斯·貝廷格則是一位法國男高音。兩人都有著迷人的純正柔美音色和悠長的氣息,成功地演繹了劇中綿延的旋律。托馬斯·貝廷格多次在高音上的高難度的弱音處理,細若游絲,展現出對聲音精準的控制力。盡管他們的音量和聲音的張力,不同于瓦格納歌劇演員那般寬厚強勁的音高幅度,也非充滿爆發力和戲劇張力的聲音類型,但是他們的表現近乎完美地呈現了歌劇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延續的基本原則:詩意的語言,自然的歌唱。他們將法國浪漫主義抒情歌劇所特有的旋律美感、抒情細膩的表現力和情感的深度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那一晚,他們優美如歌的聲音在上海大劇院大劇場內自由飄揚翱翔,富有穿透力和美感,更賦予了戲劇深刻的情感內涵和豐富的層次感。其他歌劇演員的表現力也是可圈可點,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整部歌劇中,角色演員們的聲音搭配平衡,整體音色統一,空間感和層次性表現得深入人心,同時也充分具有歌劇的說服力。

作為法國抒情歌劇的典型特征,劇中合唱的戲份很足,在敘述情節發展、評論劇中人物以及推進戲劇矛盾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歌劇院合唱團作為成熟的高水平合唱團,運用合唱中多變的聲部展開,以及細膩的合唱處理,形成人聲豐富的表現力。在劇中,合唱常常作為戲劇氛圍的先導,營造出與戲劇情境相匹配的特定氛圍。全劇的序曲之后,合唱就以沉重而凝重的語氣,介紹兩個長期不和的望族之間,命中注定是一場血雨腥風中生死存亡的爭斗。在暴風雨中的一縷陽光,將最終結束兩個家族的仇恨。可以說,開場的這一段合唱,已經為整部劇的戲劇情境和色彩進行了鋪墊,當中有仇恨、有爭斗,也有溫暖和純情。隨后,在第一幕假面舞會開始的過程中,經過合唱的渲染,充分表現了舞會場面上熱鬧非凡,無比歡樂的戲劇場景。在管弦樂的配合之下,這種轉換靈活而恰到好處,共同創造了充滿戲劇性的場面。在第三幕羅密歐為了朋友刺殺了提拔特。羅密歐此時復雜的內心已經驚慌失措,合唱隨即唱響哀怨的唱段,用悲哀的語氣唱出了年輕人意氣用事,用失去理性的狂怒,沾染了悲劇性的鮮血下場,評述了這一場慘烈的戲劇矛盾。最后在半音階上行的旋律中,將戲劇情感推向高潮,之后連接公爵入場的段落。當公爵宣布不公平的處置辦法后,羅密歐失望至極,此時,合唱團又唱出了述評式的合唱,并在不公正的控訴中,將音樂推向又一個新的戲劇高潮。在幾次歌劇最重要的戲劇性轉折的過程中,合唱都發揮了重要的連接作用。
近幾年來,我欣喜地看到,上海歌劇院通過與眾多國際知名歌劇院和中外優秀的歌劇藝術名家合作的經歷,無論從選劇品位、演唱能力、演奏能力,還是表演水平、舞臺設計上看,都已邁向世界一流水平,形成了獨特的歌劇審美品格,也提高了申城觀眾的欣賞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從經典劇目的選擇上,上海歌劇院已經不再拘泥于耳熟能詳的詠嘆調所涵蓋的熱門劇目,而逐漸轉向更具有戲劇內涵、思想深度的作品,音樂也更趨于多變而復雜。對于觀眾而言,歌劇劇目的欣賞門檻更高,更需要藝術品位和修為,才能從中體味劇中人物內心動作的刻畫,領悟跌宕起伏的戲劇情節中,所展現的細膩、復雜、多變的戲劇情感,從而感受歌劇所帶來的對人物命運終極思考,積極對世界重新認知。這也體現了上海歌劇院在生產藝術產品、創造藝術價值的時候,所秉持的一份難得的文化堅守與文化自信。
(吳佳,上海音樂學院副研究員)
[本文為2024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新時代中國歌曲創作研究(項目負責人:安棟,項目編號:24BD08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為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器樂藝術研究”(項目負責人:劉英,項目編號:21ZD2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