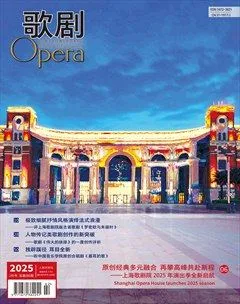宿敵抑或知己

林茨國家劇院(Das Landestheater Linz)的音樂劇作品《女王》(Die K?niginnen)首演于2024年2月10日,并于10月在2024年德國音樂劇獎的評選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最佳音樂劇”的桂冠,其主演亞歷山德拉-尤阿娜·亞歷山德羅娃(Alexandra-Yoana Alexandrova)更是憑借精湛演技和唱功榮獲“最佳女主角獎”。劇情的序幕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決絕簽署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死刑令的震撼瞬間緩緩拉開,一場波瀾壯闊的女性史詩對決,就此上演。
生而為敵:王權之路的宿命
兩位女王由于宗教信仰和國家利益的糾葛,注定成為彼此的宿敵。雙方敵對的命運在法國國王鼓勵瑪麗女王爭奪英國王位之時便已開啟。兩位女王在劇中多次交鋒,如伊麗莎白女王希望瑪麗女王嫁給自己的情人和寵臣萊斯特伯爵,從而控制蘇格蘭;而瑪麗女王順從自己心意嫁給達恩利勛爵,繼續對伊麗莎白女王發起挑戰。瑪麗女王流亡英格蘭后,成為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伊麗莎白女王為了國家安全將她軟禁。在瑪麗女王之子詹姆斯臣服于伊麗莎白女王之后,瑪麗聯合天主教教徒策劃暗殺伊麗莎白,卻被伊麗莎白的重臣塞西爾誘導留下證據,最終走向了斷頭臺。

這部劇涉及數十年歷史變遷,巧妙運用時空并置手法,讓這兩位歷史上從未謀面的宿敵在舞臺上展開交流。舞臺兩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風云變幻同時上演,立體的道具墻通過旋轉變換場景。這一手法不僅極大地拓展了故事的深度與廣度,更超越了傳統敘事的框架。劇中瑪麗女王在死刑前回顧一生,審視來自伊麗莎白女王的或真或假的評價。伊麗莎白時而在一旁冷嘲熱諷,時而與瑪麗溫情對話,打破時空界限,營造出一種強烈的真實感。她們經常借助信件這一媒介進行互動,呼應歷史上兩人的書信往來。兩位女王有時甚至跳出劇中角色,評價自己或其他角色的行為。時空并置也凸顯了兩位女王及其盟友的對抗,比如瑪麗女王祈求天主教力量的援手時,其盟友扶著巨型十字架出現在她的身后,彰顯磅礴之勢。而瑪麗女王的親生兒子詹姆斯長大成人后向伊麗莎白俯首稱臣,將母親的來信揉成一團,任其滾落到囚禁中的瑪麗足畔,訴說著權力的更迭與親情的斷裂。

從服裝到音樂,舞臺也以多種方式展現了她們的對立與沖突。瑪麗在法國時的銀灰連衣裙洋溢著青春活力,返回蘇格蘭后的黑色長裙象征她的孤獨,而被處決時的紅色長裙則是對她悲劇命運的最終注解。伊麗莎白的服裝則從帶有柔和金色光澤的紗裙轉換為泛著冷光的金屬方塊長裙,臉上也涂抹了一層厚厚的白粉,掩蓋了她的真實情感,表明她已成為國家機器的“異化”象征。瑪麗之子詹姆斯國王也身穿和伊麗莎白同樣質地的金屬色制服,表示他與伊麗莎白的利益一致,暗示權力的傳承,同時表明他站到了瑪麗的對立面。

音樂和演唱風格也體現出兩位女王不同的性格特點。瑪麗女王一直籠罩在熾熱的愛和激情當中,她多情而嫵媚,對男性頗具吸引力,充滿自然的情感流露,善于用漂亮的音色表達情感,無論是興奮、痛苦還是恐懼,不留斧鑿痕跡。她的聲音高亢直穿云霄,充滿了生命力和感染力。與之相比,伊麗莎白女王則是復雜的多面體,展現了從初登場的小心謹慎到政治博弈中的假意真情。演員以精湛的演技與獨特的唱腔,將她的內心世界刻畫得淋漓盡致。她的歌聲帶著些許戲謔與停頓,有一些刻意突出并拉長的重音,她本人仿佛是在權力游戲中游刃有余的舞者。配樂的節奏感強烈,有些段落輕盈歡快,有些則堅定有力。兩位女王的旋律也會發生碰撞。瑪麗在法國宮廷時期的音樂充滿了靈動優美的旋律,折射出她年少時幸福和驕傲的心境。她翩翩起舞,熱情如火,聲音猶如銀鈴般悅耳清脆、勾人心魄。伊麗莎白則在一旁以警醒與嘲諷的旋律切入,如同歷史的旁觀者,提醒她當心盛極而衰。而每次伊麗莎白與塞西爾商討國事時,這段旋律都會重現。在伊麗莎白決定對付瑪麗之時,她心緒不定、矛盾萬分,聲樂與戲劇性的表達完美融合,將女王內心掙扎與痛苦表達得淋漓盡致,令人嘆為觀止。歷史上伊麗莎白在下令處決瑪麗時,一度猶豫不決,這不僅出于對瑪麗的復雜情感,更源于對“君權神授”理念的深刻敬畏。在她看來,剝奪另一位女王的生命,無異于撼動自己統治的神圣根基。而劇中這一決定被賦予了更宏大的意義——為了英國的安寧與民眾的福祉。
惺惺相惜:女性命運的共鳴
該劇不僅展現了兩位女王作為宿敵的對抗,更深刻揭示了她們身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與共鳴。劇中有一首歌專門體現了男性對女性統治者的偏見,靈感來自約翰·諾克斯的《反對女性統治的第一聲號角》。諾克斯宣稱:“女人凌駕于男人之上,獨攬國家大權,有違自然規律。”伴隨著激昂的號角聲,蘇格蘭與英格蘭的男性朝臣一起合唱,從宗教、生理等各個方面尋找理由反對女性統治,還通過傾斜扭曲的肢體動作,展現出對所謂女性君主的壓迫的反抗與掙扎。這一幕不禁讓人想起幾個世紀后英國女性選舉權受阻的場面,一種歷史的延續感油然而生,讓觀眾感受到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面對不馴服的大臣,兩位女王異口同聲地宣告:“我統治著這個國家。”

兩位女王都面臨著婚姻與繼承權的難題,都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瑪麗女王從小被法國國王亨利二世視為可愛的傻瓜。重返蘇格蘭后,又在宮廷的陰謀與斗爭的漩渦中艱難求生,同父異母的弟弟莫里伯爵對她的王權虎視眈眈。約翰·諾克斯始終是她無法爭取的敵對陣營。瑪麗女王結過三次婚,除第一次婚姻將她送上人生巔峰之外,另外兩次都給她帶來無盡的痛苦。第二任丈夫達恩利愚蠢自大,想要分享王權,后離奇死亡。第三任丈夫博斯韋爾初登場時猶如英勇的騎士,最終也暴露了對王冠的野心。第三段婚禮的旋律也是第一段婚禮歌曲的扭曲變奏,寓意情感的變遷并諷刺博斯韋爾的真實面目。瑪麗女王流亡英格蘭后,莫里伯爵親自上陣,在英國陪審團面前控訴她的殺夫之罪,并以真假聲切換演繹了瑪麗出軌博斯韋爾的丑聞。瑪麗的兒子詹姆斯面對母親的來信求救則化身為冷酷君主,冰冷低沉的聲線表現其無情本質。他臺詞冷峻,隱含殺機,將母親視為自己稱王道路上的絆腳石。瑪麗女王面臨臣下的威脅與親生子的冷酷,展現了女性統治者的艱難與孤獨。劇中多處人聲吟唱也烘托了瑪麗身為女王的艱難處境。達恩利離奇慘死之時,身穿白色睡衣的眾人合唱傳達了民眾的疑惑、不滿、不安和指責,“兇手”“蕩婦”等字眼以極其現代化的標語方式出現在舞臺投影上。在瑪麗女王收到死刑通知之時,她生命中的角色紛紛登場,猶如幽靈般喚著她的名字,仿佛命運對她的召喚。瑪麗女王走上斷頭臺時,這一悲傷的場景卻選用了激昂的音樂,重現了她第一段婚禮時登上人生頂峰時的音樂,也使這一不幸結局浪漫化了,表現了創作者對她的同情。當然劇中的闡釋美化了瑪麗女王的形象,讓野心勃勃的博斯韋爾主要承擔殺害達恩利的罪責,并且還暗示英國大臣在這一事件背后的推動作用。而歷史中對于達恩利的死亡之謎雖沒有定論,基本認為瑪麗女王即使沒有參與,也至少默許了博斯韋爾的行為。

而伊麗莎白女王在童年時期就經歷了母親被父親送上斷頭臺的恐怖事件,她如履薄冰,努力鞏固自己的王權,宣布終身不嫁,將一生奉獻給國家。塞西爾起初對伊麗莎白的執政能力半信半疑,也加入了“反對女性統治”的合唱。但在女王展示了治國之才之后,他表示了臣服。但即便忠實如塞西爾,也會一再追問伊麗莎白的聯姻事宜,要求她盡早誕下繼承人,以應對瑪麗的威脅。伊麗莎白早在登基之時就宣布要保持單身,猶如現代的不婚主義者。為烘托其獨立精神,她的情人萊斯特伯爵被塑造成一個只會捧著巧克力說漂亮話的寵臣。在這段關系中,伊麗莎白明顯占據上風,她將婚姻視為政治籌碼。女性特質與女王身份難以兼容,伊麗莎白冷靜理智,有時也會摻雜一些夸張戲謔的動作,看透了政治游戲。不過舞臺并未將其塑造成冷酷無情的女人,而是賦予了一絲人性化的解讀。劇中仍然表現出她對母親身份偶爾流露的渴望之情。一處是瑪麗生子后邀請她做教母,她對“孩子”這個概念表現了矛盾的情感;另一處是她意識到詹姆斯會服從她時,告訴塞西爾英國終于有了繼承人,既有釋然,又有感慨。
兩位女王某些時刻的惺惺相惜通過音樂加以渲染,比如達恩利被殺后,瑪麗女王依然維護最大的嫌疑人博思韋爾,自己卻深陷丑聞和懷疑的漩渦。伊麗莎白女王對瑪麗女王表示了同情。兩人的重唱中提到女王的孤獨和脆弱,她們只要行差踏錯一步,就會陷入深淵。“親愛的表親”這一旋律的演變則捕捉了兩位女王關系的微妙起伏,瑪麗重返蘇格蘭后,兩人經歷了一段政治友誼的“蜜月期”,曲調線條悠揚而舒緩,如同春日里的暖陽,散發著和諧與喜悅的光輝。后來瑪麗女王流亡至英格蘭,這段旋律再次響起,表明她期待伊麗莎白女王的友好態度。而伊麗莎白采納塞西爾的計策寫信誘使瑪麗步入審判之時,這段旋律再度響起,塞西爾親自演繹這段旋律,其音色和音質與詠嘆調的美聲有些類似,用一種近乎歌劇般的莊重方式唱出這首歌,更顯諷刺意味。這段旋律最終也融入了兩位女王在舞臺上的和解片段。

歷史上的瑪麗女王以自己的慷慨赴死作為對伊麗莎白女王的最后一擊,而舞臺則將瑪麗女王悲劇性的結局歸咎為男性主導社會的壓力。她們最終的隔空和解是舞臺創作的浪漫化手法。兩人在抒情的旋律中道別,留下了無盡的遐想與感動。“‘女王’這個詞意味著什么?”“在男人主導的世界里,為什么女人要謀殺女人?”她們雖因宗教與國家繼承權之爭注定成為對手,但這一和解仿佛表達了一種超越恩怨的女性共鳴,詮釋了女性命運的無奈與抗爭。
音樂劇《女王》以浪漫化的筆觸將兩位女王之間的政治沖突升華為對女性命運共同體的深刻探討。它讓觀眾感受到那份跨越時空的共鳴與力量,以及對權力、愛情與責任的深度剖析。兩位女王面對重重挑戰與困境,以非凡的勇氣與智慧書寫著屬于自己的傳奇。她們的故事不僅折射出數百年前女性的生存困境,更是對當下社會的一種啟示與反思,讓觀眾在欣賞的同時思考女性的命運與未來。

(程夢雷,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碩士;邵舟娜,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