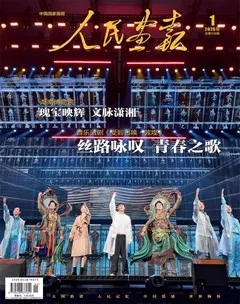對話何世堯:我是《人民畫報》“小記者”

90歲高齡的何世堯身體硬朗、精神矍鑠,人民畫報社年輕后輩皆視其為楷模。而當年,他也是人民畫報社意氣風發的少年郎。那段時間里,他跟隨攝影大師敖恩洪學習攝影,獨自赴西藏采訪,拍攝經典之作《巍巍長城》,完成120余組專題攝影報道……這些都成為令他難以忘懷的人生華彩。至今,何世堯仍這樣介紹自己:我是《人民畫報》“小記者”。
在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攝影)頒授之前,何世堯接受了《人民畫報》的專訪。
《人民畫報》:從創刊至今超過74年,《人民畫報》已經連續出版9 0 0多期。是怎樣的機緣,促使您來到人民畫報社開啟職業生涯?
何世堯:《人民畫報》創刊于1950年7月,我在1952年11月成為其中的一員。那時畫報尚處初創階段,僅出版了20多期。
高中快要畢業時,有一天班主任來找我,問我:“小何,愿意去北京嗎?”我立刻回答:“當然愿意!”那時的《人民畫報》要培養一批年輕記者,從上海選了10名高中生入社培訓,其中就有我。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有8名同學返回報考大學,我和另一名小記者鄧永慶被留了下來。就是這么一個偶然的機會,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成為攝影記者。對我來講,沒有《人民畫報》,就沒有我這個小記者。
來到人民畫報社之前,我對攝影的了解幾乎是零。是人民畫報社的老記者、老編輯手把手地教我。
當時社領導是丁聰、胡考、李千峰等,均為業界翹楚。他們覺得我在攝影上有天資,就把我交給了攝影大師敖恩洪,讓我跟他學。引導我走上攝影之路的正是敖老,他是我的攝影老師,更是我的“業師”。1953年春天,敖老帶著我到廣西漓江采訪,我們一老一小徜徉在漓江翠竹叢中,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記得當時有多么興奮。就是在這次,敖老拍下了他的傳世佳作《漓江翠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的攝影風格是在敖老的言傳身教和潛移默化中形成的。


《人民畫報》:您當年雖為小記者,但很快就獨當一面,2 0歲就被派往西藏獨自采訪。這是一段怎樣的經歷?
何世堯:我18歲到內蒙古采訪,19歲到海南,20歲到西藏。幾個采訪報道任務完成得都不錯,得到領導和大家的肯定。我也就在人民畫報社“站住腳了”。
1955年,西藏還是《人民畫報》記者采訪的“空白點”,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人民畫報社第一次派記者前往西藏采訪,竟然選擇了不到2 0歲的我。我那時“初生之犢不怕虎”,接到任務十分興奮。
我首先到成都,去運輸公司專門找一位勞模司機,搭他開的貨車,沿剛通車不久的康藏公路向拉薩進發。當時康藏公路的路況很驚險,不僅要穿越高山峻嶺,還要經過多處急流險彎。在一些被稱為“鬼門關”的路段,膽小的司機都不敢往前開。沿途我不時點香煙遞給司機,心想他可千萬別打瞌睡,結果我卻學會了抽煙。
走走停停,坐了一個月零六天的汽車,磨破了一條褲子,終于到達拉薩。在途中我就完成了一組報道—《從雅安到拉薩》,這是《人民畫報》首次刊登由本刊記者采訪的西藏報道。1959年,我第二次進藏采訪。前后兩次進藏完成了20多組專題,外加一個封面、三個封底。
人民畫報:您拍攝的《巍巍長城》影響極為深遠,根據這幅作品織就的掛毯《長城》也被作為國禮贈送聯合國。您能分享一下當時拍攝的經歷和背后的故事嗎?
何世堯:拍這張照片時我27歲。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初是我攝影創作上的第一個高峰期,完成了一系列專題攝影報道,其中就包括《巍巍長城》。1962年夏末秋初,《人民畫報》計劃較有創意地連載報道長城,為此組織有關記者、編輯查閱有長城攝影作品的中外報刊。我發現,以往拍長城普遍是“一多一少”—站在長城拍長城的多,早晚時分拍長城的少。為此我設想出拍攝一張“一抹朝陽染紅燕山峰巔,長城在灰藍色的群山中隱約盤旋”的照片。
拍攝當天,我與敖老等一行人天不亮就出發了。為了這次采訪,社里還專門派了一輛車。但到了八達嶺,我發現由于東邊有高山遮擋,陽光照到峰巔時不是“染紅”,而是“照亮”,這讓之前的美妙設想變成了空想。我就開始琢磨:因為“一多一少”,肯定是要“離開長城拍長城”的。我沿長城走到有“游人止步”牌子的一處缺口,剛準備跳出去,遠遠地看到敖老站在秋陽似火的烽火臺上取景。我向他揮手并指向長城外的山巖,敖老向我點頭示意。我隨即爬到山巖上的一處制高點。
從下午三四點到五點多鐘,我靜等光線變化。當側逆的陽光勾勒出山巒起伏的條條輪廓,微微的霧靄使遠近山體明顯分離時,我連續按下快門,拍攝了8張6×9彩色片。從林哈夫相機取景框中看到的長城是“多一分則滿,少一分則空”,盤亙起伏的八達嶺游覽段被完美地包容在取景框內,這使我興奮地癱坐在山巖上。
夏秋交替的季節,坐等這個季節的側逆光,尋找到離開長城的一個制高點,這就是“天時地利”。再加上事前的準備,腦海中有很多長城的形象,這就是“形象儲存”。正是《巍巍長城》的拍攝經歷,讓我悟到“現場構思”和“形象儲存”在風光攝影中的重要性,總結出一幅好的風光攝影作品的誕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統一。更重要的在于人的情懷,達到“山水為我生,草木為我長”。
《人民畫報》:在您的攝影生涯中,最重要的是12 0多組專題攝影,關于專題攝影您有何體會?
何世堯:我認為專題攝影是《人民畫報》最主要的報道形式,它實際上就是“用圖片做文章,用圖片表達主題思想,用圖片吸引讀者”。這是我在采訪時的體會。文學創作用文字的藝術表達來吸引讀者,畫報拿什么吸引讀者?就是用圖做文章來吸引讀者,風光攝影實際上是攝影人在專題攝影風格上的延伸和折射。
《人民畫報》:攝影報道、創作貫穿了您的攝影生涯,對您來說,攝影意味著什么?
何世堯:對我來說,攝影就是我的人生職業。這條職業道路是我在上海格致中學被選到《人民畫報》開啟的。如果我沒有被送到《人民畫報》當小記者學習攝影,我的人生道路就不知道是什么樣了。是《人民畫報》的老領導、老記者、老編輯,把一個不知道相機是什么樣的高中生培養成可獨立采訪的小記者,成長為一位善于專題攝影、人物報道和風光攝影的記者。《人民畫報》就是我的攝影母校。如果說我在攝影生涯上的一點成就,主要是那幅《巍巍長城》。這幅作品雖然沒有得過什么攝影類的獎項,但最令我欣慰的是,這幅作品被制成巨幅壁毯,至今懸掛在聯合國會議大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