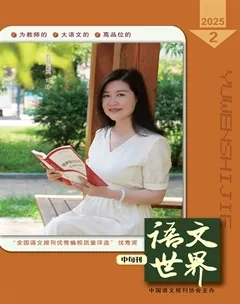大力研究語文教學 盡快改進語文教學(節選)
從一九二三年到如今,五十五年了,編選教材的辦法屢次變更,可是有一點沒有變,就是中學里白話文和文言文摻合著教。教法也有所變更,從逐句講解發展到講主題思想,講時代背景,講段落大意,講詞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來年了。可是也可以說有一點沒有變,就是離不了教師的“講”,而且要求講“深”,講“透”,那才好。教師果真是只管“講”的嗎?學生果真是只管“聽”的嗎?一“講”一“聽”之間,語文教學就能收到效果嗎?我懷疑好久了,得不到明確的答案。還有,對于白話文和文言文摻合著教,我也懷疑已久。
前些日子《人民日報》登載呂叔湘同志的《當前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擔任語文課的教師。文章里說:“十年的時間,二千七百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文章里說:“少數語文水平較好的學生,你要問他的經驗,異口同聲說是得益于課外看書。”文章里問:“是不是應該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用較少的時間取得較好的成績?”就這幾句話,盡夠發人深省的了。
我想,從前讀書人十年窗下,從師讀書,不管他們后來入不入仕途,單說從老師那里真得到益處,在讀書作文方面真打下基礎,不至于成為似通非通的孔乙己的,不知道占多少比率。向來沒有作過統計,當然沒法知道占多少比率。但是我武斷地想,恐怕不會很多吧。從前那些讀書讀通了的人,那些成為學問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所說的“得益于課外看書”(就是說,脫出塾師教讀的范圍),或者是碰巧遇到個高明的塾師,受到他高明的引導,因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的吧。
假如我的猜想有點兒對頭,那么咱們如今的語文教學再不能繼承或者變相繼承從前塾師教讀的老傳統了。從前讀書人讀不通,塾師可以不負責任,如今普通教育階段的語文教學卻非收到應有的成績不可,語文是工具,自然科學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數、理、化,社會科學方面的文、史、哲、經,學習、表達和交流都要使用這個工具。要做到個個學生善于使用這個工具(說多數學生善于使用這個工具還不夠),語文教學才算對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盡了分內的責任,才算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盡了分內的責任。以往少慢差費的辦法不能不放棄,怎么樣轉變到多快好省必須趕緊研究,總要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得到切實有效的改進。
實踐出真知,語文教學的實踐者是教師,因此研究語文教學如何改進,語文教師責無旁貸。個人研究總不及集體研究,學校里已經恢復了教研組,集體研究就很方便。幾個學校的教研組互相聯系,交流研究和實踐的結果,那是集思廣益的好途徑。
語言學科的工作者有的兼任語文教師,就是不任教師的,研究的東西往往跟語文教學有關聯。因此,語言學科的工作者是語文教師最親密的伙伴,義不容辭,要為改進語文教學盡力,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
我在這里懇切地呼吁,愿語文教師和語言學科的工作者通力協作研究語文教學,做到盡快地改進語文教學!
至于我,以往的經歷只是講書,跟從前的塾師一個樣,夠可笑的。后來不當教師了,講主題思想講時代背景之類我都沒干過,只在不多幾所中學小學里參觀過語文的課堂教學,只看過些中學生小學生的作文本子。參觀了,看了,不免有些感想。是感想,不能不主觀,又難免片面,但是也不妨說出來請同志們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