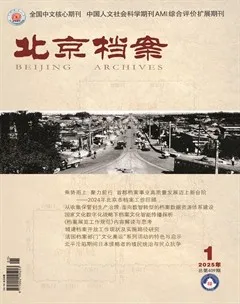咸豐年間的長蘆鹽政與地方社會
摘要:清代鹽政,舊制以巡鹽御史充任,代表朝廷巡視地方鹽務。清前期長蘆鹽政承擔著督催鹽課、緝查私鹽、糾察鹽官的鹽務監督職權。在近代社會的轉型中,長蘆鹽政的職權逐漸發生了變化。咸豐年間長蘆鹽政一方面仍承擔著督催鹽課的基本職權,另一方面衍生出防守地方的事權。面對長蘆鹽商引課乏力、灶戶灶力拮據,長蘆鹽政督催引課、額征灶課的應對之策,對地方鹽務和民力恢復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天津地方防守事務中,長蘆鹽政被賦予天津防守事權,其妥籌布置地方防守,激勵練勇,督率兵勇截剿賊匪,有力地維護了天津地方社會的秩序。長蘆鹽政由督催鹽課的基本職權衍生至防守地方事權,異化為地方行政權力,偏離了本來的鹽務監督權力。
關鍵詞:咸豐年間 長蘆鹽政 地方社會 督催鹽課 防守地方
Abstract: Salt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used to appoint salt inspec? tors as officials, who represented the impe? rial court to inspect local salt affai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anglu salt adminis? tr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ng salt tax, investigating illegal salt, and supervis? ing salt official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the authority of 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had gradually changed. During the Xianfeng period, Changlu salt ad? ministration still bore the basic authority of supervising and urging salt tax collection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derived the power to defend region . Confronted with weak payment of Changlu salt mer? chants and salt-makers difficulties, Chang? lu salt administration’s countermeasures of supervising salt tax collection and levying salt-makers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cal sal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i? vilian force. In the local defense affairs of Tianjin, 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was granted the authority to defend Tianjin. By setting up local defense, motivating militia? man and leading soldiers to combat bandits and thiefs, 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ef? fectively maintained the order of local soci? ety in Tianjin. The basic authority of Chang? lu salt administration had evolved from su? pervising and urging salt tax collection to defending local affairs, deviating from their original salt affaris supervision power.
Keywords: the Xianfeng period; Chang? lu salt administration; Local society; Super? vise and urge salt tax collection; Defend re? gion
清代鹽政,舊制以巡鹽御史充任,一年更代。[1]順治二年(1645),在長蘆、兩淮、兩浙、河東等地各派巡鹽御史一人,代表朝廷巡視地方鹽務。對于巡鹽御史與鹽政的關系,“巡鹽御史后定為鹽政”,[2]但未提及巡鹽御史何時定為鹽政。雍正以后,巡鹽御史一般簡稱作鹽政。[3]檢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大臣奏折、題本,雍正朝和乾隆朝交互出現巡鹽御史與鹽政,至嘉慶以后,清代奏折、題本、典籍不再出現巡鹽御史,而以鹽政完全取代。
鹽務作為清代三大政務之一,關系國用、軍需及民生。學界研究成果關注于清代前期鹽政或清代鹽政的個體或清代鹽政的整體考察,[4]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視角,但是對于清代中期的鹽政研究不多,尤其是清代鹽政被裁撤前的最后十年,尚未進行專門研究。長蘆是清代重要的產鹽區。清代設置長蘆鹽政,其是長蘆鹽區最高的鹽務專官,主掌督催鹽課、緝查私鹽及糾察鹽官。一切運銷征課事宜唯該鹽政總理督辦,運司以下等官皆為所統轄,責至專任,至重也。[5]然而在近代社會的轉型中,長蘆鹽政的職權逐漸發生了變化。咸豐時期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長蘆鹽政一方面仍承擔著督催鹽課的基本職權,另一方面衍生及異化出地方防守的事權。咸豐年間的長蘆鹽政始于咸豐元年(1851),被裁撤于咸豐十年(1860),歷時十年,期間崇倫、文謙、烏勒洪額、松嶺、寬惠曾擔任長蘆鹽政,其中文謙在任時間最長。[6]本文主要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奏折、題本,著重研究清代長蘆鹽政被裁撤前的最后十年,考察咸豐元年至咸豐十年長蘆鹽政督催引課、額征灶課的職權及地方防守的事權,分析其在地方社會中的重要作用與影響。
一、督催商人引課
清代鹽課分三種,向運銷商人征收的,稱引課。因引課為鹽的主要項目,又常稱為正課;向食鹽生產者、鹽戶征收的,稱灶課;各項附加稅和其他苛捐、規費等,則統稱雜課。[7]其中,引課收入最為重要。順治元年(1644),歲征正引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四錢一分二厘五毫。[8]有清一代,督催引課是鹽政的基本職權,也是清代鹽政最重要的職權。
長蘆正引九十六萬六千四十六道,隨正額余引五萬道,續請余引無定額。[9]咸豐四年(1854)五月,“應征兩年份商課錢糧,盧龍縣、撫寧縣、昌黎縣、臨榆縣、灤州縣、遷安縣、樂亭縣、濟源縣、孟縣等九州縣共額征課銀壹萬柒仟叁百貳拾肆兩柒錢捌分壹厘,舊管無項,新收銀肆仟陸百三兩壹分。盧龍、灤州、遷安等五州縣未解聲明,嚴提續報等情,循例造冊,詳情會題前來。臣將前項銀錢鈔票逐一盤查,照例出具印結,原冊分送部科查核”[10]。從長蘆鹽政文謙的題本,我們可以清晰看出長蘆鹽政督催引課具有嚴格完整的程序與步驟。首先核定額征課銀的數目,然后查看各州縣引課征收情況,對于未解聲明的州縣,做出嚴提續報、循例造冊的處理,最后鹽政逐一盤查銀錢鈔票,出具印結,分送部科查核。
鹽課是清中前期國家財政收入中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項收入,地位頗高。[11]咸豐年間長蘆鹽政督催商人引課的形勢,與清前期具有很大差別。19世紀中葉以來,英國侵華打開中國大門,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國內市場出現銀貴銀荒。咸豐時期不僅面臨國內市場銀貴的經濟情形,而且面臨英法侵華、粵匪竄擾的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加之長蘆鹽區自然災害頻發,導致長蘆鹽政督催引課十分乏力。本部分集中于對咸豐四年長蘆鹽政的奏折、題本進行論證。
針對長蘆鹽政督催商課乏力的局面,長蘆商人晉和源、兼運司天津府知府錢忻和提出解決措施。晉和源從蘆綱成本微薄、銀價日增方面陳述了蘆綱的困難局面,“蘆綱成本素來微薄,近年銀價日增虧本殆盡”,“從前尚可向銀號錢店通融周轉,上年逆匪竄擾各鋪歇業,被賊引地焚掠一空,遭水之區,銷數無所出,既乏點金之術,又無告貸之門”,其從維護商人的利益角度,提出頒發官票的解決措施,“若不稟請調劑全局,空難保全,當此經費支絀之際,不敢妄冀請帑。懇請奏頒官票一百萬兩,寶鈔制錢二百萬串,作為成本籍資營運,按引應完課款”,并且提出商人請領官票永遠生息,“現銀票鈔各半交納,所發票鈔通綱按引請領永遠生息,每年三厘,統歸年終完交”。[12]錢忻和不僅認可晉和源對于長蘆商課乏力的因素陳述,亦從蘆商成本、銀價遞增、賊匪滋事方面進行論述,“蘆商本征力薄,鮮有富厚,故從前每遇災歉,有請帑生息之案,嗣因庫項不充無款籌借,兼之銀價遞增,銷數日減,成本遂虧,往時尚賴銀錢賬局通挪周轉。自逆匪滋事以來,放債之家悉多歇業。上年逆匪竄擾直境運道。既受銀貴之累,又遭兵水之災,體察綱情”,而且提出頒發官票的補救之策,“若不設法補救,誠恐全局難支,且鈔票章程甫定,正宜設法推行,似應準所請,以蘇商困而冀流通。請頒發票銀一百萬兩,實鈔制錢二百萬串”。[13]從晉和源、錢忻和的陳述與解決措施,可以得出以下兩點:一是微薄的蘆綱成本、日增的銀價、粵匪竄擾焚掠、鹽區遭水等多方面因素導致蘆商引課的乏力;二是兩人都提出頒發票銀一百萬兩,實鈔制錢二百萬串,才能解決補救,否則出現“全局難支”的局面。其對策看似解決了商人上繳鹽課的燃眉之急,但在軍費開支支絀的情形下,并未考慮清政府頒發官票的實際承受能力以及商人按引領交息的償還能力。
對于晉和源、錢忻和提出頒發官票、商人引領交息的解決措施,長蘆鹽政文謙提出應對之策。他認同長蘆商課征收面臨的艱難局面,“長蘆鹽務自道光二十八年蒙差王大臣查辦之后,原期銀價漸平,引地暢銷數年以來,為受銀賤之益,轉遭兵水之災,遂致商本虧賠,束手無策”,[14]但對于錢忻和提出頒官票銀一百萬兩,鈔制錢二百萬串,發商生息,籍資營運的解決措施,文謙認為其雖然系為保護全局,屬于補救之策,但是仍需要通盤籌計。對于蘆綱商人,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鹽綱商人不下一百數十家,其內引地暢滯、商家殷實苦累性情,各有不同。對于豐裕、自能顧身家資本的商人,其必能妥為營運,依限繳本;而對于累商,本已拖欠正課帑利雜款,今再發給鈔票生息,其必然樂于請領且敷衍。等待數年后,本利都無法償還。[15]
面對長蘆鹽政督催商課乏力的情形,咸豐帝認為,受水災、逆匪竄擾焚掠、運路阻隔、銀價倍增的影響,蘆商請緩,“查長蘆每年應征引課錢糧向歸五月奏銷,上年下雨遇多,直省州縣均被水災,旋值逆匪竄擾,蘆綱引岸,復遭焚掠,秋后逆困踞獨流運路阻隔,引皆停領。本屬疲累之商,猝遇非常之災,又兼銀價倍增,各商屢請展緩日”。[16]雖然咸豐帝充分認識到蘆商的艱難情形,但“以承借之票,作為應交之款,名為奏銷無絀,實則減課五成。不但借項歸款無期,且恐有妨正課”,咸豐帝最終沒有批準承借之票,“該鹽政所請、承借官票之處,著不準行”。[17]值經費支絀之時,未便率準所請當飭運司照舊,一律開征,并督同該司實力嚴追。[18]咸豐帝之所以沒有批準承接之票,而是采取“一律開征、實力嚴追”的態度,一方面是由于蘆商歸款無期,另一方面是由于軍費支絀。但是面對蘆商疲敝的實在情形,咸豐帝從恤商的角度,準其五成交銀,并且五成以制錢二千、作銀一兩交納,如此變通辦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蘆商的負擔,“恤商即以裕課。該鹽政務當督飭運司、該商等應完課款,認真稽核,隨時提解,毋得任令各商藉口疲敝,再有延誤”。[19]
依照咸豐帝的諭旨要求,長蘆鹽政文謙伏思軍興以來,經費支絀異常,“何敢輕議展緩,恐該商等藉此觀望,嚴行駁飭”,然而目擊蘆商艱難,內心萬分焦灼,“開征以后,親旨運署,督同運司,逐日比追。截至五月二十九日限滿,征收甫經一半”,并且沒有采取嚴苛的期限限制,以冀多征一份,“若拘泥定限,即行截數,又恐該商等雖有續到標項,業已奏報延不繳納,向運司商酌三日一推、五日一展或發縣押追,冀多得征一分,即多得一分之用”。然而直至六月二十日,“現商全完者,不過數人,其余仍不足數。核計未完二分以上,已屬筋疲力盡。查該商等應交引課錢糧不能依限完交,照例參革抄追”。[20]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軍費支絀情形下,長蘆鹽政文謙督同運司,逐日比追引課,完成二分以上的蘆商,已筋疲力盡。看似征收引課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但對于受到水災、逆匪焚掠、運路阻隔、銀價倍增的蘆商實在情形,能取得此征收效果實屬不易,有力地保障了軍費的開支。
綜上所述,面對蘆綱成本微薄、國內銀貴、自然災害頻發、粵匪竄擾焚掠導致的蘆商引課乏力,長蘆鹽政文謙、兼運司錢忻和、商人晉和源提出不同的解決之策,咸豐帝從軍費支絀、蘆商歸借能力的角度,給予“一律開征”的政策,但準其五成交銀,并且五成以制錢二千、作銀一兩交納的變通辦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變相地減輕了蘆商的引課負擔,體現了清代最高統治者的恤商思想。
二、額征州縣場灶課
引課與灶課共同構成清代鹽課的內容。灶課作為鹽政督催鹽課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鹽的生產者即灶戶征收的課稅。灶課與灶戶的利益息息相關,與底層民生關聯度高。本部分主要考察咸豐元年至咸豐十年長蘆灶地因被水被旱、賊匪滋擾的復雜情形,長蘆鹽政對灶地征收灶課的方式。
清代長蘆鹽場灶課經歷了以人丁為派征單位到以土地為派征單位的演變過程。[21]長蘆鹽政額征州縣場灶課,會嚴格核定灶課銀數以及舊管、新收銀數。“咸豐元年,灶課應為銀壹萬壹仟叁百陸拾玖兩肆錢五分捌厘,舊管存銀玖千肆百玖拾伍兩壹錢柒分捌厘,新收銀壹萬陸百捌拾伍兩捌錢伍分玖厘”。[22]對于州縣的未解情形,長蘆鹽政崇倫做出勒令限日、立即續報的處理方式,“慶云縣知縣賀詳麟等肆縣場征存未解銀六百捌拾叁兩伍錢玖分玖厘,勒限嚴提,一俟解到,立即續報,理合造縣清冊,詳送會題”,[23]并將銀兩逐一盤查。
在清代灶課征收過程中,出現多種積欠情形。有人為因素導致的拖欠,雍正三年(1725),刁頑積習的灶戶出現拖欠灶課,“倚恃貢監生員,包役抗糧,以完課為恥,以逋賦為能,積年拖欠甚多”,[24]也有因自然災害積欠灶課的情況。灶地是灶戶的重要生產資料,理應受到保護,但咸豐年間長蘆鹽區面臨自然災害頻發,灶地秋禾出現被水被旱的情形。咸豐二年(1852),長蘆所屬天津靜海、青縣、滄州、南皮、鹽山、慶云、衡水、海豐等九州縣并豐財、蘆臺、嚴鎮、海豐周四場,灶地秋禾被水被潮。面對長蘆所屬天津靜海等九州縣灶地秋禾被水情形,長蘆鹽政文謙征收灶課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于成災歉收五分的灶地,采用蠲免十分之一,其余征收,但分兩年征收的方式,“天津等縣場秋禾被水成災五分,共灶地七百一十五頃六十二畝六分五厘,照例蠲免十分之一,銀六十八兩叁錢四分六厘,尚應征銀六百一十五兩一錢一分九厘,分兩年征收”。[25]對于歉收三四分的灶地,援照民糧之例,緩征至下年征收,“天津等州縣場秋禾被水被潮,歉收三四分,共灶地兩千六百四十三頃六十二畝九分九厘五毫,請援照民糧之例,緩至咸豐三年秋后征收”。[26]從長蘆鹽政文謙上奏的奏折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咸豐二年州縣場灶課積欠的因素,主要是灶地被水被潮導致歉收,主要依據灶地受災面積及受災程度,被水灶地的征收灶課方式不同。咸豐三年(1853)六七月,長蘆所屬天津靜海等十一州縣及海豐等四場,亦是由于秋禾被水,“長蘆所屬天津靜海、青縣、滄州、南皮、鹽山、慶云、寧河、寶坻、衡水、交河等十一州縣,并豐財、蘆臺、嚴鎮、海豐等四場因連次大雨,并因河水漲發間有漫溢,以致秋禾被水”。[27]對于天津靜海等十一州縣及海豐等四場秋禾被水情形,天津分司轉飭各州縣場,會同委員查看灶地秋禾歉收,并以州縣被水灶地頃畝分數,作為州縣被水灶地應蠲應緩錢糧數目。
除卻灶地秋禾被水導致歉收,粵匪竄擾焚燒造成民力拮據,導致灶戶無法完成灶課數目。因灶地秋禾被水、粵匪竄擾焚掠的雙重因素,征收灶課的情形更為復雜。咸豐三年十一月,各州縣或被賊竄擾或秋禾被水,分為四種征收方式。一是被賊滋擾的直隸省沙河等州縣,照常輸納會導致民力拮據,緩至下年秋后征收,“所有合境被擾之沙河、任縣、隆平、柏鄉、趙州、欒城、晉州、深州、交河、滄州、靜海等十三州縣應征糧租,緩至咸豐四年秋后征收”。[28]二是既被滋擾又秋禾被水的滄州等州縣,援照民糧的標準豁除灶課,“滄州等州縣上年九月間被賊滋擾,請將未完,咸豐三年灶課并節灶欠緩征銀兩,秋禾被水,援照民糧,奉上諭一律請豁除”。[29]三是灶地秋禾被水成災五六七分的天津等州縣場,蠲免十分之一的灶課銀兩,其余灶課銀分兩年征收,“豁免銀壹百壹兩伍錢捌分柒厘,尚應征銀陸百玖拾壹兩捌錢捌分玖厘,請分二年帶征”。[30]四是灶地秋禾被水歉收三四分的天津等州縣,援照民糧,緩至下年秋后征收。“天津等州縣場秋禾被水,歉收三四分,額征銀叁千玖兩陸錢貳分,應援照民糧,奉上諭緩至咸豐四年秋后征收”。[31]咸豐三年十一月,征收灶課之所以分為四種征收方式,考量因素有三:部分州縣的灶戶面臨灶地被水、賊匪竄擾的雙重打擊;實行蠲緩或豁免的恤戶政策,以紓灶力;灶地受災的程度和受災面積的不同。
咸豐二年和咸豐三年,長蘆灶課難以正常征收的共同原因,緣于灶地被水導致歉收。然而咸豐六年(1856)長蘆鹽場面臨被旱被水的自然災害,對灶地的破壞力更大。“咸豐六年六七月,長蘆所屬天津靜海、青縣、滄州、南皮、鹽山、慶云、寧河、寶坻、衡水、海豐等十一州縣,并豐財、蘆臺、嚴鎮、海豐等四場因雨澤稀少導致田禾被旱,又因雨水遇多導致田被淹”。[32]對于天津靜海等十一州縣及海豐等四場秋禾先后被旱被水情形,天津分司轉飭各州縣場,會同委員查看灶地秋禾歉收,并以州縣被旱被水災地頃畝分數,作為州縣被旱被水灶地應蠲應緩錢糧數目。與咸豐六年六七月天津靜海等十一州縣及海豐等四場秋禾先后被旱被水情形不同,咸豐九年(1859)六七月,蘆屬部分州縣灶地被旱,“蘆屬灶地鹽山、慶云、海豐三縣雨澤稀少,秋禾被旱”,[33]部分州縣灶地被水,“滄州、南皮、天津靜海青縣、衡水六州縣連次大雨,導致坐落滄州、鹽山等州縣境內的低洼灶地秋禾被水”,[34]天津分司轉飭各州縣場查看灶地歉收分數情況,滄州等州縣場勘明灶地秋禾被水被旱歉收三四分不等,該州縣以歉收灶地頃畝分數,作為應緩錢量數目。
綜上所述,從咸豐元年至咸豐十年的長蘆灶地情形看,不僅面臨被水被旱自然災害的頻發,而且面臨賊匪竄擾焚掠的人為危害。長蘆鹽政額征灶課時,根據灶地受災程度和灶力的困境,對灶戶實行蠲緩或豁免的救助方式,促進了民力的休養和恢復,體現出清代統治者的“仁政”治國理念。
三、防守地方事務
天津歷來為水陸沖要,具有拱衛京畿的重要作用。咸豐年間面對賊匪竄擾的嚴峻形勢,維護天津地方穩定成為重要事務。對于天津的防堵事務權,咸豐帝主要通過三道諭旨做出指示,不僅有力地維護了地方穩定,而且對長蘆鹽政的職權產生重要影響。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長蘆鹽政文謙奉上諭:
“天津為水陸沖要,拱衛京畿,所有稽查奸宄、彈壓地方,均關緊要。文謙雖無地方之責,現當辦理防堵之際,著該鹽政會同天津鎮道督率地方文武,一體認真查察。”[35]
咸豐帝頒發的此道諭旨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一是雖然長蘆鹽政監督地方鹽務,并無地方之責,但面對防堵賊匪的天津嚴峻形勢,其必須與天津鎮道共同維護地方穩定。二是在辦理地方防堵事務中,“會同”“督率”的上諭用語,體現出咸豐帝對長蘆鹽政文謙的定位。“會同”表明長蘆鹽政與天津鎮道共同監督領導地方文武。“督率”表明長蘆鹽政對天津地方文武具有監督領導權。此時的咸豐帝對長蘆鹽政文謙定位很高,賦予其充分的領導、參與天津地方防堵事務的權力。
咸豐三年九月初一,咸豐帝頒發諭旨,進一步作出巡防要求:
“天津為畿東保衛,現值逆氛未靖,一切防守關系緊要,必須事權歸一方,足以資彈壓。長蘆鹽政文謙系朕特簡之員,所有地方防堵事宜,即責成文謙會同鎮道大員妥為籌辦,并隨時督率文武員弁及紳民練勇等實力巡防,總以嚴緝奸匪,鎮定人心為要。”[36]
從咸豐帝頒發的上述諭旨要求,可以解讀以下三點信息:一是咸豐帝明確提出天津防守的事權必須歸一方,“足以資彈壓”,但并未指明天津防守的事權歸于鹽政還是天津鎮道;二是強調“長蘆鹽政文謙系朕特簡之員”,表明咸豐帝對長蘆鹽政文謙的信任程度;三是與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頒發的諭旨相比,雖然咸豐帝仍然諭令文謙“會同”鎮道大員妥為籌辦,但“督率”的對象增加了紳民、練勇,表明長蘆鹽政可以監督領導天津地方的文武官員、紳民、練勇。“督率”范圍的擴大,一方面意味著長蘆鹽政需要承擔更多的天津防堵事務責任,另一方面也為成功保衛天津提供了組織保障。
咸豐三年九月初三,面對逆賊抵達平定州、正定、援及趙州的情勢,咸豐帝頒發諭旨,“長蘆鹽政督同天津鎮道實力巡防,慶祺統領盛京官兵二千,由天津水路啟程”。[37]在此諭旨中,咸豐帝作出長蘆鹽政“督同”天津鎮道實力巡防的要求。上述三道諭旨中“會同”至“督同”的重要轉變,表明咸豐帝最終將天津防守事權歸于長蘆鹽政,不僅為咸豐年間高效保衛天津提供了機制保障,而且為長蘆鹽政職權由監督鹽務衍生至地方防守事務提供了政治依據。
依照咸豐帝的諭旨要求,長蘆鹽政文謙奉派辦理地方防守事宜。一是妥籌布置防守,實力辦理。察看何路吃緊,即于何路設防,其要口渡船,亦應設法收集,偏僻汊港,實力巡查,并隨時飛探賊情,嚴拏奸細。[38]天津為賊匪所覬覦,于咸豐三年冬曾遭賊匪攻撲,需要加倍嚴防,“就現存兵勇,與載堪慎密妥籌,同心勠力,幫同巡緝,以期先事豫防”。[39]二是激勵練勇。長蘆鹽政文謙奉咸豐帝上諭,對鄉勇妥為激勵,“使鄉勇保護鄉閭”。[40]咸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逆匪由青縣竄至天津,“彼時大兵尚未到齊,經文謙等分督防守官兵。迎頭截剿,該處練勇,復隨同天津縣知縣謝子澄,直前迎殺,擒斬甚多”[41]。“直前迎殺,擒斬甚多”,表明天津練勇作戰能力很強。咸豐帝充分肯定天津練勇忠義勇敢,勠力同心為朝廷出力。在清廷加緊推廣廣西巡撫任用在籍紳士協助地方官員辦團的模式下,[42]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長蘆鹽政文謙為在籍紳士梁寶常辦理團練請發職銜,“前因逆匪滋事,奉旨勒令地方官紳舉辦團練以資保衛。在籍紳士梁寶常等專設團練總局,招募壯勇,制備箭械,實力防剿,一切經費由本地紳民捐輸供應。按照該紳民報捐錢文所請職銜,早沐恩榮”。[43]三是帶領兵勇截剿賊匪。文謙帶勇,與其他將領配合截剿賊匪,續獲大勝。咸豐三年十月十三日,勝保奏,勝保親督天津正定河州宣化西寧各隊,達洪阿帶領健銳火器兩營兵弁,佟鑒復用神威銅炮向西橫擊,文謙帶勇,督運大炮轟擊。逆眾不敢抗拒,奔回木城,其木城外賊匪,均被我兵擊斃。[44]咸豐三年十一月,逆匪竄至天津,經文謙等帶領兵練,接仗獲勝,殲賊多名,該匪被剿。[45]
長蘆鹽政文謙妥籌布置防守,激勵練勇、帶領兵勇截剿賊匪,為之后的長蘆鹽政實力巡防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模式。咸豐八年(1858)三月初八,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督飭長蘆商人張錦文,勸諭城關四廂鋪戶居民,按照咸豐三年防堵舊章,分段設局,各自團勇,稽查奸細。長蘆鹽政烏勒洪額仍不時親查察其勤惰,分別勸懲。[46]咸豐十年七月,長蘆鹽政寬惠等調防守天津官兵并郡城練勇,赴大沽防剿。[47]
綜上所述,咸豐年間長蘆鹽政文謙、烏勒洪額、寬惠奉派天津地方防守事務,為天津地方社會的秩序與穩定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咸豐帝評價長蘆鹽政文謙,“該鹽政系特派天津防剿大員,素得該處士民之心”,[48]真正擔負起防守天津的地方之責。
四、結語
19世紀中葉,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長蘆鹽政的職權逐漸發生了變化,由督催鹽課的基本職權衍生至防守地方事權。因蘆綱成本微薄、國內銀貴、長蘆鹽區自然災害、賊匪竄擾焚掠,咸豐年間長蘆鹽政督催引課出現困境,蘆商、長蘆鹽政、鹽運使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咸豐給予“一律開征”的政策,同時實行一定的恤商變通方式。咸豐元年至咸豐十年,長蘆灶地因被水被旱、賊匪竄擾焚掠,長蘆鹽政對灶戶實行蠲緩或豁免的救助方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灶力的拮據。
天津不僅是水陸沖要,而且為畿南門戶,是拱衛京畿的重要屏障。面對咸豐年間粵匪北竄的嚴峻形勢,維護天津地方穩定成為重要事務,最終咸豐帝授予長蘆鹽政防守地方事權。長蘆鹽政文謙妥籌布置防守,激勵練勇,帶領兵勇截剿賊匪,“以新集之勇,挫方盛之鋒,賴以保全大局,津郡生靈得免荼毒,實為御災捍患,功德在民”,[49]有力地維護了天津地方社會的秩序與穩定,達到“力拒狂寇,保全闔郡,屏蔽京師”。[50]長蘆鹽政由督催鹽課的基本職權衍生至防守地方事務,是清代中期局勢的必然。一方面,長蘆鹽務日漸衰敗,長蘆鹽政擔負的鹽務專責亦遠遠不如清代前期。另一方面,天津防守緊迫,需要信任之臣擔任。長蘆鹽政作為皇帝的特簡之員、特派天津防剿大員,被賦予地方防守事權。長蘆鹽政的職權衍生至防守地方事務,異化為地方行政權力,偏離了本來的鹽務監督權力,其最終于咸豐十年被裁撤。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社會組織和國家基層治理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3ZD248)的階段性成果;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清代河東巡鹽御史與鹽務監察研究”(課題編號:2021YJ096)的研究成果。
注釋及參考文獻:
[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天津市長蘆鹽業總公司.清代長蘆鹽務檔案史料選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449.
[2]自貢市鹽務管理局.自貢市鹽業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21.
[3]陳峰.清代鹽政與鹽稅[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27.
[4]參見張致和.清代長蘆鹽場灶課制度演變與灶課征收實態前沿,2024(4);黃國信.清代鹽政基本原理論綱(1644-1850).清史研究,2023(6);陳鋒.清代的巡鹽御史——清代鹽業管理研究之三.人文論叢, 2016(2);常建華.清順治朝的長蘆鹽政.鹽業史研究, 2012(3);芮和林.勤政清廉的長蘆巡鹽御史──莽鵠立.鹽業史研究,2000(6)。
[6]烏勒洪額.題為造送鹽課正雜錢糧清冊事,檔號:02-01-04-21591-0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據該題本記載,文謙自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咸豐六年六月三十日交卸。
[7]金人慶.中國稅務辭典[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412.
[8][9][24]黃掌綸,等.長蘆鹽法志[M].劉洪升,點校.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94,142,133.
[10]文謙.奏銷長盧龍等州縣額政咸豐二年份商課錢糧事,檔號:02-01-04-21536-00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11]黃國信,劉巳齊.交易成本與課入量:清代鹽課基本原理研究(1644—1850)[J].學術研究,2021(10):114.
[12][13][14][15]文謙.奏為蘆綱疲敝擬請體察商情分別設法補救以保全局折,檔號:04-01-30-0470-00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奏折。
[16][18][20]文謙.奏為征補現商懸岸課銀并陳蘆綱被災情形請將未完銀兩分別勒限催征折,檔號: 04-01-35-0519-0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奏折。
[17][19][39]清實錄:第42冊[M].北京:中華書局, 1998:277,277,247.
[21]張致和.清代長蘆鹽場灶課制度演變與灶課征收實態[J].前沿,2024(4):121.
[22][23]崇倫.奏銷長蘆咸豐元年份額征灶課錢糧事,檔號:02-01-04-21497-00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25][26]文謙.題報長蘆所屬天津等州縣場咸豐二年灶地秋禾被災地畝分數蠲緩錢糧事,檔號:02- 01-04-21514-00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奏折。
[27]文謙.長蘆所屬天津等地灶地秋禾被水情形事,檔號:02-01-04-21536-0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28][29][30][31]文謙.長蘆所屬天津靜海等十一州縣并豐財等四場,咸豐三年灶地被水成災,又靜海滄州交河三州縣并豐財、嚴鎮、海豐三場被賊滋擾豁免各情形及征免數目案事,檔號:02-01-02-3056-00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32]烏勒洪額.咸豐六年天津等州縣灶地秋禾被水被旱情形事,檔號:02-01-04-21627-0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33][34]寬惠.長蘆所屬滄州等地咸豐九年六七月間灶地被水情形事,檔號:02-01-04-21678-0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題本。
[35]奕,朱學勤.剿平粵匪方略[M].清光緒內府鉛活字印本,1894:3714-3715.
[36][40]沈家本,榮銓,徐宗亮,等.(光緒)天津府志:54卷[M].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1899:209,240.
[37][41]李鴻章,黃彭年.(光緒)畿輔通志[M].清光緒十年刻本,1884:859,889.
[38][44][45][48]清實錄:第4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595,683-684,652,769.
[42]崔岷.紳士無以救時:咸豐六年清廷推行團練“任官督率”的背景與意蘊[J].安徽史學,2021(5):38.
[43]文謙.奏為在籍紳士梁寶常辦理團練請發職銜執照事,檔號:02-4196-09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錄副奏折。
[46]文慶,賈楨,寶鋆.籌辦夷務始末[M].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影印清內府鈔本,1930:8240-8241.
[47]潘頤福.東華續錄(咸豐朝):卷九十五[M].清光緒刻本,1892:7403.
[49][50]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8[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55.
作者單位:1.山西師范大學社會學與法學學院2.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