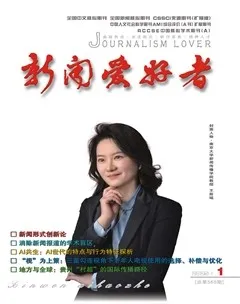新聞形式創新論
【摘要】新聞業在面臨環境巨大變化時進行了大量的新聞形式創新,以期適應變化和謀求新發展。但新聞形式創新行動本身并不一定帶來正面效果,它也可能產生大量關于新聞形式的困惑、退化,甚至會影響新聞的存在根基。因此,理解新聞形式的創新機制就顯得十分重要,這類實踐理論知識將幫助行動者增強對新聞形式創新的自覺和省察,減少盲目性。本研究認為不能僅靠傳統的“題材”和“體裁”分類來理解新聞形式,還需從系統功能的角度理解新聞形式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變化發展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新聞形式創新,遵循著外部轉化、內部重組和優化功能的一般機制。數字傳播環境加速了新聞形式創新的外部轉化,但對內部重組的冷靜思考以及新形式是否能優化而非損害新聞功能的審慎判斷,同樣是新聞行動者需要重視的。
【關鍵詞】新聞形式;新聞創新;系統論
進入數字時代之后,新聞業被認為出現了多重危機。近年來,筆者在新聞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直觀感受到的一重危機是“新聞形式的危機”。在這一危機下,新聞使用者經常發出對新聞媒體的指責——“沒有新聞可報了嗎?”新聞生產者也常陷入自我懷疑——“我做的還是新聞嗎?”甚至,在分析近些年國內外獲重大新聞獎的新聞作品時,這樣的詰問都會不時出現。
“什么是新聞?”再次成為無論是新聞實踐還是新聞研究都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考慮到信息環境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并不輕松。只考慮“應然”問題,難以解決理念與實踐日益增大的落差,甚至會因此產生理論無用的輕蔑;只考慮“實然”問題,就像不少研究所做的傳播效果“測量”,按照目前的知識看,新聞恐怕難逃悲劇的命運。如2018年,三位麻省理工研究員在Science期刊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虛假新聞比真實信息更有傳播力,大數據分析證明,在社交媒體上前者總是傳播得更廣、更快也更深,[1]但好在真正的社會行動并不會割裂應然與實然。正如德國學者韋伯在對社會行動類型化的同時也高度關注社會行動的正當性問題[2],若非如此,我們恐怕很難理解行動的“意義”。做新聞也是這樣的社會行動。一方面,當下出現了不少關于“這還是不是新聞”的爭議,歸根到底是公眾對打著“新聞之名”的文本還能不能履行新聞功能、體現新聞對社會認知秩序的價值貢獻產生了疑問;另一方面,進入全媒體時代之后的新聞生產為了適應新的信息環境,被動或主動地進行了大量變革。新聞行動者面臨的困境是:不變,“新聞”的公共能見度可能會越來越低;改變,“新聞”的規范性可能會受到挑戰沖擊。如何破解這一困局?本文認為,可在系統理論的視角下重新理解新環境條件下新聞形式的變化機制,并為行動者如何同時做到新聞規范與形式創新提供思路。
一、新聞形式為什么重要?
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理念論的基礎上,第一次對“形式”與“質料”的關系進行了理論闡述,這就是著名的“質料形式論”(Hylomorphism)。而且形式與質料并不二分,前者是潛在于后者的內在本原,后者則是前者外化后的現實構成。[3]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認為,任何可感物都是形式與質料的復合體。質料是事物的物質基礎,而形式決定了事物“是什么樣”。形式/質料的關系放到文本上,則變成了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敘述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敘述研究首先反對割裂地看待內容與形式。正如黑格爾所說,“內容之所以為內容,即由于它包含有成熟的形式在內”[4]。黑格爾用莎士比亞的杰作《羅密歐與朱麗葉》舉例,說它如果只是在講兩個家族的仇恨而導致一對愛人毀滅,單就這個故事內容而沒有“悲劇”形式的話,不足以造就莎士比亞不朽的作品。其次,對敘述形式的分析要深入到文化意義分析的深度。形式不是隨意打造的內容容器,“任何形式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結構。因此形式的分析必須是對意義形式的分析”[5]。敘述學家趙毅衡也認為,敘述學的形式分析可以而且也必須進行到文化形態分析的深度,“只有深入到產生敘述形式特征的文化形態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一種敘述形式的實質”[6]。
新聞與其他文本類型一樣,都有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兩者之間既有同一性,又存在巨大張力。再考慮到新聞這種真實的、關于當下世界的“鮮活故事”,與個人、與社會之意義關聯的密切,探討新聞“形式”及其文化意義,本應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新聞學研究領域。但遺憾的是,不同于文學領域對“形式”研究的高度看重,傳統新聞研究對事實內容性質的興趣更大,對新聞形式問題則關注寥寥。學者劉建明也提到,新聞報道是新聞理論界的“學術盲區”。[7]究其原因,或許可以說這本就是新聞這種特定文化形式施加于自身的一種“障眼法”。盡管新聞從業者必然要挑選、組裝、結構、凸顯不同的事實,并用特定的符號轉化事實素材,再以相對穩定的風格呈現出來,但這一系列復雜的“制作”過程,向來被很好地隱匿在后臺,新聞敘述者有意讓“事實”作為唯一的主角站在前臺。“讓事實來說話”“展示,而非講述”等敘述“技巧”,在生產“新聞”這一文化形式時則被視為“信條”。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新聞形式的“成功”,反而使得新聞形式不受重視,它很好地隱身了。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學者集中發表了一批被認為是“新聞編輯室”研究的經典著作,他們從組織、科層和專業的角度關注新聞生產的制約因素,提出了一批富有解釋性的概念如“新聞常規”(newsroutine)、“新聞時間”(newstime)、“新聞網”(newsnet)、“新聞考量”(journalisticconsideration)等。[8]有意思的是,這些旨在探究新聞編輯室如何把“事實”制作成“新聞”的研究,都很少關注新聞的“形式”。如甘斯在研究中雖也把媒體的“樣式考量”作為諸多“新聞考量”中的一種,但他認為當時在新聞媒體上通行的、最基本的樣式“都非常穩定持久”。他對新聞樣式的改變也持保留態度,在他看來,“技術的進步時不時即會浮出臺面,但它們似乎并不能改變樣式或故事選擇過程”。[9]因此,不難理解的是,新聞“形式”為什么恰恰是當它無法再如之前那樣運行自如時,才會成為顯而易見的問題。眼下,就是迫切需要重新理解新聞“形式”問題的時機。
新聞形式問題當然與“新聞是什么”或“什么是新聞”有關。新聞學關于這類問題的回答,一般被歸為“新聞價值”或“新聞選擇”研究,也就是考察事實具備什么樣的“要素”,才會被新聞業者視為新聞來報道。但這類研究對“什么是新聞”的問題,回答是不充分的,因為具備成為新聞之潛能的事實,也不會自動變成新聞報道,對從事實到報道過程的研究仍舊是不可缺少的。邁克爾·舒德森認為,新聞的權力主要在于它提供形式的能力,因為事物只有在這種形式中才被宣稱為真實。[10]同樣是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一件事,新聞“這種形式”與現實主義小說、社會事件電影等其他形式的文化意義則大為不同。
如果把新聞報道這種文化形式視為一個文本系統,那么按照系統論的觀點,系統總會“維持邊界“,將自身與其他系統劃分開來。[11]同樣,新聞形式也得有能力維持其自身的差異性,保持與其他形式的明顯區隔,否則新聞就不成為“新聞”,只能淪為其他形式的附屬。系統存在的合理性是因其對社會來說有不能被替代的獨特功能。系統不僅要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還要有能力在環境出現了重大結構變化時,仍能維持系統。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在被其稱為“超級理論”的社會系統論中明確指出了系統需要不斷變化才能持存的道理。換句話說,如果系統自己喪失了維持界限、保持自己差異性的能力,哪怕此時外部環境有利,系統仍然可能失敗。作為形式系統的新聞報道,眼下已經浮現出兩重危險,在系統理論視角下,這樣的危險不可忽視。
一重危險是新聞形式坍塌。正如上文所說,當公眾和從業者不時產生“這難道是新聞”的詰問時,批評的不僅僅是個別報道,而是對“新聞”這種形式還能不能穩固特定文化意義產生了疑慮。若“新聞”與自媒體博主的個人故事、與根據事件或事實改編的藝術創作、與依靠創意和觀念的純宣傳作品等都混同起來,新聞的差異性也即新聞以獨特方式認知世界的力量將大大削弱,公眾也將無法再信任“新聞”這種文化形式可以提供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敘述,更糟糕的是還沒有其他任何形式能夠替代“新聞”的這種文化形式意義。另一重危險則是新聞形式退化。“形式退化”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它指一個形式或結構變得無法保持其原有性質、水準或功能。簡單說就是形式雖然會存活下來甚至變得更普及,但它變得沒有過去那么“好”了。對于文化保守主義者來說,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紐約時報》的古典音樂評論家安東尼·托馬西尼發現,當擴音設備掌控了百老匯,觀眾無可避免地變得較不機敏,并更為被動。同時也改變了音樂劇的每一個元素,從歌詞變得較不細膩和不復雜開始,到題材和音樂風格變得浮夸、豪華和低劣。隨著音樂劇變得“更沒文化素養和更淺顯易懂”,擁有“歌劇品質聲音的歌唱家逐漸邊緣化”,這個藝術類型演變成像《歌劇魅影》和《西貢小姐》一樣的劇情片表演。[12]大多數人可能不會介意,甚至不會覺察到一種文化形式是否發生了退化,但文化保守主義的警告并非都是九斤老太式的過氣慨嘆,它們有助于社會保持對形式在變化和創新過程中可能要付出什么代價的警醒,在行動時有清醒的自覺。當下,新聞形式也有“退化”的風險,包括新聞媒體“足不出戶”地生產大量簡單搬運與加工的信息、在新聞媒體的短視頻賬號下放置大量無法核實的“生活瑣事”、花費大量資源制作缺乏新聞價值的形象宣傳片等。
在外部環境變化巨大的情況下,新聞形式如果要保持活力,就不得不從外界吸收新元素,并在保持自身不坍塌的情況下積極變化,但如何變化才能有利于新聞形式系統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因此維系和發展新聞形式對社會的獨特貢獻?行動者需要對新聞形式以及形式系統變化創新的內在機制有清醒認知,才可能避免因盲目行動而產生的新聞形式危機。
二、什么在決定新聞形式?
理解“形式”,往往是從對形式的類型化開始的。遺憾的是,新聞形式的類型化在理論上還很不成熟,它大多依靠一些約定俗成的“叫法”,很少深入到形式背后的文化意義層次。但實踐中,行動者對新聞形式的創新行動又很多,新聞形式家族不時會增添“新成員”。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形式的劃分,也即所謂的“新聞類型”,通常是混亂而雜多的。如國內一本新聞寫作教材對新聞體裁的劃分竟有125種之多,這就完全失去了把形式類型化的意義。形式類型化本質上是通過簡化和抽取公約數來深刻理解一類形式,太多的“形式”,只能如研究者所批評的那樣“使人發昏的五花八門的劃分標準”。[14]進入數字時代,新聞形式在全媒體環境下又有了很多新發展,研究者干脆用一個表示未知數的“X”來表示形形色色的新聞新形式,也就是在新聞前加上特定的限定語。研究者將收集到的166種“X-Journalism”命名聚類為八種,發現它們并非完全獨立,不同的“X-Journalism”術語可能在不同的類別中重合,但它們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在這八種聚類中,聚焦“特定動機和報道風格”“主題焦點或報道領域”以及“技術或數據驅動方法”的分類與報道文本直接有關,而它們之間也有交叉重合。[14]
新聞文本的“形式”固然很難做到嚴格互斥,但大體上還是有兩類主要的劃分方法,亦即按照“題材”和“體裁”分類。研究者和從業者很早就發現新聞報道對象中的一些事實元素構成了它們成為新聞的理由。這些元素被認為主要是由讀者興趣決定的。1960年的一項研究把當時美國地方報紙上的新聞和讀者評分結合起來分析,發現讀者對含有“名人”“犯罪”“事故和災難”“地方社區”和“社會安全”“教育”“政府行動”“政治”等事實元素的報道感興趣。[15]實際上,這些元素通常會在一些社會議題和社會特定領域中反復出現,從而形成了根據新聞報道事實本身的特點而劃分新聞形式的方式:新聞題材。對新聞題材的劃分沒有統一的標準,除了一些“約定俗成”的“題材類別”外,很多媒體也會按照自己主要關注的社會事實領域來劃分題材。比如新華網上的新聞欄目有46個,大部分都是按照題材設立的。“時政”、“國際”、“財經”、“體育”、“教育”、“城市”這樣的大類顯示了新華網關注領域的全面和綜合,“高層”、“人事”、“政務”、”“一帶一路”等題材類目則顯示國家通訊社在一些特定領域的報道和發布優勢。
若按照新聞報道中素材和符號的生產、組合、表達方式來區分,則構成了“新聞體裁”類型。如按照獲得和加工新聞素材的新聞工作方式不同而產生的新聞體裁,包括新聞訪談、調查新聞、精確新聞、新聞直播等;按照新聞作品使用的主要符號類型和傳播媒介不同而產生的新聞體裁,包括文字報道、廣播新聞、電視新聞、短視頻新聞、數據新聞、新聞攝影、新聞播客等;按照內容組合和表達方式不同而產生的新聞體裁,則包括消息、通訊、特寫、特稿等。恰當掌握關于新聞“題材”和“體裁”的知識有利于提升新聞生產內部分工的效率和質量。但僅從“題材”和“體裁”角度來理解新聞形式,雖然有利于新聞生產,卻很難說清“形式”的實質,也即一種特定的新聞形式對于社會來說有什么文化意義,因此我們還需要引入一種新的劃分新聞形式的思路——按照新聞的文化功能來劃分。
新聞業最基礎的功能是守望,所有的新聞報道都應以不同的方式體現這一功能,也即通過向社會成員真實敘述當下世界,使他們獲得必要的外部信息,并以此調整自己的行動。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評論》上雄辯滔滔地闡述新聞業的功能,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已成為現代新聞業之隱喻的“瞭望者”說。在普利策看來,記者不僅會報道可能帶來危險的淺灘暗礁、大霧和風暴,也會關注好天氣下海平面上出現的有趣事物、遠去的風帆,并提醒船只去解救落水的人。[16]這段話在被多次轉譯后成了更有浪漫色彩的、為世人熟知的名言——“倘若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新聞記者通過新聞工作和報道,了解到公眾無法、無力或無暇去親自獲取的事實信息。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靠新聞記者才能獲得重要事實信息的壟斷性被打破了。社交網絡上自媒體、權威和精英人士、社會組織機構以及公眾無時無刻不在生產和交流關于當下世界的信息,對傳統新聞媒體的權威形成了很大的挑戰。這種挑戰性不僅在于,這些并非是傳統新聞組織的行動者事實上正在做過去被認為是新聞記者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者生產出的巨量信息以及由社交媒體算法主導的信息傳播網絡可能會淹沒新聞報道。新聞報道還能不能履行“守望”社會的功能,以及新聞報道如何在與虛假信息以及網絡信息泡沫的抗衡中重新成為數字時代社會公共認知不可或缺的文化形式?新聞業必須在變化的環境下重新交出對這一新聞形式合法性問題的答卷。
新聞報道不僅“反映”現實世界,還在“反映”中強化社會規范。媒體和社會理論家亞歷山大(Alexander,J.C)認為,新聞媒體對社會規范層面的關注極其重要,正如個人會不斷從各種規范的角度來組織自己的經驗一樣,新聞界則是為全社會這么做。新聞敘述中有強烈的規范性和道德性觀點,將單一事件與更普遍的價值判斷聯系起來。僅僅只是“發生了什么”是無法成為新聞的。[17]新聞報道對社會規范的強化可以從正、負兩個方面進行,分別是“示范倡導”功能和“輿論監督”功能。
我國新聞與宣傳這兩種文化形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們之間存在很大的交集。這一交集中活躍著“正面報道”、“重大主題報道”、“典型報道”等常見新聞類型,在全部的新聞實踐活動中占據著相當高的比例。西方知識界往往不能接受“宣傳”之名,將“宣傳”視為洗腦、欺騙和隱瞞,但另一方面又有高度發達的宣傳知識、傳播技巧。在避免使用“宣傳”概念的情況下,具有明確倡導意圖的新聞報道在實踐中大量存在。如美國“黑人報刊”(BlackPress)就被認為是倡導性新聞業的典型例證,研究發現黑人新聞記者不受“客觀性”概念束縛,從19世紀廢奴運動到21世紀“黑人性命攸關”運動,一直積極為非裔美國人群體服務、說話和戰斗。[18]大量的生態環保報道、女性議題報道等也都采用的是倡導性新聞范式。可見,具有“示范倡導”功能的新聞形式不僅在中外新聞實踐中大量存在,而且具有特定的重要文化意義。但中外新聞學對該形式—功能的新聞實踐都較缺乏基礎理論研究,國內存在用文件解讀代替學理研究等過于政治化的問題,而國外則存在回避和忽視該領域新聞實踐及其新聞作品的問題。
與“示范倡導”一體兩面的是,具有“示警”作用的“輿論監督”。兩者都是能在告知的同時強化、鞏固社會規范功能的新聞形式。如果說“示范倡導”形式選擇的是超出社會常規的、正面的“超常”事實加以報道,那么“輿論監督”則是發現規范被打破的“失常”事例并使其成為新聞。“輿論監督”不是一個體裁概念,而是一個功能形式概念。傳統新聞研究很少區分體裁(文體)和功能的形式分類,這容易在實踐上出現一些認識誤區。比如可能窄化“輿論監督”報道的范圍,認為只有“批評報道”“調查性新聞”等體裁才算。事實上,各種新聞文體只要具備輿論監督功能,都可被視為輿論監督報道。筆者與合作者曾給輿論監督報道下過如下定義:“輿論監督報道是新聞媒體通過對與重要公共利益相關的負面新聞事實進行公開和有明確價值規范的報道,旨在引起公眾關注、促使社會各方面形成共識與合力,最終達到正向社會效果的新聞行動。”[19]這個定義試圖明確地把輿論監督報道放入功能形式類型而不是傳統認為的報道體裁類型,并希望以此在現實條件下推動新聞媒體具有輿論監督功能的各類新聞報道健康發展。
除了“守望”和“規范”外,新聞還具備協調溝通、促進社會共識的功能。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因為階層、地位、年齡、性別、種族、收入、教育、文化等分化機制,社會不可避免地分化。“當子意義世界建立后,人們看待社會總體現實時就會有多個不同的視角,每個視角都來自于某個子世界。按摩治療師與醫學院教授的視角不同,詩人與商人的視角不同,猶太教徒與非猶太教徒的視角不同,不一而足。”[20]個體只有超越自己去了解、理解他人和外在的世界,才可能相互結合而成為社會、成為人類共同體。現代報業在我國發展之初,首先被認識到的功能也是“通”。而隨著一些更加細致的新聞類型的出現,新聞業通過持續報道不同群體的生存狀態和不同的觀點見解,使社會內部的差異性可以被其他社會成員感知到,并以此調節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和行動。越是復雜社會,人們的利益訴求和看待現實的角度越是多元的,新聞業有責任維護好這種健康的多元化信息生態。這也正是為什么“邊緣群體”“冰點議題”等會成為重要的新聞題材類型,而更加偏重理解性的新聞文體如“特稿”“新聞性非虛構”“解釋性報道”“闡釋性報道”“慢新聞”“長報道”等能克服時效性相對弱的劣勢,成為蓬勃發展的新聞形式。
本文認為,僅靠傳統的“題材”和“體裁”分類不足以理解新聞形式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可能是更深層理解新聞文本為何如此、為何變化、如何發展的解釋因素。
三、新聞形式的創新機制
新聞業在面臨環境巨大變化時進行了很多創新行動,以期適應變化和謀求新發展。其中,一種顯而易見的行動目標是:讓新聞產品“重新贏得受眾”。在此目標驅動下,數字時代的新聞業進行了大量的新聞形式創新。但正如前文所述,新聞形式創新行動本身并不一定帶來正面效果,它也可能產生大量關于新聞形式的困惑、退化,甚至會影響新聞的存在根基。因此,理解新聞形式的創新機制就顯得十分重要,這類實踐理論知識將幫助行動者增強對新聞形式創新的自覺和省察,減少盲目性。
文化形式變化最主要的驅動力是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變化。如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所說,20世紀初期中國小說之所以在整體上發生了敘事模式的轉變,也即表現出的作家主體意識強化、小說形式感強化和小說人物心理化的傾向與五四一代所弘揚的個性解放思潮密切相關。“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就不單是文學傳統嬗變的明證,而且是社會變遷(包括生活形態與意識形態)在文學領域的曲折表現。”[21]和其他文本一樣,理解新聞形式的演變也要去探求新聞形式背后變化的“意識形態要素”。如《新聞形式史》的作者將美國報紙上的新聞形式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印刷式、黨派式、維多利亞式和現代式,并強調技術不是導致新聞形式變化的主要因素,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的變化才是。[22]張亞萌、王燦發分析了1921到1949年間中國共產黨報刊新聞文體的演變,認為文體變革受到黨的宣傳政策調整與文體間互動的雙重作用,呈現出與時代進程、革命實踐以及對宣傳規律認識相一致的特征。[23]劉勇則將1949年之后中國新聞文體的演變過程視為宣傳范式、文學范式和專業范式的共生與交融。[24]筆者亦曾在拙著《嬗變的新聞:對中國新聞經典報道的敘述學解讀(1949-2009)》和《新中國新聞報道史暨代表作研究》中闡釋過新聞形式與其時代精神的連聯互構與“雙重變奏”。
但長時段的新聞形式演化史難以直接回答行動者“當下”的問題——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對新聞形式進行某種改動和創造?這是一個典型的具有創新視角的問題:創新理論作為研究視角的價值正在于能提供對系統“躍遷”(同時又不消解系統)的解釋。它不僅關注新行動及其帶來的變化,更要去研究造成變化的條件、方向以及后果,并始終在變化中考慮系統如何“持存”。換句話說,創新理論視角的獨特性在于它堅持在規范與變化的關系中去理解一個系統為何會“發展”。[25]如前所述,決定新聞形式的重要因素是它區別于其他形式的文化功能。那么,我們可以說,站在新聞行動者的立場上,新聞形式創新指向的就是不斷通過外部轉化和內部重組,將新元素內嵌于新聞形式并持續優化其文化功能的過程。
(一)外部轉化
外部轉化,意味著行動者把原本不屬于新聞的元素拿來為新聞形式所用。如作為中國當代新聞文體史之重要節點的“散文式新聞”,其確立的過程就體現了“新聞文體對于散文的借鑒與吸納”[26]。進入數字時代,新聞形式通過“外部學習”的創新大大加速,新聞不斷從小說、散文、故事、戲劇、表演、游戲、歷史、科學等其他形式、新技術以及環境中吸取“新元素”為己所用。如“數據新聞”就是一種因數字時代對“數據”元素的加速轉化而成功完成類型化的新聞形式。人們意識到,“數據”是一種不同于采訪所得“故事”的認識世界的新方式。隨著社會科學方法逐漸引入新聞生產中,用“數據”作報道開始從媒體的偶然實踐變為小規模創新實踐。如《精確新聞學》的作者菲利普·邁耶對1967年美國底特律騷亂的調查發現,在南方長大的黑人只有8%參與了騷亂,在北方長大的卻有25%參與了騷亂,這篇普利策獎獲獎作品用調查數據揭示了當時流行認識的錯誤。[27]“量化”真實等“科學思維觀念”、計算機輔助技術等都推動了基于“數據”的報道成為可能,但獲取和分析數據的高成本、對受眾理解能力的較高要求也制約著當時的數據新聞,使其僅能作為一些媒體的“先鋒性”試驗田。2010年后,以《衛報》數據博客上發表《伊拉克戰爭日志》等為標志的數據新聞才最終完成了它的“類型化”,成為數字時代新聞媒體的一種普遍形式。從零星出現到先鋒性實踐再到成為常規報道形式,數據新聞形式興起并最終擴散成果得以常規化的首要原因是“數據”的豐富性和可得性顯著增強,而大量數據可視化軟件的發展也大大降低了新聞行動者在外化“數據”時的難度。需要注意的是,“數據化”和“數字化”是不同的概念,舍恩伯格等對此的區分是:數字化是把模擬數據轉化成0和1的二進制代碼,數據化則是把現象轉化成可量化分析的材料。[28]所以,數字化不僅助推了數據化,更是通過網絡等傳播基礎設置打通了一切模擬符號的快速轉換,這就是當下新聞形式創新格外繁榮的原因——把外部新元素轉化到新聞形式中的門檻前所未有地降低了。比如,為何當下新聞報道的題材中會出現大量的“普通人新聞”?這不僅與當下普通人話語權和能見度的增加有關,也與傳感器的大量鋪設和社交傳播網絡的發達有關。“普通人的故事”能夠被記錄和捕捉到,是這種與傳統新聞選擇不同的新元素得以進入新聞形式的重要前提。
(二)內部重組
內部重組,意味著行動者要把包括外部轉化來的新元素等多種元素重新組合并穩定嵌入新的新聞形式。這一過程的關鍵是新元素和新組合的方式不能破壞新聞形式自身的穩定,即不能破壞新聞形式與其他文化形式的差異性。比如,“融合”作為我國新聞媒體創新的重要方向,在新聞文本層面的重要體現就是“融合報道”(convergence news)。如其名稱所示,“融合報道”是由多種報道元素尤其是數字時代新出現的媒介技術元素——H5、數字互動、3D模擬等重新組合而成的新聞報道形式,其中每種媒介符號呈現的信息是互相補充而非重復的。但少有人意識到,“融合報道”的名稱也表明多種媒介元素的重組并未真正完成——它更多強調的是多種元素在報道中的“相融”,至于相融后會“合成”什么新形態卻很少被提及。在數字時代大大加快了從外部獲得新元素的創新驅動下,“融合報道”其實是一種具有過渡性質的、對吸納了新元素但又尚未充分完成內部重組的新報道形式的統稱。因此,不難理解,“融合報道”在積極展現數字時代新聞敘述潛力和可能性的情況下,也會因為內部重組的穩定性不夠而產生爭議。如用數字建模制作的虛擬場景可以“栩栩如生”,甚至可能讓人產生“身臨其境”的沉浸式體驗,但如果這樣的“視覺奇觀”沒有或缺乏足夠的事實素材做底,新聞報道就會因為追求好看而失去根基。這樣的問題已經在實踐中出現,甚至出現在獲得新聞獎的“融合報道”作品中。如一則獲獎報道試圖用數字建模渲染清末的十三行場景,為了凸顯國際貿易,該場景還展示了多國國旗,而查證后則發現不少國旗來自于20世紀60年代后才成立的國家。目前,有較多新聞媒體把新聞創新資源投入到開發利用技術新元素上,傾心于把技術新元素“融”進報道后可能帶來的炫酷效果,卻較少考慮經過這樣的外部轉化后能否成功地進行新聞形式的內部重組,往往會生產出“融而不合”、不像新聞的作品。只看重外部轉換新元素,忽視之后的內部重組過程的行動,是違背新聞創新機制內在規律的。這樣做不僅浪費了新聞生產資源,還可能產生危害新聞形式穩定性的產品,應引起行動者的警惕。
(三)功能優化
經過外部轉化和內部重組而產生的新的新聞形式是否有生命力?是長久存在還是曇花一現?是廣為擴散還是有限應用?這些問題需要實踐給出答案,并非出于行動者的主觀意愿。但從新聞形式的演化規律看,只有那些最終被證明能優化新聞形式功能的創新才可能長久流傳,并成為穩定的新聞品類。新聞形式的三大功能:守望、規范(倡導和監督)、溝通,在全媒體環境下都面臨挑戰。如很多事件一發生即被圍觀者手機直播,待媒體趕到現場,事件最初的媒介化可能已經完成。在公民個人和大量社會組織都擁有“自媒體”賬號和“組織機構媒體”賬號后,若有想向社會公開的信息就可以自行傳播,無須新聞媒體用新聞報道作為中介。新聞的守望功能是否會因此衰落,甚至旁落?文藝作品也一直在行使倡導或監督的社會規范功能,一些技術驅動的新元素更容易被不受事實真實性約束的文本類型采用,如電腦特效、互動技術等,因此近些年以非新聞方式出現的創意宣傳發展較快。再加上在數字政務等趨勢的推動下,公民上網辦事、投訴、解決問題的渠道也增加了許多,在此情況下,還需要新聞報道來倡導和監督嗎?再者,許多“網紅”與受眾形成了信任、支持甚至“準親密”關系,他們是否更有可能促成粉絲共同體,而無須新聞報道促進社會溝通?的確,這些都是新聞形式在新的傳播環境中面對的重大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動搖新聞存在的根基。同時也說明,新聞形式無法僅僅通過堅持傳統而維系自身。面對挑戰,新聞形式只有變化創新才可能繼續具備乃至強化本系統的形式功能。分析這些挑戰了新聞功能的新行動者,不難看出,其實他們也各有各的“短板”,新聞形式通過恰當的創新完全有可能變挑戰為機遇,在差異化競爭中鞏固自己的地位。
比如,新聞媒體不僅可以通過加速新聞生產的“即時新聞”或與社會傳播網絡合作的“熱點新聞”繼續維系“守望”功能,而且更應看到在信息過載狀態下公眾對真正重要的環境變動仍然可能是無知的,因為過多的泡沫信息和眾聲喧嘩反而可能阻礙公眾深入了解重要的公共事務。這就是為什么高質量的深度報道和新聞評論具有很大的形式韌性,在新聞媒體財務危機、評論人才難培養等困境下,仍有蓬勃生機的原因。某種意義上,環境變化更加凸顯了這些新聞形式存在的價值。此外,近年來,對抗虛假信息的“事實核查”、引入“數據”、“科學研究方法”等新元素的“數據深度報道”“數據可視化報道”“調研式報道”等形式的興起,也是新聞報道抗衡信息泡沫化,以新方式強化社會守望功能的表現。再如,要優化“規范”功能下的“倡導”,新聞創新不應該走上脫離具體事實的創意宣傳道路,而應該在“用事實說話”的工作方法上尋求新的突破,比如典型報道中近些年出現的與“普通人新聞”結合的新趨勢等。在“輿論監督”上,盡管現在有“打假網紅”“公民投訴平臺”等新事物,但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報道不僅可以在強化權威性、公信力、專業性上下功夫,更應該從單純的新聞生產者進入社會治理系統,扮演好“協調者”角色,使輿論監督報道不僅能引發關注,更能真切地推動社會進步。特稿、新聞性非虛構、當事人敘事、長對話等形式都在努力突破表面的新奇,追求對“和而不同”的多元化社會群體的真正理解,并在此基礎上促進更符合現代公民社會的“理性共識”。
因此,新聞形式當下面臨的危機和挑戰并不可怕,它們都不足以動搖新聞形式存在的基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強化了新聞形式的差異性價值。但需要警惕行動者在危機和壓力下的盲目行動,反而可能會破壞新聞形式創新過程。比如新聞形式演化中不斷出現新聞對娛樂的模仿就容易遭致爭議。有些形式在一度興盛后被新聞業整體驅逐或遠離,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黃色新聞”。“報告文學”與新聞的關系也在幾經討論后被歸置為現實主義文學,國外的政治脫口秀被歸為喜劇而不是新聞,甚至被有些學者稱為一種假新聞形式,等等。但因為娛樂元素、故事元素對受眾有吸引力,傳播者也就常為之折腰,近年來引發討論的“新黃色新聞”不過是新聞又一次過度模仿娛樂后引發的對新聞功能合法性質疑的例證而已。這樣的波動,在新聞形式創新中總會不時出現。外部轉化的可行性與可能效果會激發行動,但對內部重組的冷靜思考以及新形式是否能優化而非損害新聞功能的審慎判斷,同樣是新聞行動者需要重視的。數字傳播環境加速了新聞形式創新的外部轉化,這導致當下的新聞形式創新既活躍又混亂,在短時間內很多過去沒有或不成氣候的新聞新形式強勢崛起,同時對于“四不像”新聞的質疑也日益加劇。而此時,可能需要對新聞形式創新的前一個加速階段適當“減速”,在新聞生產和評估過程中更多關注如何消化被代入到新聞形式中的新元素,重建對數字時代新聞形式功能的規范敘述,“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么出發”。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媒體傳播體系中網絡化新聞業建設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3BXW034)]
參考文獻:
[1]Vosoughi S,Roy D,Aral S The spread of true and 1 news online [J].Science,2018,359(6380):1146-1151.
[2]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M].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53.
[3]曹青云.亞里士多德“質料形式理論”探源[J].哲學動態,2016(10):67-75.
[4]黑格爾.小邏輯[M].賀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33.
[5]曹禧修.敘述學:從形式分析進入意義[J].文藝評論,2000(4):21-30.
[6]趙毅衡.敘述形式的文化意義[J].外國文學評論,1990(12):3-9.
[7]劉建明.消除新聞報道的學術盲區[J].新聞愛好者,網絡首發2024-11-28.
[8]陳陽.為什么經典不再繼續?——兼論新聞生產社會學研究的轉型[J].國際新聞界,2018(06):10-21.
[9]赫伯特·甘斯.什么在決定新聞:對CBS晚間新聞、NBC夜間新聞、《新聞周刊》及《時代》周刊的研究[M].石琳,李紅濤,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02-212.
[10]邁克爾·舒德森.新聞的力量[M].劉藝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11]Parsons,T.amp; Shils,E.A.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07.
[12]桑德爾.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M].黃慧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8.
[13]強月新,單波.現代新聞寫作[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65.
[14]Loosen,W.,Ahva, L.,Reimer, J.,Solbach, P., Deuze,M.,amp; Matzat,L.‘X Journalism’.Exploring journalism’s diverse meanings through the names we give it.?Journalism,2022,23(1):39-58.
[15]Bush,C. R. A System of Categories For General News Content.Journalism Quarterly,?1960,37(2):206-210.
[16]Pulitzer J.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4,178 (570):641-680.
[17]Alexander,J. C.The mass news media in systemic,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E.Katz and T.Szecsko (Eds.),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Beverly Hills,CA:Sage. 1981:17- 49.
[18]Miya Williams Jayne, Advocacy Jour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Rethinking Entertainment in Digital Black Press Outlets,Journalism,2003,24(2):328-345.
[19]王辰瑤,張雨龍.全媒體傳播體系下的輿論監督報道:規范、功能與“解困”[J].青年記者,2024(4):28-35.
[20]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M].吳肅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08.
[21]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
[22]Kevin G.Barnhurst amp;John Nerone:The Form of News:A History.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2001.
[23]張亞萌,王燦發.中國共產黨報刊新聞文體的歷史演變(1921—1949)[J].新聞大學,2022(10):38-49.
[24]劉勇.新中國新聞文體70年:“范式”的共生與交融[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133-145.
[25]王辰瑤.新聞創新研究的進路[J].新聞記者,2024(11):3-18.
[26]李娟.新聞文體“文學范式”的生成與型構[J].未來傳播,2019(8):66-71.
[27]Philip Meyer.New precision journalism: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 Rowman amp;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2.
[28]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北京:湛廬文化,2012:89.
作者簡介:王辰瑤,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創新實驗室主任(南京 210093)。
編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