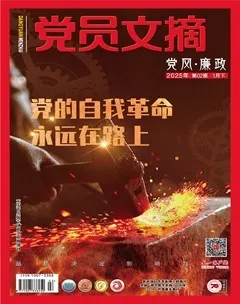三個村莊的逆襲之路
三個昔日或偏遠落后、或寂寂無名的村莊,如何逆風翻盤,分別化身最佳旅游鄉村、塞上主播第一村、露天電影打卡勝地,實現經濟、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的逆襲,煥新鄉村面貌,給出鄉村振興的新答卷?讓我們一起來探尋答案。
最佳旅游鄉村,用綠水青山留住鄉愁
地處武陵山脈南支脈仙女山腹地的重慶市武隆區仙女山街道荊竹村,曾是以種植烤煙為主的貧困村。
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冉光芳記憶中的日子是“天不亮就要去插秧子,晚上又要起來熬夜燒火烤煙,一年累到頭,賺的錢只夠下一年的肥料錢”。
2012年,荊竹村迎來轉機,泥石路被改成瀝青路,叩開通往深山的大門,林海、草甸、天坑、峽谷等多種景觀的旅游潛力逐漸被釋放。2015年,武隆仙女山成功創建“國家級旅游度假區”,荊竹村迎來發展良機。荊竹村抓住機會廣納人才,設立向仲懷院士工作站,聯合各大高校建設合作新場景、新模式;聚攏人氣,引進歸原小鎮等一批文旅項目,舉辦荊竹春晚、大地藝術節等活動吸引游客,帶動村民回村就業;共建共享,村民和各界人士在荊竹夜話為發展建言獻策。經過多年發展,2022年12月,荊竹村成功入選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公布的當年“最佳旅游鄉村”名單。
荊竹村歸原小鎮是由以前的烤煙房改造擴建而來,其“現代創意活化傳統鄉愁”的設計理念讓向往田園生活的游客慕名而來。冉光芳現在的工作地點就在這里。“一開始我只是在這里做清潔,洗咖啡杯。店里咖啡師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看我好奇就教我做咖啡。”冉光芳將學到的內容用本子記下來,常常練習并參加培訓,成功變身為鄉村咖啡師。
2024年國慶假期,均價三四十元一杯的咖啡,她一天能賣幾百杯。“我們一家人都在村里面上班,一年收入大概十幾萬元。每天也不覺得累,還有人專門開車來喝我做的咖啡呢。”冉光芳開心地說。
如今,荊竹村年吸引游客55萬人次,帶動山羊、肉牛、苕粉、西紅柿等農副產品年銷售達2000萬元。荊竹村黨支部書記諶菊感慨:“哪兒能想到今天村里大部分人吃上了旅游飯。”
下一步,武隆區將保護和利用好生態資源,繼續走好旅游致富路,持續放大“世界最佳旅游鄉村”品牌效應,用綠水青山留住鄉愁,吸引更多人回歸田園。
塞上主播第一村,用網絡趟出振興路
在中國的西北角,有一個村子因其獨特的網絡主播經濟而被冠以“塞上主播第一村”的美名。這就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寧縣的大戰場鎮元豐村。在這里,傳統農業與現代互聯網經濟融為一體,創造出了一條令人矚目的鄉村振興之路。

30多年前,一批從寧夏南部山區來到寧夏中衛市中寧縣大戰場鎮的移民,開荒種地、蓋房成家,在這里扎下根來,形成了如今戶籍人口超5萬、常住人口超過9萬的繁榮村落。這一繁榮的景象,在很多農村都難以見到。
交通便利與水利設施的改善,為大戰場鎮的早期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今,互聯網的崛起則成為了推動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元豐村借此機會,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網絡主播,被譽為網絡主播的搖籃。村民通過短視頻和直播,不僅展示自己的鄉村生活,還成功將地方特產推向全國。
面對越來越多的村民希望從事主播行業,元豐村實施了“電商新農人助力鄉村振興”的黨建項目,建設了“黨建引領先鋒助農主播孵化中心”,在主播集中、設施完善、環境良好的巷道打造了主播文化一條街。這一條窄窄的村道,既催生出坐擁百萬粉絲、被抖音官方認證為“鄉村守護人”的“大V”牧颯,也盛滿了全國網友的鄉愁鄉盼。
中寧縣委網信辦主任麻云興說:“我們網信辦聯合商務和投資促進局,從2021年起每年舉辦網絡主播培訓班,每期50人以上,將互聯網法律法規納入培訓課程。”
“有些網絡主播文化水平不高,帶貨直播過程中出現訂單糾紛,黨支部都是第一時間聯系法律援助。融入的最好方式就是成為其中一員,我們鼓勵干部也注冊賬號,加入網絡主播隊伍,拍攝一些展示風土人情、積極向上的內容。今年,我們還發展了一名網絡主播入黨,可謂雙向奔赴。”大戰場鎮黨委書記蘇軍平說。
2024年8月,“塞上主播第一村”的大紅招牌被掛在了元豐村村口。不同于北方農村建筑的單一色調,一些網絡主播家的磚墻涂滿彩繪,攝像頭、手機等圖案告訴人們,這是屬于元豐村的“新農具”。2024年國慶長假,3萬游客涌進元豐村舉辦的美食節,兩天時間營業額達到20多萬元。元豐村黨支部書記李杏梅感慨,3年的變化,比過去10年都大。
中寧縣商務和投資促進局局長于振凱表示:“政府的引導方向與網絡主播的發展需求是一致的,那就是齊心協力,把寧夏的風土人情展示給更多人,把我們的特色產品賣到更多地方。”
四代人接力放映電影,成就露天電影打卡勝地
夜幕降臨,在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洲泉鎮馬鳴村的將軍湖廣場上,不時傳來“噠噠”的膠片走帶聲。百余名群眾圍坐在電影幕布前,與影片中的人物共享歡樂與感動。
在當地,四代電影放映員“接力”放映電影70余年的故事被人津津樂道。
時光倒回7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王志華初中畢業,隨后進入為期半年的電影培訓班,學習放映技術、電工、使用和維修發動機及發電機等課程。一畢業,他便承擔起當地放映電影的任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當地第一代電影放映員。
“那時放電影很艱苦,每個縣(當時仍為桐鄉縣)只有一支電影隊,一支隊伍要照顧二三十個村。”王志華回憶。雖然幾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來越多的觀眾圍上來,他也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義。
1973年,王志華開設了自己的第一期電影放映培訓班,手把手教授3名學生。此后的25年里,他堅持開設了40多期培訓班。
1973年,23歲的朱文炳師從王志華,退伍后在鄉下電影隊放電影。
朱文炳還記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電影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那是大年初一,洲泉鎮人民廣場上聚集了3000多號人,“連樹上都是人”。電影里大雪紛飛,電影外大伙兒穿著厚棉襖,擠著站著看完120分鐘的電影。“當時觀眾太多了,生怕放映機出毛病,我緊張得不得了。”朱文炳回憶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放電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筆寫的電影海報貼上,一個月放三場,10個村輪著放,遠親近鄰統統趕過來,家家戶戶搶著請放映員吃飯。村里的文藝生活相對匱乏,電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對村民而言,也像是一處點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1986年,朱生榮在部隊后勤部門放了三年電影。因為經驗豐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為第三代放映人,背著機器繼續奔波在各個村落。
直到20世紀90年代,當地第一家影劇院建成,銀幕從戶外“搬”進了室內。鄉親們坐進寬敞的電影院,再也不用為“只聞其聲不見其影”而發愁。
有了固定放映場所,本不用再主動“送戲上門”。但朱生榮覺得,總會有一些村民因為路途遙遠不便趕來看電影。他利用在影劇院工作的閑暇時間,和另一位放映員成立了“義馬鄉兄弟電影隊”,把機器裝在摩托車上,專門為偏遠農村的老人孩子放電影,一放就是十余載。
進入新世紀,國內影院開始大量普及數字電影,膠片電影從歷史的長河中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寬銀幕。2006年,朱生榮在隔壁村子的通橋儀式上放了最后一場膠片電影后,默默將跟了他半輩子的“老伙伴”封存進庫房。
朱生榮一度覺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兒子朱強的馬鳴電影機展示館開張。
朱強從小在電影幕布前長大,這位85后的年輕人對膠片電影有著近乎“偏執”的熱愛。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強在杭州辦事過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舊貨的老人正在砸一個老電影放映機,想把上面的鋁殼取下。朱強當即“救下”了這臺老電影放映機。
從此,朱強開始到處搜尋老式電影機和相關設備,牽頭創建了馬鳴電影機展示館。2023年2月,馬鳴電影機展示館升級為“光影故事館”。這是浙江省第一個露天電影文化主題館,也是當地的新時代文明實踐點之一。400平方米的場館,不僅展示了水鄉電影的發展歷程,也保留著百余臺電影放映機及各類老電影膠片,成為鄉村電影文化交流的重要陣地。
如今,馬鳴村的露天電影成了“網紅打卡項目”,吸引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電影愛好者來打卡。“非洲國家的友人都慕名來我們這個小村莊一睹‘光影潤人心’的風采。”朱強說。
(摘編自《新華每日電訊》《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