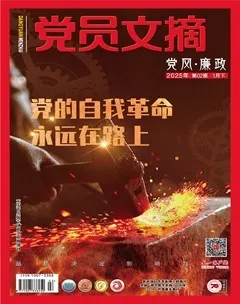不“流水線”、不攀比,這屆年輕人在重新定義婚禮
個性化的婚禮形式日益豐富,一些新人力求“重新定義”婚禮。
民國時期的青年效仿西式婚禮,新潮女性頭戴面紗、身穿婚紗,新人交換飾品,在中西文化相結合的氛圍里走進婚姻殿堂;近一個世紀后,在一些婚禮中,新人取消接親,取消交換戒指,在宴席穿便裝……他們不拘泥于形式,不“流水線”,不攀比,他們在結一種“新”婚。
從拒絕在婚禮上“搭酒塔”開始
2024年10月19日傍晚,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一場婚宴現場,300多位賓客用奶茶、果茶等飲品送祝福,新人舉著高腳杯逐桌敬茶。
“為什么辦完婚禮,新郎一定要醉醺醺地回家?”不想做醉酒新郎,31歲的韋晨昊為自己的婚禮訂購了320杯茶飲。
韋晨昊是一家宴會公司的網銷攝影師,“搭酒塔”是他最不喜歡的婚宴環節。根據當地習慣,“搭酒塔”是將紅包一層一層地疊放在酒杯下面,形成一個“酒塔”,新郎和伴郎在眾人的起哄中,將酒喝完,才能拿走紅包。工作兩年來,他經常看到新郎和伴郎在婚禮上被灌酒。
婚禮前一周,韋晨昊通過朋友聯系到一家新式茶飲品牌,提出為婚禮提供300多杯茶飲的需求。婚禮當天,距離婚宴現場最近的門店調集了十多名員工制作飲品。
受邀的賓客多數是年輕人,許多人第一次在婚宴上喝茶飲,覺得新奇。一開始,韋晨昊擔心長輩喝不慣甜飲,為他們準備了茶飲,每一桌也擺放了酒,有需要的賓客可以自行選擇喝酒。價格上,韋晨昊計算得出,奶茶和酒水的支出差不多,婚禮結束后還退回去不少未開封的酒。
韋晨昊的妻子說了一句令他十分感動的話。她認為,“婚禮的意義是在重要的場合把我介紹給他最重要的人”。對韋晨昊來說,結婚需要一個儀式,但他更希望這個儀式按照新人自己的想法舉行,省去不必要的東西。
“婚是給自己結的”
2024年10月27日,四川省攀枝花市25歲的胥月,為自己辦了一場“禁煙減酒”的草坪婚禮。從接親開始的每個環節,這位主職為圖書編輯策劃的女士都做了個性化設計。
胥月向公交公司租了輛大巴車,一行人坐上48座的浪漫“大巴婚車”,穿梭在攀枝花市的大街上。近來多地公交公司相繼推出婚車服務。
賓客提前得知了胥月辦的是一場禁煙減酒的婚禮。胥月和丈夫都厭惡抽煙,母親有哮喘病,不能吸二手煙,早在籌備期,胥月便以草坪婚禮為理由,告知賓客婚禮不提供喜煙。“相信愛我們的人,會愿意在那一天尊重我們的需求。”她在婚禮邀請函里寫道。
小時候胥月和母親參加別人的婚禮,母親不喝酒也不喝碳酸飲料,和新人干杯時只能臨時用雞湯代替,“在我的婚禮上,我不想沒有媽媽能喝的飲品”。她設置了酒水自助臺,增加了奶茶、果茶、果汁、米酒等飲品。
婚禮前一個月,胥月向賓客發了婚禮調查問卷,發現和預想不同,同齡男性對于煙酒的需求也并不高。她將煙酒預算用于增加迎賓區的移動拍照亭、游園會等,來賓可以參與圍爐煮茶、自制香囊、投壺、猜燈謎等活動。
在婚禮的主儀式上,胥月取消了敬茶改口環節。他們用給父母和好朋友頒獎的方式,表達言語之外的感恩。
因為取消了接親環節,王韻瑤的婚禮躲過了上海市75年來最強的臺風天。
王韻瑤不喜歡“折騰”的接親環節,“儀式和流程應該都是服務于人本身,而不是人去遷就它們。如果大家都樂在其中,那當然是好事;但如果當作一個項目去完成,就沒什么意思”。2024年9月16日婚禮當天,她沒有在凌晨四五點起床洗澡化妝,而是悠閑地睡到上午10點,再到婚禮現場確認準備情況。
王韻瑤與丈夫因《名偵探柯南》(以下簡稱“名偵”)結緣,從婚禮迎賓區的名偵30周年海報圖,到主舞臺上主角告白、親吻的著名場景,從指引牌,到喜糖盒子,王韻瑤的婚禮現場處處透著名偵元素。在他們的陪伴下,王韻瑤攜手佩戴著芙莎繪(名偵角色)胸針的愛人,走進人生下一個階段。
到場的人都被這一場婚禮所驚艷,王韻瑤的奶奶用手機給沒到場的親友打視頻電話“炫耀”。
新穎的婚禮形式很快在互聯網上擴散。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華夏傳播研究會副會長潘祥輝認為,這種傳播方式有助于婚禮移風易俗,推廣新的婚姻觀念。但他同時提醒,新人備婚要防止被婚慶公司利用,面對五花八門的新式婚禮,應量力而行,不能為出新而出新,不顧自己和家庭的消費實力。
“讓父母相信,我們能安排好自己的人生”
王韻瑤坦言,實現二次元主題這場“夢中的婚禮”,得益于開明的家風,她籌備婚禮期間,長輩們只問了何時到達何地,別的一概沒有過問。此外,她認為也和自己經濟獨立有關,“是否有獨立經濟權,很大程度決定了自己的話語權和行為支配權”。
盡管胥月的女性長輩們平時煙酒不沾,但也在她提出禁煙減酒時感到不理解。她們認為婚禮應該按照傳統標準辦,否則容易被說閑話,比如待客不周。飲料奶茶雖然受到喜愛,卻不如名貴白酒般“有實力”“有門面”。婚宴也是展現面子的場合。

“她們認為‘別人會不高興’,只是對過往習慣的盲從和遵照。”2023年胥月和丈夫備婚時,長輩的觀念導致他們一度不想辦婚宴。
舉辦了草坪婚禮之后,胥月發現,父母突然感受到了她的能力,賓客的反應就是最好的答案,“他們好像也意識到了,可以放心地讓我們安排自己的人生了”。
山東省27歲的安深在2024年9月結婚,也取消了接親環節,她無法接受一場意味著“女孩離開自己的家被接到新家”的接親儀式。她和丈夫都認為,婚姻不是一個家庭添丁,另一個減員,而是兩個獨立的個體為今后的生活作出選擇,是自由且平等的結合。
因此,安深選擇了旅行結婚。她和丈夫兩人到四川盆地西部地區旅行,在雪山的見證下,他們結為夫妻,當年她的父母也是這樣的結婚方式。
“時代在發展,等我們這代人做了父母,可能又有另一種潮流。沒必要苛責父母,每代人身上都有時代的烙印。”安深說。
“代際沖突在所難免,因為婚禮對兩代人的意義和內涵不一致。”潘祥輝分析,中國傳統的婚禮不僅是辦給新人的,也是辦給別人,尤其是辦給親朋鄰里看的,父母輩更看重儀式或排場,看重婚禮的“展示”功能。當前一些年輕人更注重婚禮對自己或小家的意義,而非“大家”或他人。
潘祥輝建議,父母輩要更多地尊重年輕人的選擇,將面子、排場、利益這些東西從婚禮中剝離。當然,年輕人也要理解父輩的想法,盡量和父母做好溝通工作。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