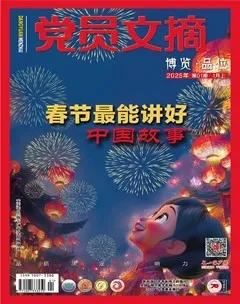追尋延安時期的火紅年味

“除夕之夜,歡樂的氣氛籠罩著我們的村莊。家家窗前點上了燈籠,院子的地上鋪滿了炸得粉碎的紅紅綠綠的炮皮。在那些貼著窗花和對聯的土窯洞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八碗’。”這是作家路遙筆下的陜北春節。作為黃土文化集中區,陜北大地的年味充滿著濃郁的黃土風情:窯洞里,蒸的是黃饃饃,貼的是紅窗花;窯洞外,敲的是震天鑼,扭的是大秧歌。
陜北是革命老區,陜北的春節擁有更多火紅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從新秧歌運動、新年畫運動到雙向奔赴的軍民大拜年,陜北的年味既有“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的熱烈,也有“高樓萬丈平地起”的豪情,更洋溢著“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的自信。
延安時期有哪些火紅年味?革命前輩又如何在艱苦卓絕的戰斗歲月中鼓舞士氣、激揚斗志?讓我們回到那片飛揚著紅旗紅花紅腰帶的黃土地,重溫那段孕育著無數希望、充盈著無限生機的歲月芳華。
接地氣的新秧歌“火出圈”
“小窯洞里,燈光如豆,安波坐在一張小桌子前……一支曲子譜完,感覺不理想馬上就改,只是開頭的‘雄雞,雄雞,高呀么高聲叫’一曲,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臨近春節,冬日暖陽中的延安年味漸濃,修葺一新的魯藝舊址靜候著佳節到來。鐫刻在舊址安波紀念館、描繪“小調大王”安波為《兄妹開荒》譜曲的這段文字,將時針撥回到82年前那個年味十足的春節。
1943年春節,延安城中鑼鼓喧天,一場精心籌備的軍民聯歡會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上拉開大幕。盡管黃土飛揚,天寒地凍,但正如臺下安波的回憶所言:“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從平地豎起。”
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來自魯藝的藝術家們在“文藝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號召下,將創作之筆對準人民、用群眾語言創作后的匯報演出。
“挑起擔兒上呀上山崗,一頭是米面饃,一頭是熱米湯。”在兩萬多名軍民的翹首以盼中,王大化身系紅腰帶,頂著陜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臺,身邊是穿著花棉襖的李波。兩人唱的是陜北秧歌調,扭的是陜北秧歌舞,演的是陜甘寧邊區農民馬丕恩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產”的勞模事跡。雖然缺乏專業場地,也沒有高端音響助陣,但在觀者潮水般的叫好聲中,以勞苦大眾為主角的《兄妹開荒》,火了!
“《兄妹開荒》轟動了整座延安城,火到什么程度?《解放日報》配發了社論,刊登了曲譜。王大化和李波成為那個時代的‘頂流’,市面上出現了王大化牌的香煙、肥皂。”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劉妮說,“當時群眾到魯藝看秧歌劇,不說劇名,都說‘去看王大化’。陜北原來只有秧歌調、秧歌舞,沒有秧歌劇。魯藝的藝術家們拜群眾為師,通過田野采風,在民間藝術的基礎上去粕存精、提煉創新,開創性地發掘了有情節、有故事的秧歌劇。”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兄妹開荒》橫空出世,新秧歌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新的內容、新的藝術形式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在秧歌劇的基礎上,魯藝發展起了新的歌舞形式、新的歌劇形式。到1944年春節,延安工廠、學校、部隊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個,上演了150多個節目。延安到處充滿了欣欣向榮的節日氛圍。”延安魯藝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強說。時至今日,當年被群眾熱捧的經典秧歌劇,仍是陜北不少地方的春節年味。
被搶購一空的年畫是啥來頭?
走進延安文藝紀念館的新窗花、新年畫展區,仿佛置身于除夕之夜的陜北農家。窯洞造型的展墻上,一格格新窗花淳樸厚重,流露著歲尾年初的富足安樂。而一幅幅新年畫則像春節的“連環畫”一般,于不動聲色中娓娓講述著革命戰爭歲月里的年畫傳奇。
1940年1月31日,農歷臘月二十三,北方地區傳統的小年。在晉東南的太行山敵后抗日根據地,時任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的胡一川,和同伴一起背著大包去趕集。包里裝的是木刻工作團為配合抗日宣傳,突擊了好幾個日夜趕制出來的水印套色新年畫。
彼時,全國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鐵蹄正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而瘋狂的掃蕩。《紡織圖》《保衛家鄉》《大家養雞增加生產》……人來人往的大集上,由于價格便宜、畫風新穎,這些鼓舞斗志、充滿民族氣節的新年畫,很快被前來買年貨的山西老鄉搶購一空。
作為民間最盛行的年俗之一,年畫是我國特有的春節裝飾品。抗日救亡大潮中,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年畫,也成為對敵斗爭的陣地。
胡一川、彥涵、羅工柳等來自魯藝的美術家,請來當地的年畫工人作指導,在木刻版畫的基礎上,創新采用畫面明朗的傳統年畫進行抗日宣傳,以門畫、連環畫、四扇屏等多種形式,全景式表現保家衛國的主題。很快,群眾家的“門神”由原來的秦瓊、尉遲敬德,變為英姿颯爽的八路軍戰士,大批新年畫陸續進入千家萬戶。
“這些來自土窯洞、沾滿泥土味的美術作品,對中國革命進行了廣泛的動員和宣傳,并在黃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結出了果。”劉妮說。
雙向奔赴的春節大拜年
“1944年春節,新秧歌活動鬧得更紅火了……橋兒溝鄉的秧歌隊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魯藝院內拜年來了……我很喜歡那位老傘頭領唱的秧歌調……唱出了與解放了的人民之間的親密無間的情誼。”
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藝紀念館收藏的李煥之著作《音樂創作散論》。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拜年方式,往往簡單淳樸又情意濃濃,除了秧歌拜年,還有座談聊天,或是互致問候。”延安職業技術學院紅色文化教育培訓中心教授高慧琳說,比如,1945年農歷大年初一,中央領導帶著警衛員到棗園鄉政府給群眾拜年。其間,陜甘寧邊區的勞動模范也來給中央領導拜年。

蔬菜、雞蛋、黃酒、油饃……延安時期,軍民之間的新春禮物,往往就是小雜糧和農家土特產。1943年春節,“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雙擁運動”在延安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正月里來是新春,趕上了豬羊出呀了門。豬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英勇的八路軍。”首演于當年的《擁軍秧歌》,以質樸熱烈的唱詞,勾勒出軍民魚水情深的熱鬧年味。
延安時期,軍民之間的春節大拜年可謂是雙向奔赴。1943年春節,毛澤東得知棗園村有24名60歲以上的老人,其中2名老人正月十五過生日,便在元宵節當天宴請24名老人,飯后給每人發了一塊香皂、一條毛巾,還請大家看了場電影。
有一年春節,秧歌隊來楊家嶺拜年,有戶人家住在后溝里,因為要保障春節供應,忙著磨豆腐,顧不上看秧歌。毛澤東得知后,請秧歌隊專門繞到豆腐坊,給那戶人家扭了場秧歌。
“人民這么擁護共產黨,根本原因是共產黨讓勞苦大眾找到了做人的尊嚴。”陜西延安干部學院副院長楊曉紅說。正如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的所見所聞: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因為“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窮人分到了田地,娃娃能上學;很多工人過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

“共產黨領導下生活的巨變,是延安時期火紅年味的現實土壤。”楊曉紅說,“春節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佳節,勞動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里,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樸實也最隆重的方式,表達翻身做主人的喜悅,表達最真實的歡暢。而藝術家們通過深入群眾,創作大量接地氣的年畫、秧歌劇等文藝作品,為群眾代言,用藝術禮贊這種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時代。”
當春節的腳步臨近,今天的革命圣地,火紅年味歷久彌新:悠揚的民歌唱起來了,歡騰的腰鼓打起來了,熱情的秧歌又扭起來了……
(摘自《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