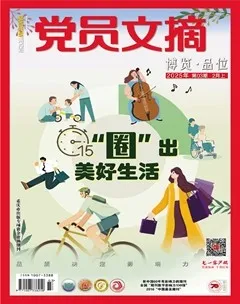上海“15分鐘社區生活圈”進階之路
早在2014年,上海在全國率先提出“15分鐘社區生活圈”概念;2016年,上海制定發布全國首個“15分鐘社區生活圈規劃導則”,并納入《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簡稱“上海2035”)。
在上海的城市實踐中,“15分鐘社區生活圈”是在市民慢行15分鐘可達的空間范圍內,完善教育、文化、醫療、養老、休閑及就業創業等基本服務功能,提升各類設施和公共空間的服務便利性,構建的是以人為本的“社區共同體”。
“圈”在進化:承載起全年齡段人群需求
中午,上海市普陀區曹楊新村街道黨群服務中心武寧片區,社區食堂里的人絡繹不絕。數據顯示,這里日均客流量達1300多人次,在上海社區食堂里名列前茅。
曹楊新村街道黨工委書記許春輝介紹:“根據后臺大數據分析,我們保留了清蒸鱸魚、紅燒牛肉等受歡迎的菜,淘汰了重油重辣的辣子雞等不受歡迎的菜。食堂還和社區衛生中心聯動,推出春日健康藥膳,比如核桃炒春韭、金橘檸檬飲等。”
2024年,上海社區“寶寶屋”也實現了全市216個街鎮(鄉)全覆蓋。在萬里街道社區生活服務中心,上午9點,在外公外婆的護送下,3歲的萌萌開心地走進社區“寶寶屋”。與“寶寶屋”隔一面玻璃墻的,是萬里街道綜合為老服務中心。這一面玻璃墻的巧妙設計,讓一老一小有了互動交流。

在上海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里,有很多像這樣集社區食堂、社區衛生中心、文體活動室、托老托幼等于一體的黨群服務中心、鄰里中心,已成為承載市民服務功能的重要載體,甚至成了網紅打卡點。
據上海規劃部門介紹,以前的綜合性公共服務設施一般以街鎮為單元配置,如果街鎮面積太大,或是形狀不規整,就可能出現設施布局不均衡、出行距離較長等情況。在居民日常生活中,還是缺少能把所有功能集中起來的綜合性公共服務設施。
為了解決這些痛點,“15分鐘社區生活圈”應運而生。如今,上海已形成約1600個社區生活圈基本單元。上海“15分鐘社區生活圈”逐步完成載體建設,正以整個街區為單位,承載起全年齡段人群從日常生活保障、安全、歸屬,到學習、交往、創造等各層面需求的美好愿景。
上海16個區各具特色,各街鎮的城市空間和功能優化面臨的情況也不同。未來上海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建設,將更因地制宜、創新方法,越來越呈現個性化。
“圈層”進階:文體空間豐富多彩滋養人心
在社交平臺上常常能看到這樣的感慨:上海的社區已經“Next Level”(新高度)。家門口的公益閱讀場所提供當季新書,居民有心儀的書目,還可以向工作人員“點單”;位于郊區的一些閱讀空間,不僅24小時開放,還提供了兩三百冊全英文繪本……
這些直指全年齡段人群需求的貼心甚至“超前”之舉,都是上海打造“15分鐘社區生活圈”所作出的探索。
80后朱云是嘉定區菊園新區綠地·天呈小區居民,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們遇見時,她正在家門口的“我嘉書房”,邊讀烘焙類書籍邊做筆記。“這本書講得特別細,比網上的教程還要好。”朱云表達了對“我嘉書房”選書的認可。

在空間資源較為匱乏的中心城區,各區、各街鎮都在挖空心思盤活、利用一切可用之處。
虹口區涼城復旦小區曾經并不起眼的門口,如今成了前衛的“門衛美術館”。在其不遠處,由小巷書屋升級而來的“小巷美術館”,既保留了書屋功能,又增加了美術館兼容空間,促成了居民喜聞樂見的“美術館式的讀書會”環境。
在普陀區甘泉社區,原本屢遭居民投訴的垃圾回收站,搖身一變成了集裝箱房形式的“青立方”市民健身中心。近2000平方米空間內,包含了7片羽毛球場、2個乒乓球桌、1個飛鏢館、1個桌球房和1個體操房,以及市民體質檢測站。
眼下,越來越多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手持一本“護照”便可在家門口接觸到世界一流的藝術人文教育資源。
2024年,靜安區聯手上海蘇富比空間、尤倫斯美術館等藝術場館,推出蘇河灣區域“藝術觀賞護照”,讓周邊的學生、居民和白領在藝術氛圍“拉滿”的高品質公共空間與優質人文資源“親密互動”。
不在頂級資源集聚的“宇宙中心”怎么辦?寶山區的做法是,打造“小而美”的文化空間與服務。2024年3月,首發項目——位于大場鎮祁連公園內的寶山社區美術館·公園里正式啟用,受到周邊社區居民的普遍歡迎。
還有一種原因不容忽視,那便是社區主體的參與熱情。涼城復旦居民區和涼城三村居民區的社區干部有著共同的體會,“門衛美術館”“小巷美術館”開放后,社區氛圍變得更加融洽。藝術仿佛一把金鑰匙,打開人的心門。從前互不認識的、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因為藝術而相遇,相互交流起來。
誰在造“圈”:凝聚社會自治共治力量
15分鐘,不只是一個時間尺度,更是衡量生活便捷度與幸福感的標尺。
2024年10月,北外灘街道的“濱芬食光·熊貓飯堂”開業。72歲的居民郭奇章去嘗了一次后,向街道干部提了兩個建議:“半份菜”的標識能不能醒目一些,讓老年人看得更清楚;每天能否推出一個特價菜,讓一些生活不太富裕的老人也能來吃。
郭奇章是一名社區“議事員”。從飯堂籌備到建設,再到建成運營,他和周邊三個居民區的居民代表全程參與其中。“在菜品設置、定價標準、運營方確定等關鍵環節,街道組織我們開了好幾次意見征詢會、溝通會。飯堂開業后,街道又邀請我們去品嘗,提意見。”郭奇章說。
伴隨“15分鐘社區生活圈”建設的深入,上海各社區搭建起多種形式的社區民意傳遞與收集通道:線上線下的調查問卷、人民建議征集、居民訪談、社區大討論,邀請市民作為“監督員”“議事員”等。完善的群眾參與機制的建立,讓群眾成為“15分鐘社區生活圈”的“功能決策者、過程參與者、建設監督者”。
上海“15分鐘社區生活圈”不僅是宜居圈,也是宜業、宜游的“朋友圈”。只有讓“圈”內的不同主體、不同平臺發揮優勢,一起參與“造”圈,“15分鐘社區生活圈”的內涵才愈發豐富。
上海還將“社區規劃師制度”寫進城市總體規劃,楊浦區依托同濟大學,選聘規劃、建筑、景觀等方面的專家教授擔任社區規劃師;黃浦區依托華建集團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為建設“15分鐘社區生活圈”提供專業支持。
以外灘街道山東北路更新項目為例,規劃師董怡嘉將更新的著眼點聚焦在山東北路人行道上,打造了一段可呼吸的“海綿式平臺”。平臺高處種了四季常青的綠植,低處打造了座椅。她說:“社區規劃師是城市觀察者,帶著專業的視角在社區中尋找各種不起眼的空間;也是一個媒介,將居民需求與空間緊密結合。”
這兩年,上海各社區大多數民生服務與項目都圍繞著建設“15分鐘社區生活圈”開展。熱火朝天的背后,能否撬動更多的力量、連接更多的資源參與造“圈”,考驗著社區治理的能力。
(摘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