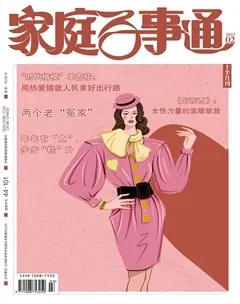人生不過三場雨

年少時熟背過唐宋時期的一些經(jīng)典篇目,那些平平仄仄的句段里有著無限美好的唐宋風光,而蔣捷的那首《虞美人·聽雨》,始終在我的心頭縈繞。
我家住在四樓,西邊戶的橫廳有一長串的玻璃,隔著玻璃是樹齡近百年的梧桐樹。春天,樹上小小的嫩芽冒出來,隨著一場接著一場的春雨漸漸長大,顏色也從早春的新綠到夏日的深綠色。到了深秋和初冬,巴掌大的梧桐葉子漸漸從青黃到紅褐色。每逢下雨天,我在窗前讀書,寫字,雨點打在梧桐葉子上,蔣捷的這首詞作就不自覺在我心頭泛起波瀾。
由此我想到,人生的一生,也大抵是這三場雨。
年少時的雨,多少是浸潤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思,也帶著些許天真和爛漫,“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大概是因為年輕,對紅塵世事充盈著追逐、向往、努力,在此追逐過程中,有很多困惑、迷茫、不解、沖動、莽撞……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們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悟。我們都曾在那場雨中追逐過、淋濕過、哭泣過,哪怕當時的我們在雨中沒有傘,但依舊盡興。當懂得如何珍惜和把握機會時,我們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回不到年少時的那場雨中了,那場年少的雨,來得快去得也快,終究是鏡中花與水中月。
而壯年時的雨,那是擁有一定的人生閱歷之后的自我認知、自我救贖。蔣捷寫道:“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這是中年游子在客舟中的惆悵,回望小半生已過,大約有遺憾、有離別、有悔恨、有不甘、有不舍……每個遠離故鄉(xiāng)的人,會在中年時對鄉(xiāng)愁產(chǎn)生格外清晰的自我認知與注解。年少時想到“好男兒志在四方”,不做井底之蛙,世界那么大,要出去看看。幾年下來驚覺,異地的美食再豐富,可能還是沒有兒時母親腌制的咸菜、醬瓜可口;異地的風景再美,可能還是沒有家鄉(xiāng)的小河親切、靈動;異地的朋友再熱忱,可能還是沒有家鄉(xiāng)的親友掏心窩……中年的聽雨,是在回味小半生的雨聲。記得母親當年無論如何也挽留不住我遠嫁的心,臨了無奈地對我說:“只有等你有了孩子,你才能體會到!”如今想來,這話就如同那場回不到從前的雨,那場雨和雨中人始終無法同頻,等雨中人領悟真諦,那場雨已經(jīng)結(jié)束。
晚年時的雨,大抵帶著悵然。蔣捷寫道:“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晚年的他,白發(fā)蒼蒼,臨時寄宿在一簡陋的僧廬之下,窗外是雨,點點滴滴,雨未停、他未眠……或許他想到的是這大半生的人情世故與悵然別離,人間有太多的陰晴圓缺、悲歡離合。人生本是一趟單行線,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實不斷在和別人告別。有的人可能在你毫無防備之時,輕描淡寫地說出“再見”,后來就真的再也見不到……
從蔣詞中深悟這三場雨,除了惆悵,當然也有啟發(fā)。古人云“晴耕雨讀”,晴天時忘我工作,雨天時不妨坐下來好好讀書和思考,臨窗聽雨,捧一杯熱茶,給自己一些身心休息和調(diào)整的時間。雨夜里也許伴隨著雨聲,生出絲絲惆悵,忽然分外思念故鄉(xiāng)、故人,那么等雨停了、天晴了,不妨立刻驅(qū)車去看看故鄉(xiāng)、訪訪故人。
因為人生不過三萬天,人生不過三場雨。
編輯|郭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