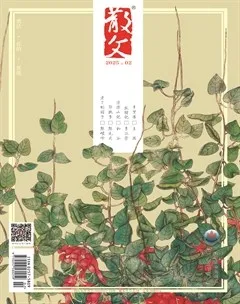清涼山記
居長安三爻,抬腳可登清涼山。三爻,是隋文帝大興城南的第三處山梁。因山上有清涼寺,便名為清涼山。讀寫之余,散步歇腳,所思所感,隨手記之,曰:清涼山記。
一
偶爾在書架上取出一本小書, 是契訶夫的《草原》。它等我許久許久了,孤寂地等我的體溫。
1888 年的作者寫下此書,百年之后的我讀到,仍眼前一亮。一個九歲的孩子,隨大人走過草原, 目之所及是牧人的生活情景。沒有驚人的事件和傳奇,卻透過平淡而詩意的文字,傳遞出背后的情感魅力,讓人愛不釋手。
小書裝幀潔雅, 小三十二開本,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印,定價四角六分。舊書的主人戈黃在扉頁上簽名鈐章, 它是如何被掃地出門,流浪于舊書攤,被我什么時候從哪里揀回,已經不記得了。
二
前不久去了張載祠,除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外,他的氣體論亦被視為認知世界的論斷,是說大自然中一切可視的物象皆源自氣。氣聚,則存在;氣散,便消失。
那么一個人的存在,俗話說“人活一口氣”,咽氣便亡了。又說物質不滅,人亡后化為另一狀態而存在,只是不可視見而已。也恐怕是量子說的平行空間之存在。說話的人沒死過,未經實踐檢驗是否為真理,也只是一種類似“上帝說”的自我安慰而已。
人的肉體百年會腐, 木質器物千年也爛,鋼鐵礦物質亦然。而源自土與火的陶瓷永世不滅,證明土地永恒,天地永在。
氣,是空氣,空而不空。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念叨念叨阿彌陀佛,聊以自慰罷了。
三
叔父成有打電話,索要《和氏家譜》電子版,想補記近二十年家世演進文字。家譜是我從海南島重返故城后協助叔父在2002 年修訂的。及時續譜,是先人序言中叮嚀的,不敢忘卻。
續譜附錄,應錄入2016年在老縣城高坪發現的一塊碑的碑記,是1903年去世的老老老祖父時雍(自謙)公撰文并書丹,公時年九十上下。
我從電腦中搜索出這篇碑文, 將學弟秦隴華圖文轉發于博客公示, 一以抵制遺忘,二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閱,不亦樂乎。
窗外冬陽燦爛, 金黃的銀杏葉翩然飄落。葉落歸根,人亦如此。
四
一位朋友發微信說, 正辦簽證去美國帶孫子。
多年前, 我遇到她帶幾歲的兒子到海南島玩,她對調皮的兒子說:你看,叔叔的兒子都考上清華了。她兒子說: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
之后,她兒子果然不食言,上了清華。她說:人家叔叔的兒子都到美國讀博了。她兒子說:我也能。
再之后,她的兒子果然也去了美國讀博。
幾年后的一天,她的兒子學成探親,在西安上島咖啡請我坐坐。他說起小時候在海南島的那次相遇, 如今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是步學兄后塵一路前行的。我把兒子的聯系方式給了他,供他們交流。
盡管陰差陽錯二人一直未能謀面,但通過互聯網對話知道, 后來人與先行者在異邦立足都不易。
你看,她兒子已經在那里謀職,娶妻生子,要她去帶小孫子了。我的孫輩生在那里長在那里,已到上大學的年齡了。
然而,我們只是在思念中漸漸老去。在這秋風落葉的傍晚,為此回憶而悲欣交集。
五
昨在東木頭市一家酒樓宴飲時, 母校劉教授說到大音樂家劉熾,說:你寫劉熾傳合適。
我說,前幾年寫了《柳公權傳》,寫了《音樂家趙季平》,劉熾傳值得寫,但如今拿不起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 我在西影廠招待所寫電影劇本《石魯》,有一天來一老者,說他是劉熾,延安時代他與石魯住在清涼山的石窟里,同是所謂紅小鬼,拍石魯的電影,他是當仁不讓的作曲。
我向前輩致敬,贊同老人的提議。出生于西安甜水井的劉熾,所作的《讓我們蕩起雙槳》等歌曲家喻戶曉,不勝枚舉。
他回京后還寫信詢問電影進展情況,拍攝計劃已列入副廠長鄭定于老師辦公室的板報, 初定張子恩導演, 后因劇本涉及“文革”計劃擱淺。
去年有導演找我,重提拍《石魯》,我與石丹電話聊了,又未如愿。
舊事一樁,說說而已。
六
千耦其耘,出自《詩經·周頌》。耦,二人并耕。千對農人在耕作,是對西周農業生產勞動場面的描寫。昨日參加“千耦其耘:梁耘師生畫展”,我說了幾句。
梁耘的繪畫實踐始于我的家鄉銅川陳爐,我前不久偕妻在陳爐繪瓷,聽老人說梁耘從美院畢業后在此地參加工作。鄉情使然,我與他交集幾十年,印象深的是他畫范寬《溪山行旅圖》摹本的照金,還有黃陵柏。
我寫了《柳公權傳》后,他催促我寫范寬, 還一起求證照金一個叫范家砭的古村落可能是范寬的故里。他對范寬的繪畫風骨一往情深, 承傳其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理想,成就斐然,并帶起家鄉千耦其耘,功不可沒。雙木成林,三木為森,蔚然大觀。
出席畫展的有崔振寬、程征等畫壇翹楚,與耿建等鄉友一聚,不亦樂乎。
七
今《人民日報》發表拙文《在家鄉打酸棗》,系前些日子在老家所見聞。
耕地邊緣或荒野的野生酸棗, 如今比小麥值錢, 自然生長的紅棗母本的酸棗紅火了。這是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亦是鄉村人氣凋零的真相。
懷舊,是老的征兆。鄉愁,比酸棗還酸心。
八
遇到黃機與洪昇。
己亥夏末, 小住西湖邊的中國作協杭州創作之家,別墅在靈隱路上,禪寺抬腳即到。茂林修竹,開闊處是白樂橋龍井茶的種植區,北高峰的索道凌空飛過。
午后信步踏入石板小路, 兩旁是一畦畦的茶田。有一些茶田荒蕪, 野草比茶畦高。一茶農在畦間鋤草,周圍的茶田長勢不一,參差不齊。
石板小路的盡頭有一尊高大的石碑,背靠翠嶺。走近仰望, 碑文有少許文字可辨,碑腳有一小標志牌:黃機墓碑。碑后有一處被草木掩蓋的小丘,當是碑主的墳墓。石碑傾斜了,僅占有茶園一二平方米土地。
黃機(1612—1686),清初名相,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黃機在官近四十年,兩袖清風,人稱太平良相。按《黃氏世譜》,此處應有墳墓三座。黃機之父黃克謙官至廣東參政杭州右衛所指揮使,兒子黃彥博官至庶吉士,祖孫三代為進士,均葬在此處。
比黃機更為世人所知曉的, 是杭州戲劇家洪昇。黃機是洪昇的外祖父,洪昇之妻黃蕙又是黃機的孫女。黃機還曾給洪昇詩集《嘯月樓集》作序。
洪昇(1645—1704),為南宋名臣洪皓之后,高祖洪椿任明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洪起鮫在清初也曾出仕。洪昇憑代表作《長生殿》,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并稱“南洪北孔”。洪昇生于世宦之家,康熙七年(1668)北京國子監肄業,歷經二十年科舉不第,白衣終身。他的傳世之作《長生殿》歷經十年,三易其稿,問世后引起轟動。次年因在孝懿仁皇后忌日演出《長生殿》而被劾下獄,后人嘆曰:“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
洪昇晚年歸錢塘,生活窮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寧織造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長生殿》,洪昇應邀前去觀賞,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 于烏鎮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終壽六十。
經典戲劇《長生殿》,作者寫出了帝王的愛情傳奇,七夕密誓之后,漁陽鼓動地而來,他們終于自食苦果。
十多年前, 我參與過西安華清池實景舞劇《長恨歌》的編劇和顧問工作,細讀過《長生殿》劇本,對洪昇充滿敬意。眼下,在靈隱路小住時,卻不經意走近了他,感慨萬千。而其機緣,竟是龍井茶園石板小路旁的高大石碑所提供的。
那么洪昇的墓碑在哪里? 有待遇見。
九
鳳鳴于岐,翔于雍,棲于鳳,神話化為現實,此地名鳳州,今稱鳳縣。
三十年后我又來。
百度搜索,《鳳州城記》刊于《散文》1988年第3期。
之后為陜西電視臺的一個系列專題撰稿,講述航天基地科學家張貴田事跡。他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回國, 來到這片群山環抱的僻壤, 從事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液體發動機的研制,貢獻卓著。地處鳳州的紅光溝,嘉陵江源頭的科學之神,如火鳳凰,光耀太空。
早在抗戰時, 外國友人艾黎曾在此進行工合運動,舊居的窯洞尚存。
在兩當起義策源地紀念館, 重溫革命前輩的足跡,從此地至照金至延安,血與火的歷史,堪比神話。
靈官峽, 是嘉陵江邊寶成鐵路游覽景地,云霧繚繞,奇峰蒼翠。世人知此地,緣于作家杜鵬程的散文《夜走靈官峽》入選課本,給幾代人留下深刻印象。江水仍在崖下流動,時間流逝,而人文精神永傳。
鳳縣,奉獻,聽此地人說這兩個詞,同音,亦同義。
十
文友發來微信,圖片加文字,問:此人是不是你寫的《市長張鐵民》的秘書? 我一看是胡太平,怎么在昨天去世了。胡太平恪盡職守,官至副省級檢察長,六十五歲,令人惜惋。
1984 年秋天,我采寫鐵市長,胡太平任市長秘書,三十歲,風華正茂,厚道實誠,作為向導和我騎自行車大街小巷穿梭,采訪數十人,幫我梳理張市長生平,始成文稿。
三十五年過去,雖再不曾謀面,還是關注著他的蹤跡。
斯人已逝,我找出發表于《人民日報》的《我寫鐵市長》一文,重溫提及胡太平的文字,歷歷往事,如在昨日——
一個秋雨天的午后,我如約騎車子趕到了省醫院干部病房采訪鐵市長。秘書胡太平在門口等我,帶我走進一樓南面的一間病房。市長顯然是剛剛接受完治療,從病床上走到外邊的會客室。他很爽朗地笑著,吩咐我坐在沙發上,然后點燃一支煙親切地同我攀談。
談到采訪,張市長真實的想法是:原先是不愿意讓人寫他自己的,現在想想,快到站了,總結一下工作也好,有經驗也有教訓。我為他的坦率所感動。他特意提醒我,寫的時候要注意分寸,不要只寫了他的好而顯得別人不好。他讓我先多聽聽別人的意見,然后需要他談什么,他會坦誠地如實講出來的。他一邊說,一邊給胡太平交代,提到需要采訪的市委、市政府及一些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還把熟悉情況的一些人名讓我記下來,由胡秘書負責聯系。
接下來,我和胡秘書相約,由他引見或聯絡, 我有時乘車有時騎車,有時還步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追尋“鐵市長”的足跡。
《市長張鐵民》很快在《延河》1985 年第五、六期發表。當我把刊物送到張市長的手里時,他真切地說:謝謝。后來我問過胡太平, 他說市長是在病床上斷斷續續讀完的,醫生多次勸說市長不能再勞累,要好好休養。誰知沒過幾個月病情嚴重惡化,一口氣沒上來,就離開人世了。
十一
看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是對止戈傳媒創立者孫春龍的訪談,很生動。
孫春龍生于1976年,他說在我的老家屽村讀書時,受到我作品的影響,步后塵做了記者。又從新華社辭職,成立深圳龍越公益機構,做“老兵回家”項目,尋找遠征軍老兵遺骸回家。后在昆明創辦止戈傳媒,呼喚人類和平。
德國作家阿倫特說:“每次你寫了什么東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變成了公共事務。”這是傳播的價值所在。從私人或者從一種隱秘的角落走向公眾, 走向大家都會思考的問題, 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傳播的價值。
從新聞到紀實文學, 其寫作的意義與價值,恐怕也不過如此。
十二
讀伯濤海南詩, 偶成: 別離海南二十年,依稀夢里海連天。今詠老友伯濤詩,盡是酸辣苦甜咸。東坡花甲歸去來,吾輩還鄉愛田園。莫道天涯與海角,冬日遙寄寸心寒。
順記趙伯濤《海南之海》——
在海南,痛飲一杯水
把海用淚水隱藏
生命總是從丟棄處啟程
船
像一條逃亡的魚
人,是一滴迷路的水
坐在大海的桌前
嚼著血的咸
在海南,有人跳下了海平線的背面
明天沒有謎底
1988已經老去,青春的紅珊瑚
依舊在海底
舉著海洋
責任編輯:施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