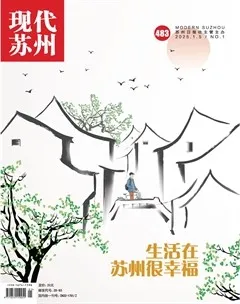凡是生活,皆可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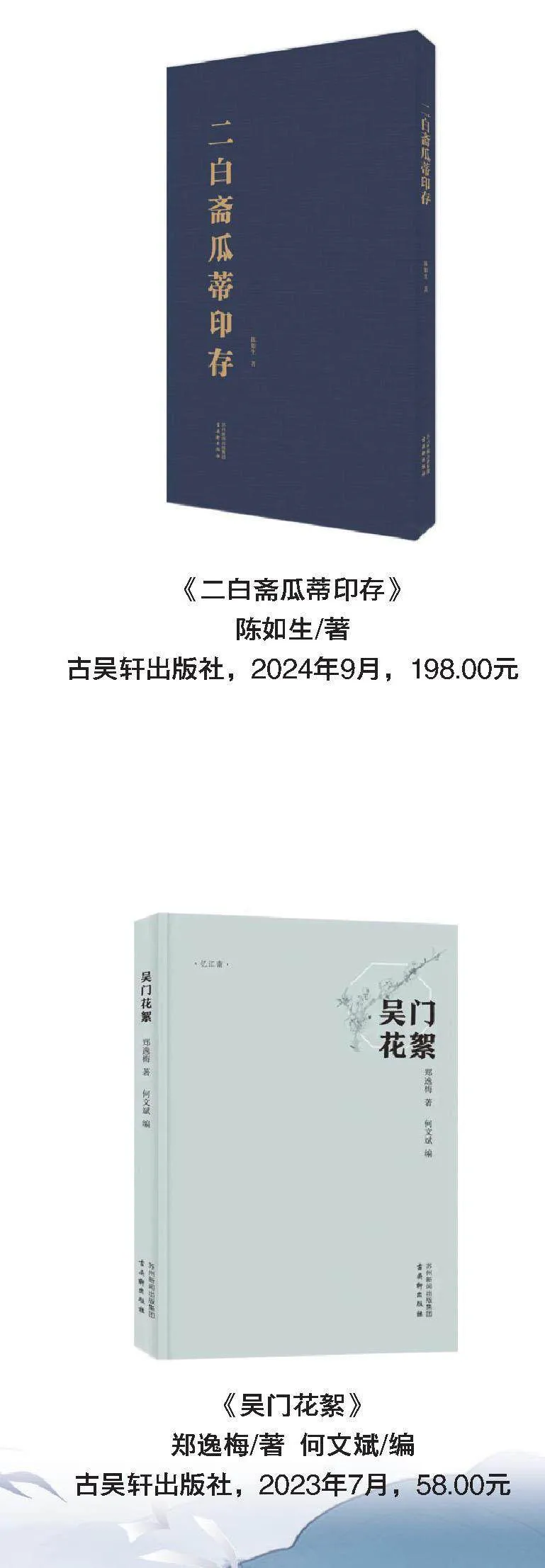
從古至今,人們始終在尋找生活中的美,飲食、茶道、書畫、篆刻、清供,這些在傳統(tǒng)文化中滋養(yǎng)出的中式美學,也已融入生活狀態(tài)中。書之妙道,神采為上;篆刻之妙,亦須傳神。而清供則稱得上古人雅致生活的一種縮影。清供,供的是自己的那份清心,而人的欣賞,終將會慢慢變成“雅物”。(編輯:陶瑾)
此書是陳如生先生的篆刻藝術精品集。以質樸無華的瓜蒂為藝術載體,收錄了陳如生近百枚瓜蒂印佳作,并附原作相片及創(chuàng)作隨筆。書中既涵蓋詩詞、書畫、琴曲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瑰寶,也涉及名川勝景、佛學、動植物等內容,更有意融入蘇州名勝、蘇州評彈等吳地文化元素。瓜蒂印隨形賦勢,令人嘆為觀止。通過書法篆刻中華文化精粹,不僅能夠擴大江南文化的影響力,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為篆刻藝術注入新動能,從而推動篆刻印譜史的發(fā)展。故此,《二白齋瓜蒂印存》于當今的印譜出版而言,頗有開創(chuàng)之意義。二白齋主陳如生,師從吳昌碩二代傳人、中國美院諸涵教授,其書、畫、印既傳薪吳缶翁一脈,又自出機杼。
【自序】
清代金石學興起,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發(fā)展。印人在金、銀、銅、鐵、玉石、瑪瑙等傳統(tǒng)印材外,取獸骨、象牙、果核、瓜蒂治印,開拓了印材的使用范圍。近世以來,嘉興許明農、蘇州張寒月先生用本土南瓜蒂刻印,各具風采,令人矚目。瓜蒂質本素心,樸實無華,用作印材,雖不能與田黃、芙蓉、封門、雞血媲美,朽木可雕,也能體現(xiàn)出篆刻的基本要素和質樸的鄉(xiāng)土情懷。就地取材,融入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了瓜蒂的生命力和價值,使其成為喜聞樂見、雅俗共賞的藝術品。今選出十多年來部分習作,積微成著,匯集成冊,并附上創(chuàng)作隨想,拋磚引玉,以饗同好。旨在弘揚傳承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藝術,守正弘道,更廣泛地進行瓜蒂印創(chuàng)作的學術交流。同時拾遺補闕,填補篆刻史上瓜蒂印譜刊發(fā)的空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本書收錄了逸梅先生諸多關于江南的文章,文辭優(yōu)美,內蘊深情。書中文章錄自民國老報紙、舊時出版物等,薈萃江南記憶,均為難得一見的作品。大體可分為三類,紀人、紀物、紀游,既是文化散文,又可作為歷史掌故閱讀。蘇州地區(qū)的自然名勝、園林景觀、物產特色、風土民俗,舊時文化名人的交游情況以及他們的精神風貌,二十世紀上半葉江南的時代特征,盡在其中。經蘇州文化學者何文斌先生編選,更顯江南特色。
【精彩選段】
我把這篇妙文發(fā)表的下一天,有事經過卓呆所居的普恩濟世路(即現(xiàn)在的進賢路),順便到他家里灣一灣,我就問他這豆餅粉當真可口么?因為卓呆游戲三昧,往往說著開開玩笑的。不料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豆餅粉的確很好吃,這里多著呢,你可以帶一些去嘗嘗。”說著即由他的夫人包了一包給我。我?guī)Щ丶遥攬鲈囼灒诙癸灧壑屑尤肓诵┌滋牵X得香甘可口,風味不亞于豆酥糖。我吃了再吃,越吃越有味,可是吃完了,不便再向卓呆索取,以為橫豎當局要配給出來,吃的機會多著哩……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菜譜之一,或許有不少人都曾聽說過此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書里收錄的104道菜中,其中九成都是素食。林洪所寫的《山家清供》是一本富有文學韻味和醫(yī)學養(yǎng)生知識的飲食筆記。全書分上下兩卷,共104則食譜。所謂“山家清供”,是指山野人家待客時所用的清淡田蔬。作者以此作為書名,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清淡菜蔬由衷的推崇與喜愛之情,也體現(xiàn)了其追求“清”“雅”的飲食美學思想。這本書是讀者了解傳統(tǒng)飲食文化與生活美學的佳作。
【點評】
宋朝飲食繁榮,文人學者相關著述也極為龐雜,大致可分為食經、茶學和酒學三大類。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從中脫穎而出,不僅是菜譜,還有掌故,既有樸素的飲食美學,又有清雅脫俗的詩詞,還有各種食療養(yǎng)生,看似小品式的散文卻有著別樣的大性情、大胸懷、大格局,可謂“舌尖上的大宋”,兩卷104道菜有淵源,有佳句,美食家必讀!
喵書上新
生活中,貓咪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無數(shù)人的寵物,它們的一舉一動萌化了我們的心。然而,你是否曾好奇過,貓咪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著怎樣的故事和文化內涵呢?《貓在故紙堆》以“貓”為線索,介紹了多種與貓有關的古代文獻,如《貓乘》《貓苑》《銜蟬小錄》等,也涉及貓名、養(yǎng)貓、聘貓等貓的各種知識。全書分為《古籍里的各種“貓”》《我佛不養(yǎng)貓》《有關貓的“血淚史”》《以貓為名》《貍貓和太子的三段往事》《貓書解題》《民間歌謠中的貓》《紅樓夢中貓》等章節(jié),通過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爬梳,考證古籍中與“貓”相關的物種,闡述貓與佛教文化的聯(lián)系,講述貓在歷史發(fā)展中的境遇,解析貓與古代人名、地名、民俗、歌謠的關系,立意高遠,充滿趣味,又能引起讀者對于相關問題的思考。
【自序】
一個默認的現(xiàn)實是,當大家翻開一本貓書時,大概率會抱著一種“我要愛”的心態(tài)。拙著《貓奴圖傳》出版之后,我看到的絕大多數(shù)推薦語,針對的都是愛貓者。在國內某頂級媒體推送了相關書訊之后,我對《貓奴圖傳》的序作者林趕秋先生說:“還是林公懂我。”因為我看到只有林先生在推薦拙著時,會直言不諱地告訴讀者:“劉朝飛不喜歡貓。”大眾似乎更關心情感,而非事實。《貓在故紙堆》是一本“放飛自我”的書,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的,也就是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并沒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安排。《貓在故紙堆》寫完之后,我仍然剩了很多材料沒有用到,中國貓兒文化中還有很多有趣的話題可以談,比如中國貓兒美術史,就值得寫一本書。這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