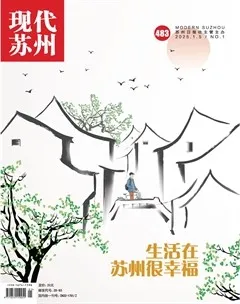走進《姑蘇橋》幕后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蘇州是水的故鄉,也是橋的王國,蘇州古橋是江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姑蘇橋》收錄了胡忠勤拍攝的蘇州地區的349座古橋,并對每座橋的基本特征、歷史變遷、文化典故等進行了文字闡述與總結,充分展示了姑蘇橋的悠久歷史和獨特風韻。
對江南橋梁文化的一次回眸
作為一名老蘇州,胡忠勤自2017年開始探訪、拍攝蘇州現存古橋,希望用文字和圖片永恒記錄下那些逐漸被人遺忘的古橋及其背后的歷史人文,展示古橋風韻,呼吁全社會共同保護珍貴的古橋資源,傳承古橋文化。他對蘇州現存古橋的探訪、拍攝,打卡、建檔,是對吳地古橋現狀的一次精心梳理,也是對江南橋梁文化的一次全面回眸,更是為蘇州古橋保護性研究盡了一份力。
“我是一個在蘇州出生、長大的蘇州人。從小住在念珠街(現吉慶街),出門不遠就要走過石巖橋(孫老橋)、歌薰橋,或者來遠橋、萬年橋,真所謂‘無橋不成行’。蘇州的古橋與蘇州文化、江南文化緊密結合,是蘇州名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保存至今的古橋越來越少。”胡忠勤說,他既為故鄉的小橋流水感到驕傲,又為日漸消失的古橋感到痛心。而在感嘆唏噓之余,他想讓這些飽經歷史滄桑,已成為文化、文物的古橋盡可能地為人所知、所愛、所惜,并由此得到一個妥善的歸宿,最大可能地保護和傳承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遺產。
正是懷著這樣的情結,2017年初,胡忠勤踏上了探訪、拍攝蘇州現存古橋之旅。6年多來,除了受疫情的影響,他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在找橋、拍橋、寫橋。“我一般是白天在外尋找探訪、拍攝古橋,干的是體力活,當作是體育鍛煉;晚上查閱資料,撰寫文稿,干的是腦力活,當作是防止老年癡呆。”胡忠勤說,每當順利探訪、拍攝好一座古橋時,內心便會充滿了喜悅,特別是有新發現的古橋時,成就感立刻爆棚。而當看到一些古橋被拆除,特別是面對古橋的殘骸時,他往往會傷心不已。
拍攝古橋過程中曾幾次遇險
不為人知的是,胡忠勤探訪、拍攝古橋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曾經幾次遇險。
“記得有一年的夏天,我在平江路探訪、拍攝至中午時分,也許是在37攝氏度以上的高溫下太久了,我中暑了,差點昏厥過去,幸好在陰涼處躺了一段時間,緩過了神來。”胡忠勤說,還有一次,他去金庭鎮探訪、拍攝永泰橋時,得知橋孔內有一方石碑,上有銘刻,因急于拍攝,見永泰橋下河水不深,有的地方河床還裸露,就一手搭著河駁岸上的石欄桿,想順著河駁岸慢慢下河。“誰知那欄桿沒有‘長牢’,我重重地摔了下去,有整整2米多深。萬幸的是,隨我身體一起摔下去的石欄桿沒有砸在我身上,否則后果不堪設想。”胡忠勤忍著手臂多處嚴重皮外挫傷的疼痛和渾身上下泥水的惡臭,堅持把這明景泰二年(1451年)的石碑拍攝了下來,變成了珍貴的資料。而因為專注觀察、拍攝,胡忠勤一不小心腳下踩空、仰面摔倒之事時有發生,但在他看來,這些雖然辛苦,卻也充實。
因不愿敷衍了事、拼湊成章,每座橋胡忠勤均不止一次到現場探訪、拍攝,并測量尺寸和經緯度定位,特別是對其中留有歷史印痕、記憶的橋名、橋聯、銘刻等進行重點攝錄、仔細辨識,努力在文稿中杜絕硬傷,減少差錯,并且積極糾誤。“為了仔細辨識,有多少個夜晚,我在電腦前看白天攝錄的橋名、橋聯、銘刻等照片,看得眼睛都‘蕩(突)’了出來,第二天早上還會發現寫字臺下面的地板上都是脫發。此外,我還多次請教朱九如老師和王曉芳、陳慧中等老師及有關同學。”胡忠勤說,如此認真,也小有成果:比如婁門下塘的傅文涇橋,有關資料上只表述“清康熙年間重建”。而他在探訪、拍攝該橋時發現,其橋梁石北側有雕刻橋名“傅墓涇橋”和銘刻“嘉慶壬申年八月吉日立”“里人重建”等字樣,故他在文稿中表述為“始建年代不詳,清嘉慶十七年(1812)里人重建”。類似種種發現,多達幾十處。
“全實美”成就“最美的書”
在胡忠勤看來,《姑蘇橋》有著三個特點:“全”“實”“美”。
“全”,是指收集的古橋數量比較齊全。《姑蘇橋》共錄入了蘇州城區目前現存的349座古橋。這些橋, 要么是始建年代不晚于清末或民國初期,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橋;要么是重建、重修后仍基本保持原貌或原構件的古橋;要么是舊貌雖改,但在歷史上有一定名氣的古橋;要么是因拆遷而移建別處并保存尚好的古橋。
“實”,是指內容比較實在。《姑蘇橋》共分四個章節:一是園林名勝;二是大運河;三是古城水巷;四是鄉村田野。每橋自成一篇,圖文并茂,數幅圖片全方位展示古橋現狀和風貌。文字介紹包括古橋所在位置,建、修年代,基本數據,形制特點,相關典故及人文故事,以及目前狀況和探訪、拍攝有感等等。每橋還附詩一首,均為傳統文化愛好者張建林所作,詩情與橋韻共鳴。
“美”,是指內容和形式結合完美。從拍攝角度來說,胡忠勤注重了橋韻全貌的展示和局部細節的特寫相結合;從裝幀角度來講,古吳軒出版社的書籍裝幀設計師李璇精心設計,從外形到內頁均采用了大量蘇州元素,并有著厚重的歷史感。
“最初看到這本書的內容時,我就想要把它做成‘一塊橋石’,以呼應蘇州古橋給人的古樸厚重的感覺。但實物要做到厚而不重,既有石頭的外形,又要保證讀者翻閱起來輕松舒適、便于拿取。因此在紙張的選擇上,經過反復討論和比對,我們最終采用了表面粗糙的輕型藝術紙,既保證觸感上有磨砂質感,與整本書‘塊橋石’的調性相符,又不沉重。”李璇說,通過和胡忠勤的實地探訪,他們決定書籍整體外觀采用虎丘區滸墅關鎮眾緣橋上的石紋。
眾緣橋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00多年歷史,雖然橋的規模不大,但工藝精巧,且保存良好。該橋的橋基由花崗石及青石壘砌而成,橋面則由一整塊武康石構成,這在蘇州地區的橋梁中十分罕見。而作為蘇州古橋建造時使用的代表性石材,武康石表面有非常多的孔隙,且顏色呈非常漂亮的紫褐色。由于設計書籍時正值盛夏,橋體比較干燥,為了能更好地呈現橋石的顏色與質感,李璇在橋上灑水、噴水,等待水滲進石頭里才開始拍攝。通過在4米長的橋面上反復對比、采樣,李璇最終挑選出書籍現在呈現的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