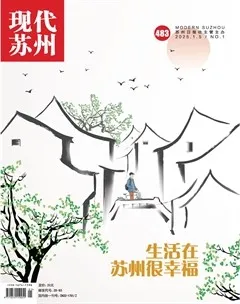《音學五書》:開啟清代韻學山門,探賾古音悠遠奧秘





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是明末清初的一部重要音韻著作,大約成書于公元1667年,全書分為五個部分: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作者對古音學的基本看法,詳細討論了古音和古音學上的重大問題。顧炎武在《音學五書》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觀點,包括“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古詩無葉音”“古人四聲一貫”等,這些觀點對于理解古代漢語的音韻和語言演變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期,我們跟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文一起走進顧炎武的“音學”世界。
舒君amp;《現代蘇州》:中國是什么時候開始研究語音現象的呢?
孫玉文: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語音現象的國度之一。在世界語言學史上,大約只有古印度比我國研究語音現象要早一點,古希臘和古羅馬也較早研究語音現象。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采用的文字系統是表音文字,語音問題容易引起他們的興趣。公元前4世紀,古印度的波尼尼撰成《梵語語法》,其中有關于語音的內容。我國在先秦時期已經對漢語語音有零星的描寫,漢代人在訓詁實踐中明確地認識到古今語音有變化。大約東西漢之交時產生了用一個漢字給另一個漢字注音的直音法,東漢中期產生了用兩個漢字給一個漢字注音的反切法。
作為一門學問,中國傳統音韻學的出現應以三國時期魏人李登《聲類》(已佚)的出現為標志,迄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的歷史,成果累累,建立了“古音學”“今音學”“等韻學”三個分支學科,在世界語言學史上取得了巨大成果。
舒君amp;《現代蘇州》:請您談談中國傳統音韻學大致發展過程。
孫玉文 :最早出現的是今音學。這門學問在李登《聲類》基礎上逐步蔚為大觀。《聲類》應是以曹魏時期的音系為基礎音系產生的一部韻書,隨后有西晉呂靜的《韻集》(已佚,是仿照《聲類》作的韻書,也應是以時音為基礎撰寫的韻書。南北朝出現類似的韻書更多,可惜這些書也都亡佚了)到隋代,陸法言編寫《切韻》,吸收了此前音韻書的編寫經驗和教訓,也吸收了此前韻書的分韻,審音精細,分韻相當細密,以時音為重,力圖溝通古今都有的讀音分別和南北方音。唐五代之后,有不少《切韻》的增訂本,被稱為“《切韻》系韻書”,有的增訂本比《切韻》分韻還多。《切韻》的分韻、聲調、四聲相承以及每個字的反切讀音都是已知的,但它的聲母、介音以及聲韻調配合情況卻沒有告訴我們,需考證。清代陳澧寫《切韻考》,清人至今人在陳澧的基礎上不斷研究,將《切韻》音系基本上研究清楚了。
唐代始,人們還編寫了反映唐代北方讀音的韻書,但亡佚了。今天留下來最早反映當時方音的韻書是《中原音韻》,這是反映元代中原讀音的韻書,分為十九個韻部,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哪些字的字音相同也是已知條件。明清時期,反映各地方音的韻書多了起來。例如明朝有《洪武正韻》《韻略易通》《韻略匯通》等,清朝有《五方元音》等一大批韻書,都對理解明清時的音系有幫助。
在唐代編寫韻圖之前,唐人對當時漢語的聲母有了系統的認識,三十六字母應是唐五代的產物。
大約中唐以后,出現了等韻學,主要是編寫連續性的《切韻》系韻書聲韻調配合表。早期的韻圖和等韻學,今所見主要有《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等,都是以方便拼切《切韻》反切為目的的,后來逐步擴大到反映《切韻》系韻書之外的音系,甚至時音音系,著述甚多,明清時代為甚。等韻學不但反映了歷代音系,而且也反映了歷代學者對于字音及音素的認識成果。
明代學者陳第等人認識到上古音是一個共時的系統,可謂清代古音學的開路先鋒。明末清初,顧炎武撰寫《音學五書》,顧氏是古音學的開山祖師,他研究的是上古韻部,主要依托于上古韻文。沿著顧炎武古韻分部的路子走的,主要有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等人,古韻分部幾成定局,后來只有王力先生的脂微分部。
清代有成就的古音學家都認為上古有聲調,但具體看法很有分歧。段玉裁提出“古無去聲”說,有得有失,其得在于看出中古的一部分去聲字上古要歸到入聲。現在可知,上古至少有平聲、上聲、去聲、長入、短入五個聲調。
研究上古聲母系統,沒有研究韻部系統這么好的條件,因此清代古聲母研究的成果有限。其中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說法成為不刊之論,清代還有的學者對上古聲母有一些具體設想,可惜沒有來得及加以證實,只有結論性意見。章炳麟主張“娘日歸泥”,黃侃主張“照二歸精”“照三歸端”,曾運乾主張“喻三歸匣”“喻四歸定”,錢玄同主張“邪母歸定”等,雖然不一定是定論,但都很有價值。章炳麟、黃侃還提出了自己的上古聲母系統的假定。
舒君amp;《現代蘇州》:《音學五書》是顧炎武先生學術作品中的代表作,歷來對它的評價都很高。請您談談它在傳統音韻學中的價值。
孫玉文:《音學五書》的問世,意味著上古音研究成為漢語音韻學中的“古音學”,也意味著古音學跟今音學、等韻學并立為傳統音韻學三大分支的格局的形成,萬事開頭難,因此《音學五書》在傳統音韻學中具有極高的地位。清代“小學”發達,其精髓在于因聲求義,因聲求義的精髓在于建立了科學的古音學,顧炎武《音學五書》具有首創之功。可以說,沒有《音學五書》,就不可能有清代小學的巔峰境界。
舒君amp;《現代蘇州》:顧炎武《音學五書》具有開創性和可行性,通過上古韻文來進行古韻的系統分部,是顧炎武的卓識所在。您可否舉例與讀者分享?
孫玉文:就拿大家普遍熟悉的《詩經》來說。客觀上說,韻文材料是研究上古音最好的材料,《詩經》為其中之最。這是因為:一、《詩經》有三百零五篇詩歌,一千七百多個韻段,基本上能反映當時的韻部總體情況。二、《詩經》時空明確,它創作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以前約五六百年的時間,語音的變化不會太大;產生的地域處于黃河到長江北岸的湖北段,相當于今陜西、甘肅、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湖北等地,地域相距不太遠,因此基本上能從《詩經》中求出一個共時的韻部系統。其他任何一種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大都沒有《詩經》等韻文材料的時空一致性高。三、《詩經》是“天籟”,它的押韻只能是依據當時的口語,不可能模仿前代的詩歌;當時也沒有韻書一類的書,因此它反映的必然是當時的韻部系統。四、《詩經》經歷了經典化階段,據說原來《詩經》的篇目較多,孔子刪《詩》,當然會統一各地詩篇的文字,而且歷代對它的字詞句釋讀基本上形成了定論。經過顧炎武等人的研究,至清末,上古有多少韻部,基本上有了定論。
舒君amp;《現代蘇州》:當今出土了一些文獻材料,其中不乏韻文,包括《詩經》的一些片段。有人說,其中的用字跟今傳《詩經》有一些差異,《詩經》應經過了后人的改動,但出土材料沒有推翻古音分部的成果,出土材料反而印證古韻分部是正確的。請教孫教授,這是什么原因呢?
孫玉文:這個問題的回答牽涉到對顧炎武開創的清代古音學的認識,因此很值得研究。我的初步想法是,這要分為分部和歸部兩個方面看。
從分部看:一、上古韻部是上古語言中的韻部,不是上古文字的韻部。碰到入韻字,只要該字記錄的詞沒有換成別的詞,只是換成別的字,那么無論后人如何改動其用字,所反映的語音事實都是一樣的。人們通過《詩經》研究上古韻部,得出的韻部不可能不同。二、《詩經》在春秋時期應該沒有出現異文,那時候諸侯的使臣出使,常常賦《詩》以言志,這應建立在各諸侯國有統一文本的基礎上。有人說,《詩經》出現異文是從漢代開始的,恐怕不確。《詩經》在戰國時期應已出現異文,漢代更多,這只要將漢代出土《詩經》跟他書所引《詩經》互相比較,比如跟《說文》引《詩》進行比較即可知道。所以東漢《熹平石經》、唐朝《開成石經》都有《詩經》,這都對遏制后人改竄《詩經》起到積極作用。《詩經》異文反映在文字上,前人都知道《詩經》是押韻的,碰到韻腳字,他們往往不會輕易改成一個押不上韻的字。所以韻腳字的用字大多相同,即使有異文,也往往表現在異體字之別、本字和假借字之別、不同的假借字之別。同樣地,現已出土多部《周易》,比勘一下可知,《周易》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不少異文。因此,出土戰國至漢代《詩經》片段的文獻不少,只能從另一個角度印證顧炎武以來的古音分部是正確的。
從具體字的歸部看:絕大多數異文能進一步印證傳統的歸部是正確的;也有極少數的異文能糾正以前因為材料不足而誤歸韻部的結論。因此,出土材料對于研究上古音歸部非常有好處,不可忽視。
這說明《詩經》雖經后人改動,但是韻腳字并沒有經過傷筋動骨的改動。進一步說,認為出土材料能否定傳世文獻得出的古音研究成果的說法,是缺乏事實和理論證據的。
顧炎武研究上古韻部,不但將《詩經》《周易》等上古韻文作為一個共時的系統從事客觀歸納,而且還跟《廣韻》進行對比,這都是很正確的。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已經意識到上古音是一個共時的系統,開始大規模地系聯上古韻文,但他沒有從事古韻分部,只是從一個字處在不同的韻段中確認具體字在上古具有跟中古不同的客觀讀音;至顧炎武,則比陳第更進一步,據此來劃分上古韻部。上古音跟中古音必然具有嚴整而系統的對應關系,但是陳第沒有想到這一層,顧炎武將韻腳字跟《廣韻》韻屬一一比對,看出《廣韻》有些韻在上古合為一部,有些韻一半歸上古甲部,一半歸乙部,從而打散《廣韻》韻字,歸屬上古不同的韻部。這無疑是以韻腳字系聯為基礎帶來的做法。后人管這種做法叫“離析《唐韻》”,這里的《唐韻》實即《廣韻》。顧氏分出古音十部,其中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四部成為定論,其他各部的分部還比較粗疏。后人進行古韻分部,都繼承了顧氏韻腳字系聯和離析《唐韻》的做法,越分越科學,越分越系統,這都是因為顧炎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