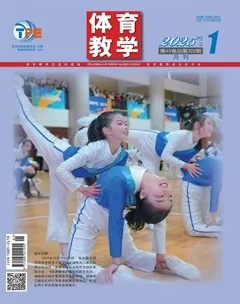追問運動技術(shù)
摘" 要:明確運動技術(shù)的本義是討論“運動技術(shù)課課會”的前提。以往相關(guān)研究偏重“科學”卻脫離真實運動情境。將“運動技術(shù)”置于真實的運動情景中分析可知,“運動”并非機械運動,而是人的身體運動;“技術(shù)”并非“科學技術(shù)”而是身體技術(shù);運動技術(shù)與作為主體的身體同在,存在于體驗時空系,而非物理時空系。運動技術(shù)形成于運動主體在解決運動課題時對自身運動感覺的重構(gòu),其實質(zhì)是運動認知,具有主體性、具身性、意會性、整體性特征。
關(guān)鍵詞:人的運動;身體技術(shù);體驗時空系;運動認知
中圖分類號:G623"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5-2410(2025)01-0012-04
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在解釋“課程性質(zhì)”時這樣表述“……體育與健康課程以身體練習為主要手段……”。體育課上的“身體練習”絕非盲目練習,必然強調(diào)合理、科學、規(guī)范,這樣的身體練習必然強調(diào)技術(shù)性。另外,體育課有“學科類(理論)”與“術(shù)科類”的分類方式,“術(shù)科類”指的是以運動技術(shù)為載體的體育課。以田徑、球類、體操為載體的體育課自不必說,體能練習課同樣強調(diào)合理的動作方法(哪里該發(fā)力,哪里該放松,姿態(tài)該什么樣),這樣的動作方法亦屬于運動技術(shù)。可見無論從“術(shù)科類”的說法,還是從體育課應有面貌來看,沒有運動技術(shù)就不會有體育課。
眾所周知,與數(shù)學、語文、物理等“知識類”課程強調(diào)“懂(理解)”相比,體育課更加強調(diào)“會”。也就是體育課上學的技術(shù)、動作,重點在于學生通過肢體行為按一定標準展示出來,而非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然而,多方信息顯示12年中小學體育課運動技術(shù)教學效果(所謂的“會”)并不盡如人意。為了扭轉(zhuǎn)這種局面,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舉措。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的《關(guān)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zhì)量的意見》明確強調(diào)“讓學生掌握1-2項運動技能”,《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2022年版)》進而將之具體化為課程目標。當下成為熱點話題的“教會、勤練、常賽”、大單元教學亦試圖扭轉(zhuǎn)這種局面。
上述做法導向明確,但均屬于“怎么做”層面的操作性舉措,在這之前“是什么”層面的性質(zhì)(意義)界定,如果得不到準確解答,操作性舉措的實際效果很可能會大打折扣,甚至南轅北轍。因而,在“教會、勤練、常賽”理念下討論“運動技術(shù)課課會”問題時,首先有必要清楚運動技術(shù)的本義。
一、以前運動技術(shù)研究的缺憾
檢索可知,運動技術(shù)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謂豐碩,研究對象涉及運動技術(shù)內(nèi)涵(概念、定義)、形成(掌握)的規(guī)律、診斷、發(fā)展的歷史及趨勢等,研究視角涉及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哲學等。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提及運動技術(shù)的內(nèi)涵,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將之界定為運動的方法、手段,還有將之界定為運動的知識、能力。歷來運動技術(shù)研究的共同之處在于,多從第三者(旁觀者)的立場,將運動技術(shù)看作客觀研究對象,卻遮蔽了運動技術(shù)的主體性特征;多從“科學”(力學、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等)的視角解釋運動技術(shù),解釋的只不過是表象的運動技術(shù)[1]。
回到身體運動情境中思考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的運動技術(shù)是“前科學”的,表象之下蘊含著豐富而生動的內(nèi)涵。想一想走路、跑步、打球等日常生活及競技運動中的運動技術(shù)如何發(fā)生,很容易明白這個道理。顯然,現(xiàn)實的運動技術(shù)才是真實的運動技術(shù),并不能完全用“科學”衡量。再稍加細致審視會發(fā)現(xiàn),用“方法”“手段”“知識”“能力”進行界定,也未捕捉到運動技術(shù)其本義,而是將其本義關(guān)進了“黑箱”里。進一步追問這些界定方式對運動訓練、體育教學有何實際意義時,總會有未切中要害之感。
由上可知,想要洞悉運動技術(shù)的本義,首先要懸置一切成見,包括“科學”的、“權(quán)威”的,不打折扣地置身于現(xiàn)實的運動情景中,思索主體運動行為的生成、發(fā)展。如何展開思索?運動技術(shù)是由“運動”與“技術(shù)”組合而成的復合詞,洞悉運動技術(shù)的本義,有必要將“運動”與“技術(shù)”置于現(xiàn)實的運動情境中逐一分析。
二、作為身體運動的“運動”
“運動技術(shù)”中的“運動”指的是人的身體運動,而非物體運動或機械運動。以籃球投籃為例,原理上機器人投籃與真人投籃有著質(zhì)的差異。視頻中看到的機器人投籃,動作非常標準,命中率極高,非真人所能及,但這都是人為設計、調(diào)試的結(jié)果。原理上,機器人投籃主要包括傳感器感知(實際上是測量)、控制器程序計算和電動機械臂投籃三個步驟。傳感器(鏡頭及激光傳感器)用于測量籃球到籃筐的距離、方位、角度。控制器依據(jù)傳感器收集到的信息(數(shù)據(jù))計算出最佳的出手角度和力度。電動機械臂依據(jù)傳感器的指令完成出手動作。概括而言,機器人投籃無論多精確,原理上也都是機械運動,是在計算機語言支配下的數(shù)字化(計算)的運動結(jié)果,這樣的運動實際上是數(shù)學、物理時空系中的物體位移[2],其運動機制可用物理學等科學知識解釋清楚。
真人完成投籃,用運動生理學的運動反饋機制、本體感覺機制等可做出詳細解釋,也可用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出最佳的出手角度、出手初速度等。這些科學成果在某些方面對運動訓練、體育教學確實發(fā)揮了促進作用,但這些屬于事后分析,且分析的只是在學科知識范圍內(nèi)可言說的部分。真人投籃動作可以說整個身體參與其中,即需要物質(zhì)性存在的骨骼、神經(jīng)、肌肉協(xié)調(diào)聯(lián)動,又受身體狀態(tài)(疲勞、傷病)及精神狀態(tài)(興奮、緊張、情緒)的左右。即便能夠測量某根骨骼、某塊肌肉發(fā)揮多大作用,但包括精神狀態(tài)在內(nèi)所有構(gòu)成要素如何聯(lián)動,全部言說出來絕無可能。
近代以來,尤其近100多年運動人體科學研究極大推動了運動訓練水平,促使眾多運動項目成績屢被刷新,但也應正視運動人體科學研究的邊界。數(shù)字化、可重復性等是“科學”研究的特征。作為“前科學”的現(xiàn)實的身體運動實際上并不能數(shù)字化,且不可重復。試想自己投籃時,是否能說出準確籃球到籃筐的準確距離、出手角度、力度?實際上很難。那自己到底是否知道籃球到籃筐的距離及方位?肯定知道,不然那些投籃高手怎么能高命中率投中。只不過真人知道的是體驗時空系意義上的距離、方位。體驗時空系由視覺、觸覺、運動感覺等協(xié)同作用而成,以運動感覺為主。人的體驗時空系意義上的身體運動是作為主體的、第一人稱的“我的身體運動”,由感覺、感動、感情交織而成的生命氣息充斥其中,主體性、具身性(身體性)、默會性(意會性)是其特征。
三、作為身體技術(shù)的“技術(shù)”
運動技術(shù)的上位概念是技術(shù),要明確運動技術(shù)的含義,有必要將之置于“技術(shù)”中。由社會發(fā)展史可知,原始社會的人類發(fā)現(xiàn)火的用途,掌握鉆木取火技術(shù),發(fā)現(xiàn)用石頭砍、砸、削的用途,并掌握制造石器工具的技術(shù),后來又制造出青銅工具、鐵制工具……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本身”,人的勞動行為與工具相伴而生,工具是人類技術(shù)的表征,人的勞動是技術(shù)性勞動,人的存在實際上是技術(shù)性存在。即人與技術(shù)同在,不分先后,技術(shù)實為“人的存在方式”[3]。這一點從人類與其他動物對比中很容易明白。小羊出生后5分鐘左右就可以獨立行走,很多鳥類從破殼到獨立生存只需要25天左右……且眾多動物先天具有保持體溫、保護自身安全的皮毛,卓越的奔跑、跳躍、攀爬能力。人類沒有皮毛保護,奔跑、跳躍、攀爬能力也非常一般,在成人保護下蹣跚學步大多也1周歲左右,獨立生活則要十幾歲以后,但人類掌握了技術(shù)并依靠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人既是地球上最柔弱的動物,也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動物,柔弱在于其先天能力不足,強大在于后天可以學會技術(shù)。
上述事實告訴我們,“人的最基本的工具、最基本的技術(shù)是我們的身體技術(shù)”[3]。從出現(xiàn)時間及邏輯來看,身體技術(shù)顯然比“科學技術(shù)”悠久得多,因為,“科學”相對人類歷史而言,極其短暫,而身體技術(shù)則伴隨人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是人類與其他動物區(qū)分的重要標識,“科學技術(shù)”則意味著從科學的角度看到的技術(shù)。概言之,身體技術(shù)是一個存在論意義上的概念,而“科學技術(shù)”則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
身體技術(shù)含義寬廣,日常生活中各種各樣的身體行為(如行走、餐具使用、家庭烹飪、書寫、交通工具駕駛)幾乎都可歸入身體技術(shù),職場勞作中的身體行為(操作器具、使用用具)也屬于身體技術(shù)。運動技術(shù)更是典型的身體技術(shù),只是它不像日常生活與職場勞作中的身體技術(shù)那樣更具實用性,而是更具消遣性,更像前兩類身體技術(shù)的心理補償[3]。運動技術(shù)同樣是人的存在方式,獵豹跑得快,袋鼠跳得遠,猴子攀爬靈動帶有強烈的先天特征,而人類則可通過習得運動技術(shù)將先天運動能力更大限度地發(fā)揮出來,甚至可借助外界設備超越先天運動能力(如跑鞋、踏板、撐桿等)。
無論外界設備有多先進,技術(shù)分析有多科學,最終也要落實到自身的身體運動行為中。外界設備功用的有效發(fā)揮,使用者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將之化作自己身體的延長,例如掌握使用筷子,協(xié)調(diào)駕馭撐桿,適應新球拍。運動技術(shù)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借助的是相關(guān)學科知識(如力學),屬于“概念性知識”范疇,將之運用于運動訓練、體育教學需要一個轉(zhuǎn)化過程。沒有相關(guān)運動訓練、比賽經(jīng)歷的生物力學專家無法直接指導運動訓練,實施這種轉(zhuǎn)化任務的是運動指導者(教練、體育教師)及運動者本身。運動指導者實施轉(zhuǎn)化任務依賴的是其自身的運動經(jīng)驗。這些現(xiàn)象充分佐證了“運動技術(shù)與身體同在”,即具身性的特征。
四、運動技術(shù)教學的機理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知,無論“運動”,還是“技術(shù)”,都應從人的身體運動的角度理解,而非機械運動。運動技術(shù)是典型的身體技術(shù),其含義或可解釋為運動主體在解決具體運動課題時更加有效駕馭自己身體的能力。這樣解釋意味著運動技術(shù)是作為主體的“我”的運動技術(shù),別人無法代替,“運動技術(shù)與身體同在”(具身性)也就是運動技術(shù)屬于自己。“有效駕馭自己的身體運動”指的是自己現(xiàn)有絕對力量、柔韌等再好,未必運動技術(shù)好。例如鉛球運動員臥推能力、深蹲能力可看作絕對力量的指標,如何將自己現(xiàn)有絕對力量有效發(fā)揮出來,這是運動技術(shù)訓練(教學)的核心命題。
“運動技術(shù)與身體同在”的道理,還告訴我們運動技術(shù)自身無法用語言描述清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20多年前巴西對陣法國隊的一場比賽中,卡洛斯主罰任意球,足球在中途改變方向,繞過人墻直奔球門。這一被載入史冊的經(jīng)典進球俗稱“香蕉球”,可用流體力學中“馬格努斯效應”解釋足球飛行軌跡。那樣的飛行軌跡由腳擊球的位置及擊球力度決定。對之用數(shù)學、物理知識可精確計算、清晰分析,但這樣的解釋并非任意球技術(shù)本身。卡洛斯本人并不能清楚地說明白那一腳如何踢出、力度多少。說不明白,并非他不知道怎么踢。卡洛斯目測足球到球門的距離,對彼方球員站位做出判斷,助跑、出腳均依賴于多年訓練、比賽中形成體驗時空系意義上的運動經(jīng)驗,他是在體驗時空系意義上“測算”的同時一氣呵成完成一系列動作,這與物理時空系意義上的測算、機械運動有質(zhì)的差異。
由上面卡洛斯踢任意球的事例可知,體驗時空系存在于運動者的身體中。從知識、認知的角度理解的話,體驗時空系就是體知(身體認知、身體知、具身認知)。運動者在學校體育活動、競技體育(sport)活動中構(gòu)建的體驗時空系則可將之稱為運動認知(認識)。卡洛斯精妙的任意球的技術(shù)(技藝)是典型的運動認知范例。這樣運動認知形成于日復一日的運動情境中,是運動者解決運動課題(如射門、過人、傳球)過程中重構(gòu)自己體驗時空系的結(jié)晶。重構(gòu)自己體驗時空系也就是重構(gòu)由自身骨骼、肌肉、神經(jīng)等構(gòu)成的運動感覺。看到某人跑得很舒服、很靈動,我們常會說一句“他運動感覺真好”,實際上就是對其運動認知能力的簡明概括。
運動技術(shù)自身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并非否定運動訓練、體育教學中的言語交流。在運動訓練、體育教學過程中言語發(fā)揮的作用與輔助手段、手法發(fā)揮的作用類似,在于能否借此提示有效的“焦點意識”信息[1]。在眾多運動項目的教學中經(jīng)常使用的那些口訣發(fā)揮的正是這種作用。例如有人將前滾翻的動作要領(lǐng)概括為“弓、蹬、團、跟”或者“低頭提臀腳蹬地,頸、背、腰、臀依次滾,胸、膝緊靠,肩向前”。20多年前北京史家胡同小學的王仲生老師曾展示一節(jié)“低頭看天學前滾翻”的課,更是堪稱經(jīng)典[4]。王仲生老師考慮到授課班級學生現(xiàn)有認知狀況,引導學生“低頭看天”,潛移默化地讓學生感悟到了前滾翻的要領(lǐng)。這樣的口訣、范例顯示,運動技術(shù)訓練、教學時運動指導者的作用在于呈現(xiàn)合理的“焦點意識”信息,從而引導學習者對自己的運動感覺進行重構(gòu)。
本文討論可知,必須將運動技術(shù)置于人的身體運動的語境中,緊扣身體運動的具身性、意會性、整體性特征進行指導,講解、示范、練習方法與手段的使用等均應遵循這樣的規(guī)律。
參考文獻:
[1]方婷,王水泉.運動技術(shù)的內(nèi)涵、形成機制及教學要點[J].體育與科學, 2022,43 (05).
[2]王水泉.形式與實質(zhì):體育學何以未能升級為學科門類[J].中國學校體育(高等教育),2014,1 (06).
[3]吳國盛.技術(shù)哲學講演錄[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4]毛振明.論在體育課中如何有效地傳授體育知識(下)——論體育知識的傳授問題與改善方略[J].體育教學,2011,31(04).
[基金項目:浙江師范大學2024年度教學改革重點項目:問題導向的《學科課標研究與教材研究(體育)》課程設計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