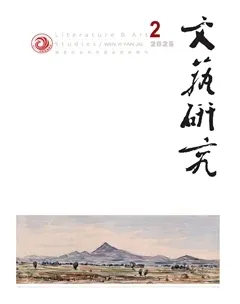文明視域下的韓愈與韓學
摘要 劉寧《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一書提出的“同道中國”“內在責任”以及詩文對理解中華文明的意義等一系列重要命題,指示了韓學的新門徑與新范式。沿著該書的問題意識進一步思考,會帶來許多新的啟示:韓愈所建構的“同道中國”,既“無長無少”地超越鄉土,又“亦孝亦慈”地植根于鄉土,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內在于韓愈的“同道共同體”之中;韓愈不但重視“內在責任”,而且時時強調“外在秩序”,這與中唐政治社會密切相關;古典詩文在中華文明研究中具有整全性價值,韓愈詩歌堪與韓愈古文一體通觀。可以說,該書深具經典意識、學科意識和時代意識,對構建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示范引領意義。
韓愈作為中國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宗匠巨擘,在他身后一千二百年間,與之相關的研究構成了綿延不絕的學術傳統,蔚成韓學之大觀。特別是20世紀以來,隨著學術研究的現代轉型,韓愈研究的方法與意義從更深層面、更廣維度被不斷激發出來。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之一,即陳寅恪的《論韓愈》(《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一文。該文從思想、學術、風俗、文學等方面入手,揭示韓愈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獨特地位,賦予韓愈研究以廣闊而高遠的文明視域、深沉而熾熱的時代觀照,將韓愈研究的學術境界和文化情懷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劉寧《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以下簡稱《同道中國》,引文凡出自該著者,均只隨文標注頁碼) 與《論韓愈》分為六門的散點透視不同,著意聚焦韓愈構建“同道中國”之功,從經典文本的內在肌理出發,更為自覺地探問韓愈之于中華文明的意義。“同道中國”命題的提出,不僅包含著宏闊的文明視域,也具有強烈的學科意識,即發掘中華文明中的“詩文”血脈,彰顯古代文學經典研究的重要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同道中國》與《論韓愈》一樣,不僅植根于厚重的學術史,而且充滿了鮮活的當下性。在筆者看來,《同道中國》一書最具啟發之處,即“同道中國”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何種背景、何種質料上建構起來的。這大概需要從“同道中國”與“鄉土中國”、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古文與詩歌等若干重要命題出發,詳加探討。
一、“同道中國”與“鄉土中國”
韓愈建構的“同道中國”,是指“在鮮明的國家文化自覺的前提下,建構儒學的普遍性”(第22頁)。值得注意的是,韓愈是借助具有強大精神感染力的古文來重建儒學的普遍價值的。從文教的角度看,“宋代以下,士人代代誦習以韓文為代表的古文,深切體會儒家倫理作為絕對信念和內在責任的意義,在古文的化育下,成為彼此同道相應的精神共同體”;從文本的角度看,韓愈《師說》“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是其所建構的‘同道共同體’的真實寫照”;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中唐到20世紀初的一千年時間里,這個‘同道共同體’一直是士人的理想追求,為新儒學奠定了最廣大的社會基礎”(第20頁)。如此,《同道中國》一書從文教、文本與歷史影響等三重維度,闡釋了基于古文建構“同道中國”的基本內涵及其重大意義,為韓愈研究提供了提綱挈領的重要范式,為韓愈對于中華文明的貢獻做出了探本之論。
若進一步思考,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實在是擺在每一位學者面前的終極之問。回顧20世紀以來的學術史,不同學科有各自的視角、方法和觀點,毋庸諱言的是,各學科的研究程度也存在深淺之別。相比于史學、哲學和以社會學為代表的“闡釋中國文化最為活躍的學科”,從文學出發闡釋中華文明的力度、廣度和深度,的確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態。而這一現象“深植于現代文化學術轉型的內在困境”,“新文化運動推翻‘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消解了古典詩文的神圣內涵。現代學科體系中的文學學科,也缺少對詩文綜合文化意義的關注”(第23—24頁)。由此反觀“同道中國”的提出,乃以文學學科之主體自覺探尋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命題。
既然“同道中國”作為文學學科的“破局”之器,自然離不開與其他學科經典命題之間的交流對話。《同道中國》選擇的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概念,進而指出:
對于理解中國,我們既要看到費孝通先生立足鄉村社會所揭示的“鄉土中國”,也要看到以古文為代表的中華文教所建構的“同道中國”。費先生著力關注的是地方鄉村,是對親情血緣依賴很深的社會。鄉土社會無疑是中國社會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我們也必須關注在中華強大文教傳統塑造下所形成的士人精神群體。韓愈是宋代以下千余年間文教的核心典范,他所開創的古文,養育了一代代士人,建構了超越血緣、地域與鄉土的“同道中國”。(第23頁)
從學科本位出發,“同道中國”作為一個與“鄉土中國”平行甚至具有超越意義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不僅可以用來理解韓愈及其以降的古代中國,而且可以認識“近代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征程”,并展望“面向世界建設中國文化的未來”(第2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它不僅提示我們更加重視同道背后的古文與文教,同時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同道既然“超越血緣、地域與鄉土”來塑造“士人精神群體”,那么血緣與鄉土在同道之道和士人精神中到底處于什么位置?同道與鄉土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或許只有厘清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理解“同道中國”的意義。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韓愈在思想世界中對血緣和鄉土既有超越也有依賴。眾所周知,韓愈對儒學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大學》之義,而《大學》強調“修齊治平”的貫通性,其間基于血緣和鄉土之“家”,是勾連個體與社會的關鍵環節。正因如此,《原道》在闡述儒家基本倫理關系時,列舉了“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六大維度,其間凸顯了深具同道意義的“師友”和“賓主”,而家國同構的“君臣”與“父子”高居其前,同屬鄉土之維的“昆弟”“夫婦”駢列其后,六維之中,與“家”直接相關者有其半,如此排列組合和比例分布,讓人感到韓愈在追尋定名的過程中,既有同道之開闊,也不忘鄉土之根深。
韓愈不僅在“立本義”時不忘鄉土,而且在“破邪義”的過程中時時體現家國一貫之思路,痛斥佛、道二氏之說對建基于鄉土之上的家族倫理與親情倫理的顛覆和破壞。如《原道》謂二氏“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論佛骨表》謂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在這些經典論述中,以父子為代表的家族倫理與以君臣為代表的國家倫理形影不離、相伴相生,共同構成“天常”的內核。與此相應,《原道》篇末提出破解二氏異端的方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人其人”是出發點,意謂回歸人倫之常、回歸“天常”,至“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則是在更高層次上維護“天常”。所謂“鰥寡孤獨”,可以籠統看作失去家族成員、失去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的庇佑而身心缺乏依靠之人。那么,如何讓這些人實現“有養”呢?韓愈并沒有展開論述,大概因為時人對這一儒家基本命題非常熟悉。《禮記·禮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孔穎達疏:“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余年也。”“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要讓鰥寡孤獨者“有養”,關鍵就是貫徹推己及人的仁愛原則,讓他們重新回歸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的光輝普照之下,由此才能實現天下大同。韓愈將“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作為《原道》一篇的結尾,將其視為“庶乎其可”的理想境界,正是對開篇“博愛之謂仁”這一儒學普遍性原則的回應。由此可以肯定,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在韓愈思想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它內在于普遍的仁愛以及韓愈建構儒學普遍性的“天下公言”之中。
其次,韓愈的人生歷程及其情感世界中,對血緣和鄉土有著深沉的依戀。從情感充沛真摯的祭文創作來看,韓愈有多篇為其親屬撰寫的祭文,如《祭故陜府李司馬文》《祭十二兄文》《祭鄭夫人文》《祭十二郎文》《祭周氏侄女文》《祭滂文》《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祭張給事文》《祭女挐女文》等。其中,藝術造詣最高、最具文教影響力的,當屬流傳千古的《祭十二郎文》。
細繹此文,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韓愈對十二郎韓老成驟逝的巨大悲慟和強烈自責。韓愈少孤,由長兄韓會、長嫂鄭氏撫養成人,老成是韓會獨子,與韓愈義為叔侄、情同手足。老成的早亡,使韓愈陷入巨大悲慟之中,產生了“不孝不慈”的強烈自責。對于韓愈而言,老成不僅是他的至親,而且是整個家族的長孫,韓愈作為唯一健在的父輩,對老成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正因如此,韓愈深感上對不住祖先,未能保住家族長孫,是謂“不孝”;下對不住老成,未能盡到叔父之責,是謂“不慈”。可以說,“不孝不慈”既是情感宣泄,也是道德懺悔,它深深植根于家族倫理、親情倫理和韓愈的鄉土情結之中。
二是韓愈對“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的悔恨。老成生前,韓愈與之聚少離多,原因在于韓愈常年宦游各地,為了行道化今的理想和事業四處奔波。這一情形鮮明地體現了韓愈鄉土情結與行道理想之間的張力。韓愈為了追求行道化今的理想,不得不長時間地遠離鄉土、親人。然而,地理空間的懸隔并未淡化韓愈的家族意識和親情觀念。韓愈在外宦游十余年間,時時牽掛著老成和他們共同的祖先,或“歸視汝”,或“往河陽省墳墓”,或“使取汝”,心心念念“將成家而致汝”“終當久相與處”“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與老成永遠相養相守,一道過大家族的生活,是韓愈一刻也未曾忘懷的。然而,當親如手足的老成驟然離世,韓愈的內心無處安頓,甚至迸發出“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這樣痛徹心扉的呼號。由此可見,即便宦游行道已經成為韓愈的人生常態,但是親情之根、鄉土之根始終扎在韓愈的心靈深處,而且隨著時間推移、人事代謝,既牢且深,積蓄著巨大的情感力量。
三是韓愈對延續家族血脈的憂思。祭文開篇就提到韓氏門庭冷落的現實:“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只。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可以說,家族的存續問題,伴隨著“撫汝指吾而言”的少年記憶,成為韓愈難以釋懷的心結。至祭文中段,在悲嘆老成早逝和自己體弱多病之后,韓愈再次坦示了家族存續這一心結,焦慮重重地感慨道:“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直至祭文結尾,韓愈又云:“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韓愈從鄉土出發,最后又渴望以之作為歸宿。可以說,韓愈行道化今的使命并不與鄉土相抵觸、相疏離。因為家族之道本身就是儒家之道不可或缺的環節,無論仕途如何,最終還是要回歸“家道”,韓愈早年對此就有清醒的認識,他在貞元早期《貓相乳》中明言:“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縱觀韓愈一生,他始終信守祭文中的諾言,踐履家道,悉心培養老成之子韓湘,直至韓愈晚年,韓湘高中進士,延續了家族的榮光。
最后,韓愈在維系“同道共同體”的過程中,師友之道與家族之道并重,甚至有意識將二者融匯貫穿起來。比如,作為“韓門弟子”主要成員的李翱、李漢、張徹等人,深得韓愈愛重,韓愈把自己的女兒或侄女許配給他們,通過姻親關系增進“同道共同體”的凝聚力。與此同時,韓愈與他的同道之間,時時顧念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砥礪同行。如韓愈《柳子厚墓志銘》稱頌柳宗元哀憐劉禹錫老母在堂、以柳易播的仁義之舉;韓愈哀憐孟郊晚年失子無后,作長詩《孟東野失子》勸慰之;韓愈《歐陽生哀辭》表彰歐陽詹“事父母盡孝道”“慈孝最隆”,同時哀憐歐陽詹早逝、家中父母年老,與李翱分別為歐陽詹作哀辭及傳,“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以此慰藉歐陽詹的父母,助其完成未竟的孝道。
要言之,無論是韓愈個人還是他所在的“同道共同體”,都注重家道的踐履,而集中體現家族倫理和親情倫理的《祭十二郎文》《歐陽生哀辭》以及與家道密切相關的《原道》《論佛骨表》諸篇,率皆韓愈經典之作,是千年文教精粹所系。在這些作品煦育之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同道共同體”,自會體認情理兼備的家道,涵養深沉熾熱的鄉土情懷。或許可以說,韓愈所建構的“同道中國”,既“無長無少”地超越鄉土,又“亦孝亦慈”地植根于鄉土。因為,同道之道乃中國之道,中國之道以家道為底色,中華文明的根脈正在鄉土。
二、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
《同道中國》一書之所以強調韓愈構建的“同道中國”,除了強烈的學科意識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呈現韓愈重建儒學普遍性的意義。在古代中國,儒學的普遍性代表了中華文明的普遍性;而認識古代中國的文明普遍性,對于認識從未中斷的中華文明普遍性,乃至“建構人類大同的普遍性”(第22頁),均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同道中國》看來,韓愈重建儒學普遍性有一條基本路徑,那就是“立足于絕對之善和內在道德責任”(第23頁)。此說最為直接堅實的文獻依據,就是《原道》開篇那段擲地有聲的論述: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這里,“‘仁義’被界定為‘道德’的確定內涵”,同時強調“足乎己”而“無待于外”,充分體現了韓愈“對絕對之善的內在體悟”和對“內在道德責任”的強烈追求(第23、64、448頁)。
值得注意的是,《同道中國》有關內在道德責任的研究,并未滿足于《原道》等綱領性論述,而是深入具體德目及韓愈古文的相關主題之中,做了一番細致入微的探討。比如第四章圍繞“忠”這個主題探討韓愈的內在道德責任。該章首先以韓愈《張中丞傳后敘》為例,指出“韓愈樹立了以‘天性忠誠’為核心的忠臣形象”,“使‘忠’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對親情、天道的依傍,成為絕對而內在的道德追求”(第159頁);其次以柳宗元《南霽云睢陽廟碑》為例,指出柳宗元的書寫傾向是“通過強調中央權威來樹立忠義精神”,而這“是有失簡單化的”,由此更加凸顯韓愈的道德主義立意(第176頁);而后以韓愈《毛穎傳》為例,指出“韓愈諷刺對待忠臣‘老而見疏’的功利實用態度,其才情煥發的俳諧之筆,令‘忠’的絕對道德價值,得到進一步彰顯”(第159頁);最后又與杜甫的“戀闕”之情相比照,敏銳地指出“韓愈和杜甫一樣,都追求對‘忠’的內在性體驗。所不同的是,韓愈更多地表達對忠的內在而絕對的信念,杜甫的‘忠君’則更具親厚眷戀的情感體驗”(第201頁)。合而觀之,《張中丞傳后敘》是正例,《南霽云睢陽廟碑》是反例,《毛穎傳》是旁證,杜詩是參證,此章以多重視角、多重文體詳實而生動地揭示了韓愈對內在道德責任的高度重視。
在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里,“內在責任”無比重要,與此同時,或許還有與之相對而出的另一重要維度——“外在秩序”。回到《原道》這篇綱領性文字來看,開篇以“仁義道德”的定名式論斷闡明內在責任后,轉入古圣“相生養之道”的歷史化論述之中,建構了以“君”“師”為主導,以“中土”為區域,包含“衣”“食”“宮室”“工”“賈”“醫藥”“葬埋祭祀”“禮”“樂”“政”“刑”“符璽、斗斛、權衡”“城郭、甲兵”“備”“防”等一系列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素在內的文明共同體。那么,為什么要構建這樣一個文明共同體?又如何維系呢?在韓愈看來,“人之類”與其他物種相比,“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沒有先天的獨立的身體優勢,而“人之類”之所以還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關鍵在于擁有以“出令”為主要職責的“君”、以“行令”為主要職責的“臣”和以從事生產活動、商品流通為主要職責的“民”三者之間的相生相養。可以說,這一文明共同體存續的關鍵,就在于“君”“臣”“民”構筑的秩序之基。以君臣倫理為代表的“外在秩序”,可謂“相生養之道”的核心要義。
無獨有偶,在強調“內在責任”的《張中丞傳后敘》一文中,“外在秩序”同樣處于至關重要的位置。比如,韓愈為許遠辯誣的關鍵性論斷為“所欲忠者,國與主耳”;又如,韓愈褒揚張巡、許遠“雙忠”的總括性論斷為“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可以說,天性忠誠這一“內在責任”始終以維護國家利益和天下秩序為最終目的,“內在責任”并未超越“外在秩序”而獨立存在。這一思想理路最為鮮明的印證,當屬《伯夷頌》一文。韓愈通篇贊頌伯夷特立獨行的精神品質,開篇云:“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結尾云:“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可以說,《伯夷頌》把士人的“內在責任”推崇表彰到了極致,比《原道》和《張中丞傳后敘》的論述更加集中、透徹,情感也更為豐沛。即便如此,全篇結句還是倏然急轉道:“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這表明,雖然韓愈推崇“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內在性,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士人的“內在責任”必須建立在維護君臣倫理、家國秩序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只顧遵從內心,以至對抗、消解外在秩序。
韓愈之所以在強調內在責任之際,時時不忘外在秩序,將之視作如影隨形的存在,是因為中唐以降內憂外患、政局頻繁動蕩之際,內在責任的相關話語會被持有異見的政治集團所假借,用以質疑、消解王朝秩序的合理性。比如唐德宗貞元后期,柳宗元躋身王叔文集團的核心層,該集團對于德宗主導下的政局有所不滿。于是,柳宗元在《天說》一文中站在王叔文集團的政治立場上,婉言規勸韓愈不要再對現行秩序抱有幻想,其言說策略就是用“仁義”的內在責任取代“天道”所象征的外在秩序: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于果蓏、癰痔、草木耶?
以“天地”“元氣”“陰陽”代稱現行政治秩序,是漢代以來的慣習話語,唐人對此亦抱有普遍之信仰。而柳宗元以驚世駭俗之筆,全面否定了“天地”“元氣”“陰陽”的官能性與人格性,進而對天道秩序發出強烈質疑——“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從根本上否定了唐德宗“代天行法”的合理性,消解了現行政治秩序的權威性,最終以“烏置存亡得喪”的決絕斷語,表達其厭棄德宗、轉投順宗的政治立場。與此同時,柳宗元高擎起內在責任的大纛:既然外在秩序不堪賞功罰禍之任,那么就要借助“仁義以游其內”的主體自覺,讓“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樹立起新的價值標尺,與現行秩序分庭抗禮,為政治格局的顛覆性重構奠定內在責任之基。
由此可見,“內在責任”話語完全可以被政治異見者闡發、改飾和利用,走向“外在秩序”的對立面,甚至實現對“外在秩序”釜底抽薪式的話語顛覆,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作為藩鎮割據、朋黨傾軋、宦官擅權等一系列內憂外患的親歷者,韓愈深知維護唐王朝的統治秩序和君主的權威,實在是當時的頭等大事。正因如此,他在《原道》中著意強調“外在秩序”的重要性,在《張中丞傳后敘》中強調“外在秩序”的目的性,在《伯夷頌》中強調“外在秩序”的前提性,在《天說》中以“天能賞功罰禍”之論彰顯“外在秩序”的合理性與絕對性,與柳宗元偏重“內在責任”的話語形成了鮮明對照。凡此種種,足見韓愈明道化今、力矯時弊、心系天下的良苦用心。
三、從韓文到韓詩
無論是“同道中國”的提出,還是“內在責任”的發現,都是《同道中國》一書的原創性貢獻。這不僅為深入揭示韓愈思想世界打開了嶄新的窗口,還啟發讀者進一步思考“同道中國”與“鄉土中國”、“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之間的關聯與異同,開辟了一條由古典詩文理解中華文明的路徑。
正如該書一再強調的,“古典詩文作為中國古典傳統最精微的內容”,對于破解現代學術發展的“結構性困境”,“獲得對中華文明更加深邃的理解”(第24、28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當然,由于研究對象的限定,除了第七章第三節“狠重之美”等少量章節涉及韓愈詩歌外,《同道中國》主要圍繞韓愈古文展開探討。這里不妨再從韓詩的角度對“同道中國”與“鄉土中國”、“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的關系,試作一些補充性論述,以見古文與詩歌在文明研究中的整全性價值。
如前文所論,韓愈始終保有深厚的鄉土觀念和情結,并將其融入“同道中國”的建構之中。比如,他的《謝自然詩》批判道教飛升之妄,先從“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的歷史理性之維予以否定,而后立足鄉土闡發家族倫理云:“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織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茍異于此道,皆為棄其身。”在韓愈看來,“男女各有倫”的家族倫理,是人之“常理”,不但綿延家族離不開這個“常理”,尊奉君親同樣離不開這個“常理”,而且韓愈特別強調“茍異于此道,皆為棄其身”,凸顯了家族倫理在儒家之道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觀念層面的義正詞嚴,在情感層面,韓愈對鄉土的眷戀更是與日俱增。從元和到長慶,韓愈宦游日深,功名日顯,而家鄉日遠,故土難歸,這不僅沒有消泯他的鄉土情結,反而激發了他對鄉土的執著,不斷在心靈和空間的契合點上尋求“鄉土”的替代性寄托——長安城南的村落。這在元和元年(806)《城南聯句》和長慶四年(824) 韓愈逝世前所作《南溪始泛三首》中有充分體現。
元和元年是韓愈重要的人生轉折點。是年,韓愈結束了貶謫生活,回到長安任職,與孟郊、張籍等“同道共同體”核心成員久別重逢,吟詠講論,成就了一時之盛。就在這行道化今的大好契機中,韓愈仍難割舍他的鄉土情結,與孟郊一同暢游城南村落,寫下了《城南聯句》這首一千五百余字的鴻篇巨制。全詩大量敘寫鄉土風物,其間“紅皺曬檐瓦,黃團系門衡”的自然質樸,“蔬甲喜臨社,田毛樂寬征”的知足喜樂,“里儒拳足拜,土怪閃眸偵”的憨厚可愛,“利養積余健,孝思事嚴祊”的盎然禮意,都讓韓孟感到愉悅和興奮。鄉土的風物人情不僅讓韓孟“歸跡歸不得,舍心舍還爭”“足勝自多詣,心貪敵無勍”,而且還促使他們反躬自省:在一個譎詭多事之秋,在歷經讒毀貶謫之后,究竟以何種姿態發揚儒家之道,踔厲前行。在全詩結尾,韓愈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始知樂名教”,“焉能守硁硁”。耕讀鄉里的家族生活,既是人倫的起始,也是人性的回歸,道德仁義之初心,正賴以涵養存續。在韓愈看來,他早年汲汲于功名仕宦的生活,雖是行道化今的必由之路,卻難免墮入硁硁之境;如今身心不斷親近鄉土社會,才真正體悟到名教樂地所在。可以說,此時韓愈的鄉土之思已然超越了《祭十二郎文》中地理意義上的“原鄉”,在更廣維度和更深層次上啟誘著儒者的生存方式,為行道化今的高遠理想提供溫潤而切近的心靈滋養。
至長慶四年,當老病之軀難以承擔行道化今之任時,高居吏部侍郎的韓愈最終選擇退隱于心心念念的城南村落,決計徹底回歸鄉土。在被視為絕筆之作的《南溪始泛三首》中,韓愈雖然病勢日篤以至“足弱不能步”,深知“余年懔無幾”,但他感到“此已頗自由”,內心世界無比澄澈自適,因為鄉間有“囷倉米谷滿”,還有“溪流正清激”,更有無長無少的村民“勸我此淹留”的真情厚誼……可以說,鄉土的風物和情愫,直至韓愈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他心靈的棲息地。在詩的結尾,韓愈愉快地接受了鄉親的邀請,鄭重其事而又滿懷深情地回應道:“愿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眾所周知,“社”原本是植根于鄉土的禮儀與信仰,由于“古人以鄉為社”,“社”遂成為鄉土中國基層組織的代稱。作為禮儀、信仰與基層社會的綜合性載體,“社”正是韓愈所謂“相生養之道”的實踐場域,它涵蘊著中國人的天地觀念、家族倫理、鄉土情結以及一整套生活方式,是通向家國天下的智識之源和情感之基。可以說,“同社”抑或“同鄉”,就是“同道”的原初形態,仁義禮智、孝慈誠敬這些儒家之道的核心理念,最初往往是在“社”的信仰與空間中孕育和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韓愈從“同道人”到“同社人”的轉變,本質上是從文教精英共同體向鄉土社會共同體的回歸。
另須注意的是,《城南聯句》和《南溪始泛三首》不僅鮮明傳遞了韓愈本人的鄉土之思,而且凝結著“同道共同體”的心聲與記憶。如前所述,《城南聯句》由韓愈、孟郊共同創作,二人遞相聯句,如出一手,天衣無縫。從形式到內容的高度契合,充分表明了韓孟二人共同的鄉土情結,以及緣鄉土之思、濟儒道之樂的一致追求。《南溪始泛三首》雖非唱和詩,但韓愈抱病作詩之際,張籍始終陪侍,深悉韓愈心曲。韓愈病逝后,張籍《祭退之》特為追憶道:“公為游溪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于其鄉。”在張籍看來,韓愈的“愿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并非隨意應和、即興而為,而是頗能代表韓愈心境的“慨慷”之語。可以說,韓愈臨終前深沉濃郁的鄉土情結,深深烙印在張籍心里,并將它寫入以表彰韓愈“其道誠巍昂”為主題的《祭退之》一詩中,流傳千古。
當然,涉及“同道共同體”的詩作,并非始終表現為同聲相應的狀態,偶爾的差異化書寫,往往更能展現韓愈本人的思想特質。比如,韓愈與好友盧仝分別作有以“月蝕”為主題的長詩,盧仝《月蝕詩》在前,韓愈在盧詩基礎上有所變化和創新,改作《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一首。詩題中的“效”,主要指的是詩歌的藝術風格及其托諷主旨。韓詩與盧詩一樣,都是借助蝦蟆精食天眼的奇詭鋪敘,托諷元和時期成德鎮帥王承宗觸忤憲宗、盜據藩鎮之事。詳考韓詩與盧詩的關系,除了帶有謙遜色彩的“效”字之外,韓詩對盧詩有著較大幅度的改易和增刪,彰顯了藩禍背景下“內在責任”和“外在秩序”的重要性。如盧詩云:“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韓詩云:“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韓愈將盧詩的“天公行道何由行”改為“吾道何由行”,凸顯了行道的主體性,強化了“足乎己”而“無待于外”的內在性。雖然盧仝身份卑微,但在韓愈看來,詩人不能只以旁觀者的身份存在,更要以“同道共同體”之一員的責任感,擔負起尊王攘夷、反對藩鎮割據的時代使命。從“天公行道”到“吾道”,不僅強化了“道”的內在性,而且“吾道”由“念此日月者”之天道化生而出,足見“吾道”實承天道而來,同聲同氣,同向同心,絕非自外于天而別樹一道。正因如此,韓詩在結尾處新增“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數句,“天高”見其尊崇外在秩序始終不易,“赤心”見其持守內在責任始終不易,而“屬”“感”“知”均表明外在秩序之“天道”與內在責任之“吾道”貫通無礙,外在秩序與內在責任在理想情境中實現了統一。
然而,正如上節所論,在動蕩不已的中唐之世,君主所代表的王朝秩序受到挑戰,朝野上下往往假借仁義道德的內在話語,批判當世君主及朝廷決策。身為處士的盧仝,就常把自己置身事外,加入了“彼皆刺口論世事”的行列。在《月蝕詩》中,盧仝對唐憲宗處理成德叛鎮的舉措有所不滿,多處借用“天”的形象,譏諷憲宗之政,言辭十分激烈。如“人養虎,被虎嚙。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反用《尚書》“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之典,意謂“天媚蟆”亦屬“自作孽”,諷刺唐憲宗姑息藩鎮、自作自受;又如以“天若準擬錯準擬”諷刺唐憲宗選任非人、決策失誤;再如盧詩提及朝廷大將酈定進時說道“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铓生”,“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意謂酈定進真堪將才,可惜捐軀疆場,不能再統兵作戰,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天失察,再次把矛頭指向決策失誤的唐憲宗。饒有意味的是,在韓詩中,盧仝諷刺唐憲宗的詩句均不見蹤影,韓愈只是提煉了詩人忠君愛國的形象,如“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兇蟆腸”云云。可以說,韓詩著意保留了“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貫通無礙的剴切話語,剔除了僅憑一己仁愛的內在性與絕對性,對外在秩序的合理性與權威性構成挑戰的嘲諷修辭。正如韓愈在《寄盧仝》中所告誡的那樣,“故知忠孝本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潔身”與“亂倫”連屬,表征著“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的緊張關系,而這正是韓愈所警惕的中唐時代一大社會問題。
以上分析《謝自然詩》《城南聯句》《南溪始泛三首》《月蝕詩效玉川子作》《寄盧仝》等韓詩代表作,進一步揭示了“同道中國”與“鄉土中國”、“內在責任”與“外在秩序”的復雜關系,適足印證“詩”與“文”對于理解韓愈及其相關的文明命題同等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詩歌介入文明命題、呈現文明特性的方式,并不在于宏闊思想圖景的建構,而在于細膩入微的場景化、情感化書寫。比如《原道》《論佛骨表》等經典古文,相對全面地闡發儒家之道,自然融攝家族倫理,可見其內在于韓愈建構儒學普遍性的“天下公言”之中。而基于飛升場景觸發韓愈鄉土觀念的《謝自然詩》,更為集中地體現了作為“常理”的家族倫理在儒家之道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深化對《原道》等篇的體認。當然,古文書寫并非排斥場景化與情感化,只是特定的場景和偶發的情感,尚不足以對韓愈的思想世界及其文明命題形成整全性認知。比如《祭十二郎文》作于貞元時期,鄉土之情固然豐沛感人,然而,在韓愈的政治地位和行道化今的影響力不斷攀升之后,其鄉土觀念是否會發生變化?回答這個問題,則有賴更多例證來揭示韓愈的心靈軌跡。作于元和元年的《城南聯句》和作于長慶四年韓愈逝世前的《南溪始泛三首》,延續并深化了《祭十二郎文》中的鄉土觀念,充分證明韓愈的鄉土觀念非但沒有因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而淡化,反而從“原鄉”場景轉入更為深摯邃密的心靈投射。從古文到詩歌,從貞元到長慶,跨文體的長時段考察,為印證韓愈的鄉土觀念,理解“鄉土中國”與“同道中國”的關系提供了重要依據。
結語
綜上所述,《同道中國》一書從中華文明的宏闊視域出發,深度激活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命力,頗具示范引領意義。歸納而言,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經典意識。文學經典具有永恒價值,文學經典研究是學術研究永恒的核心課題,守經典之“正”,創學術之“新”,實乃一代學術之靈魂、一代學人之使命。二是學科意識。《同道中國》既立足文學學科,又銳意推動文學學科與其他學科核心議題的交流互動,在“鄉土中國”“內在責任”諸命題的跨學科對話與反思中,凸顯文學學科主體性。三是時代意識。探尋中華文明及其突出特性,既是重大學術課題,也是時代之問、時代之需。推動中華文明與文學研究的視域融合,既為文學研究提供了創新土壤,也為文明研究賦予了精深意蘊。
作者單位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文史教研部
責任編輯 高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