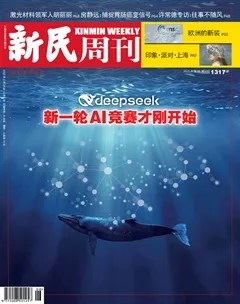胡麗麗:為“人造小太陽”鑄“心”

在人類探索清潔能源與尖端科技的道路上,激光被稱為“最快的刀”“最準的尺”“最亮的光”,而支撐其能量的核心材料——釹玻璃,則是激光器的“心臟”。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胡麗麗,正是這樣一位為“人造小太陽”鑄“心”的科學家。她帶領團隊攻克大尺寸激光釹玻璃的批量制造技術,推動我國高功率激光技術躋身世界前列。
與此同時,她還發揮在激光玻璃方面的研究特長,進一步在激光光纖、高純石英玻璃等領域攻堅克難,啃下多塊“硬骨頭”,打破了國外公司的技術和產品壟斷。
2024年,在韓國仁川舉行的國際玻璃協會年會上,胡麗麗研究員榮獲國際非晶態材料領域著名獎項——N. F. Mott獎,成為該獎項自設立以來首位中國獲獎者。此前共有14位非晶態領域國際頂尖學者榮獲該獎項,包括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士等。此外,胡麗麗還是國際玻璃協會主席獎設立30年來第三位(前兩位分別是2001年干福熹院士及2016年彭壽院士)中國獲獎學者。她被國際玻璃領域公認為杰出且令人敬佩的女科學家。
她的故事,不僅是一段科研攻堅的傳奇,更是一曲“以興趣為燈、以堅持為路”的追光者之歌。
從院士門生
到激光材料領軍人
激光釹玻璃是一種含有稀土發光離子——釹離子的特殊玻璃,它可以在“泵浦光”的激發下產生激光或對激光能量進行放大。激光釹玻璃性能的好壞直接決定了激光裝置輸出能量,是目前人類所知地球上能夠輸出最大能量的激光工作介質。在被稱為“人造小太陽”的激光慣性約束聚變(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簡稱ICF)大科學裝置中,激光釹玻璃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作用。
自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1964年建所到20世紀末,以干福熹院士、姜中宏院士為代表的激光釹玻璃團隊,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奮斗,在激光釹玻璃的研究上取得了從無到有的創新,摘下激光玻璃研究領域“桂冠”,先后研制了硅酸鹽激光釹玻璃、N21及N31磷酸鹽激光釹玻璃,為我國“神光”系列裝置提供了核心工作物質。
胡麗麗的科研生涯正是始于干福熹、姜中宏這兩位中國光學玻璃材料泰斗的指引。她師從兩位院士,繼承了他們對激光材料的深厚研究積淀。從博士階段開始,胡麗麗便專注于玻璃基礎研究,畢業后有幸從事稀土摻雜玻璃的基礎與制備工藝研究。由于尺寸大、性能指標要求極高,大尺寸激光釹玻璃連續熔煉技術挑戰了光學玻璃制造極限,美國聯合德國和日本兩家頂級光學玻璃公司進行了持續6年的共同攻關,才實現了大尺寸激光釹玻璃連續熔煉。在完成美國和法國二大激光聚變裝置的釹玻璃供貨任務后,他們拆除了大尺寸激光釹玻璃連續熔煉線,并對我國實施嚴格禁運。胡麗麗回憶,上海光機所曾嘗試從國外采購一塊大尺寸釹玻璃,但對方不僅開出天價,還以物流為由百般推諉。這一經歷讓她深刻意識到:“別人不給,我們必須自己研究!”
在被稱為“人造小太陽”的激光慣性約束聚變(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簡稱ICF)大科學裝置中,激光釹玻璃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作用。
為滿足我國自主研發激光聚變裝置的迫切需求,自2005年起,胡麗麗帶領團隊對新型高增益激光釹玻璃研發、大尺寸激光釹玻璃批量制備涵蓋的連續熔煉、精密退火、包邊、檢測四大關鍵核心技術進行了近十年的持續攻關。釹玻璃的研發堪稱材料科學的“極限挑戰”。一塊長80厘米、寬50厘米的釹玻璃,需歷經4到6個月的連續熔煉、精密退火、包邊和檢測,任何微小瑕疵都會導致前功盡棄。其制備難度被胡麗麗形容為“與嬌氣的超能力公主打交道”。
難題一個接著一個,羥基和過渡金屬雜質超標、玻璃炸裂、玻璃內部出現條紋和氣泡……胡麗麗團隊在簡陋的彩鋼板棚內啟動連續熔煉實驗。夏季棚內溫度超40℃,熔爐旁更是高達六七百攝氏度。團隊成員回憶:“隧道窯炸裂是家常便飯,玻璃碎片四處飛濺,大家只能一次次重來。”為解決玻璃在冷卻過程中的應力問題,團隊耗時半年重新設計窯爐結構,通過調整溫控曲線和氣流分布,最終攻克這一技術瓶頸。

包邊是四大核心技術之一,而包邊膠的耐環境性一度成為“攔路虎”——濕度稍高即發霉,溫差稍大即脫膠。胡麗麗帶領團隊反復調整膠體配方,引入納米增強材料,最終研發出適應極端條件的包邊技術。
2012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實現了大尺寸激光釹玻璃連續熔煉工藝、測試技術、包邊工藝、精密退火全鏈條關鍵技術集成和貫通。自主研發的激光釹玻璃成品鉑顆粒、羥基吸收系數等核心技術指標國際領先,挑戰成功了由美、德、日三家聯手才能達到的技術極限!

目前,胡麗麗團隊的釹玻璃已成功應用于我國“神光”系列激光聚變裝置和10拍瓦超強超短激光裝置。這些裝置不僅為核聚變研究提供支撐,更在材料科學、高能物理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美國有關專報曾評價:“中國在高功率激光材料領域實現了從追隨到并跑的跨越。”
光之所向,心之所往
光纖是信息社會的“主動脈”和基石材料,而激光光纖則是高功率光纖激光器的“心臟”。進入21世紀以來,光纖激光器逐步占據了激光器市場的半壁江山。其中,摻鐿大模場光纖是高功率光纖激光器的核心增益介質,它的作用是產生激光并對激光功率進行放大,從而實現上萬瓦的輸出功率。摻鐿大模場光纖產品及其制備工藝長期被美國Nufern、nLight等公司壟斷和嚴格管控。
自2011年以來,胡麗麗研究員帶領年輕的研發團隊歷經八年研發,終于在國內率先攻克了萬瓦級摻鐿大模場光纖的批量制備關鍵技術,使得我國高功率光纖激光器裝上了國產“芯”,不僅滿足了空間環境等高功率光纖激光器的應用亟需,更大幅降低了高功率激光器的制造成本,加快了我國高功率光纖激光器在先進制造中的普及應用,提升了我國先進制造的能級。
隨著人工智能及量子計算時代來臨,長距離光纖通信和數據中心的光互連對數據傳輸容量、密度和速率的需求與日俱增,對現有通信材料和通信技術提出了嚴峻挑戰。自1999年,日本學者在摻鉍玻璃中發現了半高寬為150 nm的近紅外發光后,鉍(Bi)離子作為激活離子應用于寬帶光纖放大器逐漸成為研究重點。俄羅斯、英國、美國等研究機構相繼推出摻鉍寬帶光纖產品并用于新型寬帶放大器的研究。盡管我國在鉍離子摻雜寬帶發光機理研究方面獲得了受國際關注的研究成果,但直到2020年,仍未能研發出低損耗摻鉍高磷石英基光纖。
她的故事,是無數中國科研工作者的縮影——在冷板凳上燃燒熱情,在逆境中開辟新路。正如她所言:“激光是照亮未來的光,而我們,愿做永遠追隨光的人。”
2020年,胡麗麗研究員團隊借助已有激光光纖的研發平臺和積累,開始向這一領域發起挑戰。國內20年都沒取得的突破,胡麗麗團隊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率先研制出低損耗摻鉍高磷石英基光纖,實現了國內在該領域從0到1的技術突破。隨后,他們又在國內率先攻克了高增益系數摻鉍硅基光纖關鍵制備技術,先后開發出增益范圍覆蓋O+E+S+U波段的三款寬帶摻鉍硅基光纖,極大推動了國內摻鉍光纖的研究進程,滿足我國光通信領域對新型寬帶增益光纖材料國產化的亟需。
團隊成員再接再厲,還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全光纖結構摻釹激光。2023年國家再次把建立高純石英玻璃研發平臺的任務交給了胡麗麗研究員團隊。用于高功率激光應用的高性能石英玻璃制備技術門檻極高,主要由康寧、賀利士等公司把持相關技術,其高端產品對國內實施嚴格禁運。胡麗麗團隊迎難而上,開展高純石英玻璃制備關鍵科學技術的攻關,一年時間,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套高純石英玻璃的研制平臺、制備工藝模型、極低羥基檢測平臺,并完成了數十輪工藝實驗。
實際上,玻璃的形成和結構及性能演化機制一直是凝聚態物理最富挑戰的謎題之一。我國是世界最大的玻璃生產國,但不少高端玻璃制品目前還受制于人。隨著人工智能AI的發展,玻璃的研究范式亟待改變。如何實現Al賦能的玻璃新材料快速開發成為了當下熱點。擁有開闊視野的胡麗麗研究員積極引進學科交叉領域的海外優秀人才,聯合其他科研機構一同打造涵蓋玻璃結構性能表征、分子動力學模擬、AI輔助建模的玻璃構效關系研究平臺。

多年來,胡麗麗一直保持著每天工作11小時的習慣,深夜改論文、清晨查資料是常態。即便深夜出差歸來,也要先去車間查看熔爐狀態。她坦言,自己從未刻意堅持,只是“樂在其中”。“科研沒有捷徑,但每一次失敗都是通往成功的臺階。”胡麗麗說,克服難題的瞬間,幸福感足以掃平所有失敗陰霾。
胡麗麗用三十余年光陰,詮釋了何謂“擇一事,終一生”。她說,“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已是幸運”。她的故事,是無數中國科研工作者的縮影——在冷板凳上燃燒熱情,在逆境中開辟新路。正如她所言:“激光是照亮未來的光,而我們,愿做永遠追隨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