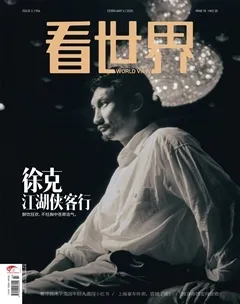產品經理陳思誠,失靈了

評分跌到6.1,票房卻逆勢上漲—巨大的反差,造就了《誤殺3》商業成功與藝術成就無法兼得的尷尬處境。
“誤殺”系列一直是電影市場的票房寵兒。第一部票房13.33億、第二部11.21億,來到第三部,盡管市場冷清,《誤殺3》依然造就了上映10天票房過5億的數字。
本系列監制是陳思誠,無論導演怎么換,陳氏配方依然不變。所以《誤殺3》雖然換了新人導演甘劍宇執導,但故事的主要元素換湯不換藥。主角依然由肖央飾演,背景依然是東南亞某個虛構國家,劇情主線依然是父親對孩子的救贖。在這個角度,陳思誠更像是一個產品經理,導演只需要按照其需求,制作出相應產品即可。
但對比前兩部,《誤殺3》也有一些變化,敘事框架更龐大了。首先就是犯罪規模升級,故事的展開不再圍繞一條被誤殺的生命,或者一座被劫持的醫院,它纏繞著一條全球兒童拐賣犯罪鏈條,以及一座隱約藏在帷幕之后的邪惡島嶼。
肖央不再扮演普通百姓,而是名門富商;被牽扯進來的不只是街坊鄰居和督察長,而是全球實時直播的網友與國家安全署署長。

線索和人物更復雜、宏大、令人頭暈目眩,但故事本身卻比較第一部索然無味了。
來到第三部,“誤殺”系列走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這也是一眾系列電影極易走入的陷阱—為了所謂的“自我突破”一味拓展敘事版圖,結果無法駕馭、適得其反。觀眾反饋的一路下跌已說明一切。
而對于創作者而言,更危險的,是對同一套敘事模板的自我復制。到了第三部,“誤殺”系列電影的生命力似乎已消耗殆盡,走入窮途末路。
司空見慣
對于熱衷懸疑作品的觀眾來說,《誤殺3》的詭計是如此俗套,幾乎每一處自以為精巧的設計都在既往經典懸疑作品中司空見慣。
比如綁匪與主角在電話中玩問答游戲的橋段,就是《神探夏洛克》中莫里亞蒂教授捉弄福爾摩斯的一貫伎倆,熟悉得令人生出一絲厭倦。
結尾的情緒高潮,安全署署長要求肖央飾演的鄭炳睿在兩個炸彈按鈕中做選擇,這是政治哲學中最經典的電車難題,也是被無數犯罪片用以刻畫人性幽微的慣用橋段。
更不要說受害者聯盟設局復仇了。這個招數在同樣由陳思誠監制的影片《消失的她》中就用過了一次,這部電影在2023年夏天取得了35.23億的票房成績。《消失的她》的片尾反轉已經令人瞠目了一次,時隔一年半,另一部懸疑電影再換湯不換藥地重演一遍,實在難以激起部分院線觀眾的驚呼。
誠然,劇情中一些小反轉的設計是精巧的、環環相扣的。通過不同角色視角所呈現的記憶誤差去呈現真相與人性的復雜,隨著劇情進展,主角鄭炳睿一層層撕扯下臉上的偽善面具。
然而,在故事中前期吊足了觀眾胃口,謎底卻與其他大熱電影“撞梗”—給人的觀感就像好不容易吹脹的氣球突然被針戳破了一樣令人沮喪。
盡管《誤殺3》與《消失的她》是同一出品公司,“撞梗”大概率是一次偶然,并不涉及抄襲。但這種偶然對于后來上映的懸疑電影來說,是足以致命的缺憾。
遺憾之余,我不禁思念起《誤殺1》曾經給人的驚喜。
《誤殺1》并沒有多么狡黠的詭計,它甚至直接把主角偽裝不在場證據的過程袒露刻畫給觀眾看。主角利用電影《蒙太奇》中的技法,通過對旁人的暗示與時間線的縫合,制造了一個幾乎完美的不在場證明,那機智、細膩和驚險的偽裝過程依然令人在觀看期間始終揪著一顆心。
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主角李杰維與督察長拉韞的拉鋸戰,期間李杰維的幾次疏漏,拉韞如動物般的直覺與對線索的捕捉,兩個人為了孩子,進行了一場智力與心理上的貼身肉搏。
《誤殺3》中似乎也曾想設計類似的富有戲劇張力的對峙。遺憾的是,它并不如《誤殺1》一般機智—只是在電話中進行幾場你問我答可算不上什么“智斗”。它也并不驚險,肖央飾演的鄭炳睿始終被劉雅瑟飾演的綁匪玩弄得團團轉,一直處于被動位置,受害者聯盟的復仇計劃實現得嚴絲合縫,幾乎沒有偏軌或失控的時刻。
唯一的失控,大概就是段奕宏飾演的警方負責人張景賢被安全署長槍殺。卻也只是如此,凸顯了暴戾,沒有纏斗。懸疑電影本應緊張刺激的心理拉鋸在一次次密集的反轉之中被稀釋淡化、聊勝于無。
罪惡奇觀
《誤殺3》糅合了無數個看似刺激的元素,綁架、謀殺、兒童拐賣、復仇、陰謀、網絡直播與輿論監督,極大地刺激觀眾的感官,整體觀感卻不如第一部精巧、高級,反而顯得累贅、冗余。
這是“唐人街探案”系列走過的老路。一味地追求刺激升級,續集電影一部比一部場面更龐大、星光更燦爛、規模更復雜,口碑卻一部不如一部,遠不及當初“小而美”的《唐人街探案1》。
《誤殺3》也是如此。它規模更大、節奏更快,從第一部的誤殺案升級成為一個龐大的犯罪鏈條,壘砌成一幕幕罪惡奇觀。但奇觀的堆砌很快就令人脫敏了,沒有好故事和好角色的支撐,它們最終都會成為一堆流于表層、乏善可陳的裝飾品。
由此,《誤殺3》對兒童拐賣這一社會議題的刻畫,顯得不夠真誠。
一部商業大片希望盡可能地展現對現實的關懷,這值得贊許。然而,假如這個現實議題被加以種種過度奇觀化的包裝,就會在觀感上顯得更像“裝飾”而非“關懷”。
比如肖央飾演的鄭炳睿。他本應是個足夠復雜的角色,最早是被拐賣的兒童受害者,在童年時期就伙同加害者拐賣他人,最終長成了這個曾經傷害自己的產業鏈條的一分子。
這種“向惡”的轉化值得更細致的凝視與刻畫,并且可以透過它去觀測被拐賣兒童的心理創傷。而在實際影片中,這種人心的變質被當成敘事反轉的一環,節奏匆匆地一筆掠過。

拐賣需求從哪兒來?社會結構如何包庇它?受害者為什么會在其中轉化成加害者?奇觀和反轉擠占了過多的敘事空間,導致人物的流動變得單薄、刻板,圍繞兒童拐賣犯罪產業的種種重要細節因此失焦。
于是,就像香港電影慣于刻畫販毒組織一樣,似乎只是因為這種犯罪組織性質足夠惡劣,容得下暴力、性、剝削等罪惡奇觀,足以制造獵奇,才會被一部電影選中。
只是懷疑,并非指控。創作究竟是否“真誠”,人心只能自證,能為外人所道的,只有作品所呈現的“觀感”如何。
不過,將兒童拐賣犯罪組織塑造得如此奇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足以令一些人印象深刻、警惕并厭惡,以至于這種情緒可以穿透銀幕,實現對現實社會的影響。
就像《孤注一擲》對東南亞詐騙組織的罪惡塑造,讓反詐宣傳乘風借力,抵達了此前難以想象的廣泛程度。如果非要這么說,《誤殺3》對“因果報應”的崇尚、對“壞人終有報”的篤信確有其現實觀照,這也是一部商業電影所能秉持的善意。
審美疲勞
盡管導演不同、故事不同,“誤殺”系列三部電影還是呈現出了氣質上的延續性。
它們擁有一致的結構與元素,比如都在講述父親對孩子的救贖、權貴階層對平民階層的利用與傾軋,并且公眾輿論在故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足以逆轉局勢的角色。這種敘事結構的成功被《誤殺1》的票房與口碑成績驗證,繼而被移植至第二部、第三部。
如今流行的一種評價是,監制陳思誠是個拍電影的“產品經理”。的確,他在商業電影的工業化、模式化中取得了不可小覷的成績,“唐人街探案”系列是一例,“誤殺”系列是另一例。
他深知怎么講故事可以撬動社會情緒、吸引最大范圍人群的關注,并將這些被市場驗證的成功經驗自我復制,取得了這兩部系列電影的票房收獲。這種模式是美國、韓國和中國香港電影產業所走過的輝煌大道。
但固定模式之下,系列電影的高度近似性不可避免地帶來審美疲勞,這也是成功的產業化電影后來走入的死胡同。
“超級英雄”電影曾經多么舉世驚艷,如今就多么令人厭倦。韓國現實主義影視作品曾經影響了法律的出臺,如今也在財閥、霸凌、復仇幾個元素之間鬼打墻地空轉。輝煌一時、曾經捧出無數巨星的港片被毒販、槍戰、警察內鬼幾個元素深刻捆綁,即使請再大牌的明星來出演,都無法掀起如今電影市場的波瀾。
“誤殺”系列電影的模式化,遲早也會落入這種圈套,無法滿足觀眾對新鮮感的需求。
比如權貴對平民的傾軋,平民對權貴的反擊。這的確可以擊中觀眾情緒痛點,制造“爽感”。但如果不對其中關系的復雜性做更深刻的挖掘,遲早有一點會令人食之無味。就像人們調侃韓劇的大反派永遠是財閥,“誤殺”系列的幕后黑手永遠是身居高位的官員,他們的傲慢、暴戾、腐敗,猶如臉譜一般,復刻到了第三部,已經難以給人更新鮮的感受和更復雜的思考。
再比如父母對子女的救贖,“誤殺”系列一次又一次地歌頌為人父母的奉獻精神,說實話,即使這種精神再無畏、再高尚,重復了太多次,依然會變成廉價的感動。
一位網友對“誤殺”系列的評價很貼切,稱它是用最刺激感官的視覺與情節去包裝一種最趨于傳統保守、崇尚家庭的普世價值觀。
這或許是《誤殺3》至今依然票房得利的原因,像一件工藝品一樣正中人感情與情緒的需求,討巧而精明,但往往是這份精致,令它喪失了作為其“第七藝術”的一份真誠與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