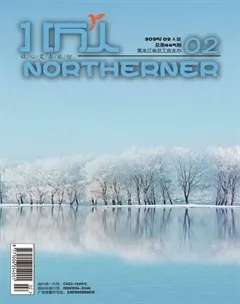舀蝌蚪
前段時間我爸生病,好在手術及時,化險為夷。多虧我家親戚多,照應得嚴密。常常來一大堆人,團團圍住病床,一齊俯下身,弓著腰,久久凝視我爸。這班人全神貫注的姿態,乍看還以為他們在觀賞金魚缸,沉醉于一尾名貴的品種。
只有一個人總在圈外,拎著茶杯,站在大家后面,目光落在大家的背上,或偶爾穿過人墻,眺望著我爸。這人就是我爸的連襟,我姨父。他不僅不往前湊,有時還要退后幾步,隔一大段距離站著,好像他不光是來看我爸的,更是來看大家的。
我姨父絕不是個涼薄的人,恰好相反,他熱厚。他與我爸多年來關系很好,這次照顧我爸更是非常積極。送三頓飯、在醫院跑腿、接待往來的親友、聯絡外地親友等等,姨父這次操勞得很。
其實他原本不用這么操勞,就算我不常在跟前,但家里子侄輩那么多,人手是不缺的,可他就要這么一趟趟跑。后來連我爸都覺出來了,因為一睜眼就看見他一睜眼就看見他。姨父比我爸年輕十幾歲,但也已經過六十,去年也大病一場,我爸因此非常過意不去。等他走后,我爸說:
“你姨父這人太好了,從來一貫的,當初咱們沒看錯人。”
我爸說的當初,是說姨媽和姨父是我媽介紹認識的,在我家相的親。那時我姨媽青春美貌,追求者甚眾,外公一直不吐口,但姨父一來,三五句話外公就含笑點頭了。
后來證明姨父果然是好女婿,哲學系的青年教師,學問當然好,又肯上我外公家干活,又喜納人,四鄰老幼都跟他有話說。我外公是寂寞憂郁的人,外婆也不善交際,自從他來了,不但家庭氣氛歡快了,連在大院兒里我家的知名度都提高了。
記得有一次,我問姨父,當時那么喧賓奪主就沒有一絲忐忑嗎?他說:
“沒有啊,外公最喜歡的女婿是我。”他沾沾自喜地說。
“咦,我以為是我爸。”我說。外公生前在我家住了很久,對我爸的滿意我親眼所見。
聽出我話里酸意,姨父馬上就改了口,他眼睛骨碌一轉,那副“急中生智”的樣子我記得清清楚楚。他說:
“喜是喜歡我,但是看重你爸噻,你爸那時好成熟哦。我那時是勤快,經常跑去買香腸給他下酒。”他說的我有印象,外公后來喜歡晚餐時喝一點酒。
其實我完全相信而且贊同姨父的話,外公最喜歡的女婿是他。女婿都是好女婿,但相比而言我爸顯得冷清溫暾,成熟但不積極,姨父卻有種自然的喜悅熱忱,從他分得很開的兩只眼睛,旋風一樣兒童式的發型,始終笑著的嘴,能看到一派天真,一經相處便被感染。
我一直以為姨父生來就是這樣快樂的,但外公說起過,并不。姨父不到十歲母親就去世了,還沒成年父親又去世了,他和親戚、鄰居把兩個妹妹盤大。實在沒辦法時,他把小妹妹送去鄉下舅舅家,哭著作別后,哭著走了幾十里路獨自回家。說起往事幾句話就帶過去了,但生活對這個少年的殘酷,我到現在都不敢細想。
20世紀80年代初,我那時滿眼都是成熟穩重的人,只有姨父跟他們大不一樣。他熱愛買菜燒飯,熱愛花鳥魚蟲,奇思妙想很多,更有一手折紙絕活兒,從動物到家什到軍械,隨手就能活生生地折出來,我們小孩佩服得五體投地。別的不提,那個“猴子爬山”,誰也學不會。生活對于他本就是樁樂事。
“將來要孝順你姨夫啊。”我爸說,“從小到大的,你姨媽姨父怎么待你的,比親爹媽也不差了。”
“那還用囑咐?”我說。
我命好,姨父姨媽他們簡直像是我爸媽的副職——副爸、副媽。而且往往是這樣,副職的更管事兒。帶我去游泳,給我買兔頭吃,上野地里捉蝴蝶,請老師補課,我離家出走把我找回來,陪我去拿高考成績,等等,都是副爸副媽經的手。
“爸,連你們都沒帶我去過動物園哦。”我將了我爸一句。
“嗯是……都是你姨媽姨父帶你去的,我記得,有段時間你們都快在動物園住下了。”他愧道。
“不過我觀察發現哈,其實姨父并不完全是為了帶我去。”
“什么?”
“明明是他自己想去——每回一到獅虎山他就激動得不行,趴在圍墻上傾訴對猛獸的崇敬;一見孔雀就揮帕子逼人家開屏,有次還帶了把花傘撐開了逼人家;買一斤蘋果只給我吃倆,剩下的他要喂猴子,騙我說孫悟空會來感謝我——你信嗎?”
“我信我信!哈哈哈!”我爸帶病堅持大笑,因為承認我說在點兒上。其實這并不是我現在才有的洞見,我五六歲那會兒就識破了姨父,但我并不失望,相反還更加高興,因為志同道合——都說小孩子眼睛最尖、直覺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同類。
正聊著,姨父又來了,陪著從外地趕來看望我爸的親戚。但他還是不往前湊,就在外圍站著。我還發現,人來得多時,他退得還更遠,干脆就站到病房門外去。后來我又發現,他在門外并不是怕影響人,而是在門外踮著腳尖往里看,使勁看,而且不知他看到什么妙處,居然有時還含笑搖頭,仿佛感慨萬千。
醫囑下來讓做CT,他又跑進來張羅,說:“我認得路,我帶你們去。”
下電梯進了一個很長的走廊,窗外的小雨飄進來,院子里開著粉白的櫻花和淺紫的二月蘭。我心里一陣傷感:這個春天爸爸錯過了。一轉頭看見姨父,他跟我一樣在東張西望,好像也被景色吸引,而且跟我一樣眼睛里也有一絲傷感,但又比我多一點什么。突然他大喊一聲:
“看嘛!就是這兒!我來過的!”CT室果然到了。我忽然想起來,姨父去年就是在這里住院。
去年他跟我爸一樣,手術及時,化險為夷,但畢竟吃了好多苦。記得我去看他,我們一幫子侄把病床團團圍住,一齊俯下身,弓著腰,久久凝視他。老實說,我第一眼幾乎沒有認出來:他的頭發突然就白透了,瘦得脫了形,人比原來小兩號。那時他仍在劇痛中,身體和意識都全力以赴與之對抗,常常有一種扭曲的表情。我心疼死了,而且忽然意識到一件可怕的、總有一天會發生的事。
姨父出院才一年,我爸又住進來了。
“你說有多巧,”姨父說,“我上次住院恰恰是去年的今天,比你爸早整整一年。”
我一掐日子,還真是。
“去年躺在這兒的人是我,很痛很老火啊。當時我就看窗外,也是春天噻。我好不容易熬過去了,真的,就是那句話,劫后余生。今年你爸又躺在這兒了,每一樣我經歷過的老火他都要經歷一遍。我看到他那么老火,我就又想起我的老火。”
“噢噢,所以你特別同情他嘎?每天都跑三趟來看他——不過真是不必要啊姨父,你自己還在恢復期嘛。”
“嗯嗯,我當然特別同情噻,我當然希望你爸快點好起來噻,但其實,我還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啥子嘛?”
“好嘛,看著你爸,我覺得我太幸運了,我想使勁享受我的幸運。但你不要理解崴了哈!我只是通過不斷回憶我經過的老火來體驗生命,我看親戚朋友圍到你爸,我就想起那時他們圍到我,當時我就像你爸一樣只能仰視他們噻,感到自己非常無力。生命那么脆弱,那種老火是圍觀我的人無法感受、無法替代的。我現在好了,我換了一個角度看這個事,我跑到遠一點的地方看他們,我的感覺太好了。”他羞愧地瞄了我一眼,確認我沒有想跟他鬧。
“曉得不嘛,我很心痛你爸遭罪——但能夠加入你們健康人的隊伍,我高興慘了。我這段時間累是累,但高興慘了,我還要加緊耍,去年春天我沒耍得成嘛。”他面對我,臉上是那種自然的喜悅熱忱,從他分得很開的兩只眼睛,始終笑著的嘴,幾十年過去了,仍能看到一派天真。
“不要給你爸說哈。”他特意叮囑我一句。
但我一轉臉就一字不落地告訴我爸了。我爸皺著眉頭聽完,說:
“哼。”
“你不會生氣了吧?”我問。
“生什么氣?”我爸嚷,“我早猜到了!”也撐不住樂了。
前天早上姨父又來送飯,一看就是一夜沒睡好,直揉眼睛。一問姨媽,果然,頭晚他在一個破本子上做數獨題,顛過來倒過去唧唧咕咕玩到凌晨,剛睡一會兒就起來。姨媽叫他不要過來了,勸他、兇他都不行,一定要來。來了也沒啥話,磨蹭了一會兒走了。可十分鐘之后,我接到他一個電話,電話里他把聲音壓得低低的:
“姨媽在旁邊哇?那你不要說是我打來的哈!你只回答是和不是!——你們吃完了嗎?”
“呃,是,是。”
“很好!你現在下來,把那個不銹鋼的飯盒帶下來。我在池塘邊上,快點。”
“呃,是,是。”
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狀況,聽口氣似有危急,馬上飛奔下去。他在池塘邊站著,看見我立刻迎上來。一揭開飯盒蓋子,里面還有剩的麥片粥。
“你喝了吧。”他叫我喝了。
“我剛剛喝過了,飽了。”
“哦不不,你應該多吃些,這幾天你也累了。”
“哎呀我不喝,你帶回去吧。”
但犟不過他苦口婆心地勸,為了我的營養為了我的健康,我只好喝了。他又敦促我一滴都別剩,說農民伯伯多么辛苦。我又把最后幾滴仰脖倒進嘴里。他贊許地接過空飯盒,高興地說:
“太好了!這樣我就可以用它來舀蝌蚪了。——你看池塘邊邊上好多蝌蚪哦!”
(摘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幸得諸君慰平生》)